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当然,散曲与杂剧同时兴于北方盛于元代,且用同类乐曲配唱,明清人统称“元曲”或“北曲”。实际上,杂剧是戏剧文学,除了曲文之外还有故事情节与演出提示之类。而散曲属于诗歌,一种可以清唱的曲文。
而作为诗歌的元代散曲,表现出与传统诗歌迥然不同的风貌。正如元人钟嗣成在其《录鬼簿序》把元曲(这里包括杂剧,实际上杂剧中也有曲文,本篇仅谈论独立的曲文,即所谓“散曲”)比做“蛤蜊”,他说:“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可见,在元代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散曲在艺术上和前代诗、词不同而别具风味了。
而元代散曲的“蛤蜊味儿”,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措辞上的俗。措辞作为文学的基本单位上,从实质上决定这种诗歌表现出不同以往的风貌。咱们先来看一段缪钺师长西席在《诗词散论》中关于传统诗歌的措辞的论述,他说:“古人谓五言律诗四十字,譬如士大夫延客,着一个屠沽儿不得。余谓词如名姝淑女,雅集园亭,非但不能着屠沽儿,即处士隐士,间厕个中,犹嫌粗疏。惟其如此,故能达人生芳馨要眇不能自言其情。”这里的“屠沽儿”,说的是卖酒的,指出身低微的人。也便是说传统诗歌,包括诗与词,多表现人生“芳馨要眇”之情,故其下字用语必定是精美细致的,才能与内容相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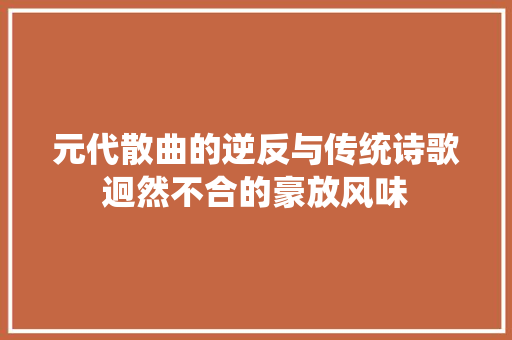
而散曲的措辞多数都是朴实、普通乃至是粗鄙的,市井盛行的口语、俚语、方言等常常涌现。如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娼寮》中的尾曲(散曲分为小令和套曲,小令便是单只曲子,套曲也叫套数,便是按照两支以上的同宫调曲牌的曲子连缀而成,《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娼寮》便是套曲):
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刚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枉被这驴颓笑杀我。
没有人工雕琢的措辞,极具当行本色。
再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尾曲: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
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正在浏览的朋友可以试着读一下,感想熏染这首曲子的口语色彩。在鄙谚中“铜豌豆”是旧时对老嫖客的称呼,而“章台柳”指的是妓女,关汉卿在这里没有传统文人的那种蕴藉蕴藉,丝毫不忌讳表明自己的身份。接下的内容反响自己独特的生活办法与强烈的个性。
其次是主题上的“不正经”。
元散曲中很少有正襟危坐、忧国忧民等比较严明持重主题的作品,而诙谐讽刺、调侃游戏之作随处可见,如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回籍》,截取几段大家感想熏染一下:
……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妇,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壁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壁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壁旗鸡学舞,一壁旗狗生双翅,一壁旗蛇缠葫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些个乔人物,拿着些未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该作品借古讽今,通过一个乡民的视角讽刺当权者的虚张声势。
元代散曲中多的是文人狂气,如王和卿的《仙侣·醉中天·咏大蝴蝶》:
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骚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搧过桥东。
庄周梦中的那只蝴蝶,来到人间尽情采蜜,吓跑了蜜蜂,扇走了卖花人。作者王和卿,是关汉卿好友,大抵是人以类聚,可以看出作者以大蝴蝶自比,展现自命不凡的气质。
还有更多的文人借散曲抒发自己视功名为粪土的方向,如乔吉的《双调·卖花声·悟世》:
肝肠百炼炉间铁,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篱茅舍。
作者乔吉自称是不应举的江湖状元,因此在这首散曲中看不到那种汲汲于功名的态度,有的只是一副看破尘凡的冷心肠。
第三是表达上的直白。
古典诗歌,不论是诗或是词,大多是讲究委婉蕴藉的,而元散曲的表达是相称泼辣且直露的,它不忸怩、狂放恣肆、高兴淋漓。尤其是个中的言情之作,如白朴的《阳春曲·题情》:
笑奖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读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
实在举的这个例子尺度并不算大,还有更多比较直白的散曲感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比较较之下,诸如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一类所谓俚词便是小巫见大巫了。
又如马致远的《般涉调·耍孩儿·借马》:
〔二煞〕不借时恶了弟兄,不借时反了面皮。马儿行叮嘱打发记:鞍心马户将伊打,刷子去刀莫作疑。则叹的一声长吁气。衰衰怨怨,切切悲悲。
〔尾〕没道理,没道理;忒下的,忒下的。恰才说来的话君专记:一口气不违借与了你。
把一个爱马如命的人借走马之后的繁芜心情表现得十分直白又精彩。正如当代学者任中敏师长西席在其《散曲概论》中说:“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
针对上述特点,我想起清人严廷中的一段很故意思的论断:“诗如夫人,以大方温雅胜;词如姬妾,流丽中尚不妨少兼端重;曲则如平康名妓,动人处正在放诞风骚,浮滑妖媚耳。”
可见,即便是有一些民间的俗诗俚词,但诗与词作为传统的诗歌文体,究竟大体上是归于典雅的,而元代散曲,为什么要对传统诗歌如此逆反呢?
首先,北方“俗谣俚曲”的兴盛。这是是元代散曲形成的根本,金元之际,民间“俗谣俚曲”的地位提升,文人们甚而认为比传统的诗词更好。这些“俗谣俚曲”经由文人加工,逐渐形成固定的曲调在各地传唱。出身于民间的曲调,注定不会特殊庄雅。
其次,少数民族乐曲的融入。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全国的朝代,元代文学中注定要熏染上慓悍粗犷的大漠民族风气。正如明人王世贞的《曲藻序》说:“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喧华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媚之。”少数民族在马背上演唱的胡乐,与燕赵地区的年夜方悲歌相结合,促进元代散曲的形成。
再者,市民阶层的兴起及其文化生活的须要。宋末以来的城市经济经由一段期间的结束,在国家稳定之后开始重新走上繁荣。并且元代朝廷是重视商业经营的,因此许多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市民阶层也随之不断壮大。市民阶级的欣赏品味是较普通活泼的,因而产生符合此情趣的诗歌样式。
此外,还有文学内部发展的缘故原由。曲与词有着公认的渊源关系。宋词中就有不少带着谐俗市民色彩的作品,而元代散曲继续之并且更加大胆地打破传统。
剖析任何文学征象,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征象,固然要从外部环境和文学内部等方面来剖析,但是更主要的是要结合创作者的心态来看待。
这批散曲家对所谓封建正统的代价不雅观念、行为规范及立身准则是相称熟习的,在中国古代,熟读儒家经典从来都是文人必修课,这一点我们无需质疑。而在实际上,援塞文人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的,所谓“八娼九儒十丐”,在社会分层上,文人地位在娼和丐之间。元代将人分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笼统地说是蒙古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南方汉人)。文人多数是汉人或南人,总归社会地位本来就很低。再加上元代科举制度时举时停,实际上传统的文人进身之路会特殊困难。
而为了谋生,文人多数混迹于市井中,做书会秀士,与倡优为伍。书会秀士,便是为艺伎写剧本、唱词的人,书会是他们的大本营,也多处于下层人聚拢地之中。
可见,传统代价不雅观念那一套对文人来说更多的是压抑与揶揄,于是,他们索性抛开传统的束缚,尽情地叛逆——也不过是在文学中叛逆。正如本篇谈论的元代散曲,不仅在选词用语上不加以避讳,在内容主题上同样不会有所收敛。
这也便是关汉卿自称为“铜豌豆”的一个紧张缘故原由,也就不难明得,散曲作家对功名为何百般轻视,这也便是他们唾弃权贵的根源。
当然,元代散曲中也是有一部分比较文雅的作品的,正如当代学者任中敏师长西席在其《散曲概论》中有过准确的总结:“词仅可以雅而不可以俗,可以纯而不可以杂,曲则雅俗皆可,无所不容。”
只是,散曲中这部分“俗”的作品,远远超出古典诗词的持重,还好,元代朝廷对文化上的束缚不多,写这些作品并无大碍,我们本日也能由此窥见元代文学与社会的各类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