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娃娃读点古典诗词,是许多年轻父母的共同选择。我曾多次在高铁上听到清脆童声的诵读,内容不是唐诗便是宋词。我也曾接管一些年轻父母的咨询,他们想与我互换关于娃娃读诗的意见。那么,为什么要让娃娃读诗,而且是读千年以前的古人所写的唐诗宋词呢?有人说娃娃有大把的空闲韶光,全用来游戏难免不免可惜,不如让他们提前学点知识。而且娃娃的记性好,不乘此时多读多背,终年夜后再读为时太晚。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利用童子功记诵的知识是终生不忘的,如果幼时背诵几百首唐诗宋词,即是在心中储存一本诗选,往后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手调拨出来默诵、回味,那是多么方便!
但此外还有更主要的缘故原由,紧张因此下两点。
首先,娃娃读古诗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提升措辞能力。措辞笔墨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手段,娃娃先是牙牙学语,然后进入学校连学十多年的语文课,都是为了节制这种本领。让娃娃读点古典诗词,便是学习措辞笔墨的最佳手段之一。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金圣叹说:“诗非异物,只是大家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流传千年的诗词佳构便是说得格外精彩的话语,娃娃从小读点古诗,进而熟读成诵,就能学到最高级的说话技能。比如春天是最可爱的时令,我们如何指示娃娃用措辞来描写春天呢?如果你在早春带着娃娃走进公园,娃娃眼尖,他会敏锐地创造远处的小草一片青青,近处反倒看不见。此时不妨与他们一起品味韩愈的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如果你们看到柳条缀满嫩叶,就可读读贺知章的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仲春东风似剪刀。”如果是暮春的清晨,夜雨初歇,娃娃从一片鸟鸣声中醒来,则可读读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如果娃娃进而问起园子里的海棠花若何了,则李清照的词句是最好的回答:“应是绿肥红瘦!
”还有什么措辞比这些名篇名句更加生动、幽美、准确呢?更何况古典诗词在措辞形式上最大程度地表示着汉语汉字的美学功能,比如笔墨上的对仗,音韵上的平仄,如果娃娃自幼熟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上苍”;或者“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神”,那就从小在语感上节制了对仗、平仄的奥秘,终年夜成人后切实其实可以不学而能。
其次,娃娃读古诗随意马虎为人忽略的好处是道德教化方面的培养和熏陶。儒家一向倡导“诗教”,也即诗歌的教养功能。五四以来,人们对这种教养功能进行剧烈的批驳,彷佛一谈教养便会扼杀自由、消耗个性,实在这是对儒家精神的误解和歪曲。孔子教诲弟子,以德行为先。但是他以“六经”为紧张教材,“六经”中的《诗》与《乐》都属于文艺的范畴。孔子为何如此重视道德范畴之外的诗歌与音乐?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培养弟子的风致教化。在孔子看来,诗歌与音乐的紧张功能不是娱乐,而是教养,它们是教化道德、熏陶脾气的利器。现在大家都强调要让中华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校园,不少学校组织学生参不雅观博物馆,或增加制作陶瓷、辨认中药材等课外活动,这些固然主要,但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看,加强“诗教”可能是更加切实可行的主要手段。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中华诗教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无不身兼幽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它们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空想与审美旨趣,在熏陶情操、造就人格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浸染。诸如热爱祖国、热爱自然、重视亲情与交情、提倡奉献精神、摒弃自私自利,崇尚高雅文明、谢绝庸俗卑鄙,诸多的代价取向,都在古典诗词中得到充分、生动的表示。娃娃年幼,逻辑的论证或理论的推导一时还难以进入他们的心灵。但是阅读古诗,让娃娃感知鲜活的生活情景与幽美的审美意境,其过程犹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夜好雨,各类启迪,各类熏陶,都会不知不觉地沁入心肺。这便是“诗教”的神奇之处!
或许有人会问:古典诗词的内容都是积极康健的吗?都适宜娃娃阅读吗?当然不一定。但是娃娃能读到的古诗都是选进历代选本的经典名篇,他们不可能打仗到古诗中的糟粕。《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选本,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天真。”所谓“天真”,意近今人所说的积极康健。后代著名选家无不遵照“思天真”的原则,经由他们的反复删选,早已把那些不足纯洁或虚情假意的作品淘汰无遗,大家可以放心阅读。虽说当今中小学的语文教材中也有230多首古典诗词,但一来总数嫌少、遗珠甚多;二来教室上的学习每每受到考试、升学等“诗外功夫”的滋扰而缺少涵泳体会,我们还是须要让娃娃加强课外阅读。还有,最好让娃娃在学龄前就开始阅读,家长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启蒙西席。试想,如果娃娃自幼熟读孟郊的《游子吟》,他怎会对含辛茹苦地养育着他的父母毫无戴德之心?娃娃读了宋人孔平仲的《代小子广孙寄翁翁》,他怎会绝不思念尚在屯子老家的年迈的爷爷奶奶?娃娃读了杜甫的《天末怀李白》及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他怎会不关心家中发生事件的幼儿园小朋友?娃娃读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怎会对附近街道上的清洁工或菜场里的小摊贩毫无同情之心?娃娃读了李绅的《悯农》,他怎会随意摧残浪费蹂躏餐桌上的饭菜?娃娃读了骆宾王的《咏鹅》及杜甫的《舟前小鹅儿》,他怎会不对弱小的生命心生爱怜?娃娃读了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及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他怎会不热爱俏丽的大自然?娃娃读了汉代无名氏的《长歌行》或唐诗《金缕衣》,他怎会不珍惜须臾即逝的宝贵韶光?娃娃读了黄庭坚的《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及杜耒的《寒夜》,他怎会不明白书斋生活远胜于灯红酒绿?……更何况读诗的终极目的便是读人,阅读古典诗词的最高境界,便是透过笔墨来走近墨客。等到娃娃读的作品逐渐增多,他就会认识那些人品一流的大墨客。清人沈德潜说得好:“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精良的诗词选本向读者推举的正是那些具有第一等襟抱的墨客,他们的作品都是第一等真诗。先秦的屈原,晋代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辛弃疾,他们都是人品一流的伟大墨客,他们都在作品中敞愉快扉与后代读者羞辱相对,读者可以通过读诗来感知墨客的心跳和脉搏。让娃娃从小与这些人物结为推心置腹的好友,难道不是父母们求之不得的天算夜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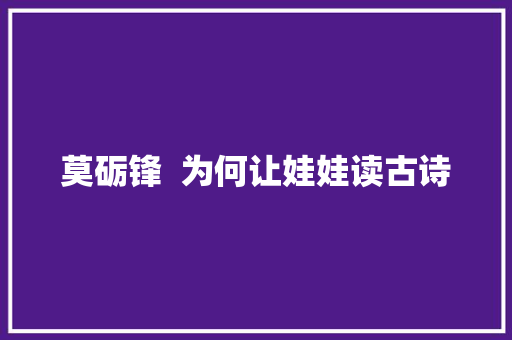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此话从正面肯定娃娃读诗的益处。如果娃娃自幼阅读古诗,他的一举一动都带有几分书卷气,他的待人接物都合宜得体,自然气候高华,不同凡俗。黄山谷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这话可从反面倒推出娃娃读诗的必要性。童年是人格养成的关键阶段,一个人的道德取向,行为习气,以及审美眼力,代价判断,大多在童年奠定根基。山谷指斥的“俗”,包括代价不雅观的鄙俗,审都雅的俚俗,以及行为举止的粗俗,人格境界的庸俗。无可讳言,全体社会环境是很难脱俗的。一旦娃娃熏染了不少俗气,终年夜后也就“不可医”了。若何才能保护娃娃,不让他们熏染俗气呢?阅读幽美高尚的古典诗词肯定是个中最易操作、最能见效的一招。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转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