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是我国古典诗歌中随处颂扬的著名诗篇。它阐述的是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经由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终极辞官回籍与家人团圆的故事。
此卷的神采,便是清新自然,气韵生动,一向到底。近三百字的长卷,无一笔走神失落韵,就此一点,足可宝藏。如果仔细玩味个中的章句,就会以为妙趣无穷。
(主席手书古诗词多凭影象,故偶尔会有错漏字)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心裁声,但(唯)闻女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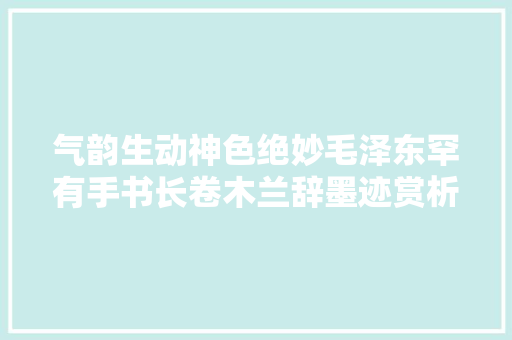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牒(帖),可汗大点兵。羽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以清新如竹的笔法,写得自然洒脱,仿佛给人一种曦辉晨露的觉得,十分可人。“当户织”、“心裁声”、“可汗大点兵”诸字,尤为生动。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鞍(鞭)。
字势逐渐走入开张奔驰。每纸六行的格式为五行所替代,每字独立的形式,似岸边白杨,一字排开,飒飒招人,各有风采。“木兰”、“替爷征”、“长鞍”等字,写得横画摇荡,用笔跳宕,点画打笔清爽,各有攸归,变革灵动。
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朝(旦)辞黄河去,暮宿青海(黑水)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阴(燕)山胡骑鸣啾啾。
这一段的书写,表现力是十分丰富的,“朝辞爷娘去”,如东风拂花;“不闻爷娘唤女声”,如绝壁摩云。随着诗意而走的感情也是明显的。“鸣溅溅”、“鸣啾啾”等字,写得水声四溅,胡马争鸣。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铎(柝),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去世,壮士十年归。
诗歌进入了代父从军的高潮,书法也相应地进入了抒怀的高潮。“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各字的姿态不同,情绪化入点画之中,给人一种跋山涉水,快速行军的觉得。“朔气传金铎,寒光照铁衣”,又是字字相连,笔笔飞动,给人一种北风呼啸,大漠冷烟的边塞实感。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象登上泰山的南天门后,使人猛然松了口气。步入快活三里,顿感赏心悦目。“坐明堂”、“尚书郎”等字,写得劲丽可人,洒脱有余。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颜来,当户理红装。
阿(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
此时,书法又高扬起来。诗歌中反复、对仗所表达的喜悦之情,人物的活动,变成了笔墨上的轻歌曼舞一样的欢畅、雀跃。尤其是当书到“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的时候,四个“我”字,四个面貌,欢欣明朗,一片活气。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出门见伙伴,[伙伴皆惊悸。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诗歌虽然进入尾声,但是书法却又掀起了高潮。书法的意象,与所书写的笔墨,既同步,又不同步;既赞许,又不同意。这是书法的绝妙之处。大书家的书法,内涵多有。仔细品赏,转有所悟。“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免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个中,重字不重笔,以既劲健峭拔、又流丽俊美的格调,写完末了一个“雌”字。
笔停,意未停。其神韵的光环,仍照耀着卷尾的空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