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年轻时并不太想结婚,他后来在 《与王庠书》中说自己“少时本欲兔脱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他最初对十几岁的王小姐也不大把稳,王弗性情沉静并不多言,刚嫁到苏家时,苏轼并不知妻子知书识字,只是每当自己手不释卷时,她“则终日不去”,拿着针线活悄悄陪坐。好几次苏轼背书卡壳了,记不起来了,夫人就在旁轻声给他提个词儿,令苏轼吃了一惊。他指着满屋的书逐一考问,王弗竟都 “皆略知之”,他 “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这才恍觉夫人原来是个沉静聪敏有内涵的女子。
苏轼说妻子“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公婆,皆以谨肃闻”,王弗稳静的个性,恰与苏轼大大咧咧的豪放性情形成互补。丈夫走上仕途后,她常以自己洞察世情的严密,做他识人的帮手。苏轼回到家来,她会细细问询都做了些什么,常引用公公说过的话来提醒他,“你离开父亲远了,凡事没人指示,不可以不谨慎。”有时苏轼在家里待客,她也会立于屏风后谛听,评价有的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何用摧残浪费蹂躏韶光与这种人谈天”;对付专意谄媚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得亲密无间的人,她也瞧不上,“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苏轼不得不承认,夫人的这些判断每每比他要准确,事后皆如其所言。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中岩风景区的唤鱼池,池畔苏轼与王弗的塑像。
又一年大雪,凤翔的住宅庭前积雪甚厚,但有棵老柳树下约一尺见方之地,独无雪迹,奇怪的是,等天晴后这方地皮又隆起数寸来。苏轼认定是古人窖藏丹药之处,丹药性热,以是地不积雪而土又坟起,他想发掘出来。王弗却说:“假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这是引用程太夫人曾经不许人发掘纱縠行老宅地下大瓮之事,来婉转谏阻夫君的逾矩行为,苏轼听了顿觉惭愧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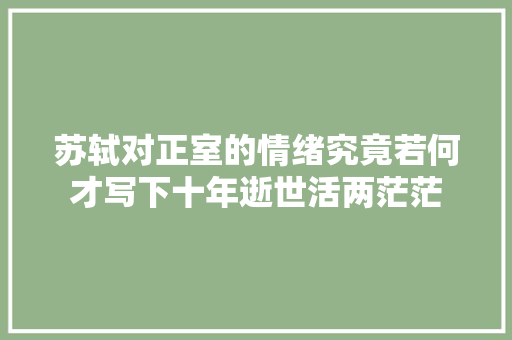
苏轼饱读诗书,学问渊博,但生活的聪慧上对夫人依赖很深。可惜王弗英年早逝,苏轼凤翔任职三年期满,于治平二年 (1065)解任还朝的当年她就去世了,年仅27岁,留下不满7岁的幼子苏迈。所有关于王弗的细节,只有如上几件小事,全部来自苏轼自己的笔墨。他在 《亡妻王氏墓志铭》里对妻子的评价是 “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有识”多用于读书人间的品议,是很爱敬的表达了。父亲苏洵也叮嘱他,“妇从汝于困难,不可忘也。异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苏轼末了悲叹道,“君得从先夫人于地府,余不能。呜呼哀哉!
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
熙宁八年(1075),40岁的密州知州苏轼,做了一个梦,醒来犹是悲惨难遣,作了这首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旬日夜记梦》:
十年死活两茫茫。不斟酌,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悲惨。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回籍。小轩窗,正装扮。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悼亡之作,最大的特点便是情真。蒋勋说苏轼“大胆”,由于他敢坦陈这十年间并不太常常想到你;苏轼也说出了某种真实的履历,当嫡亲至爱逝去,人每每会陷入失落语状态,由于感情太深重,反而不知从何提及。以是有人说开悼亡诗先河的西晋潘岳,三首诗洋洋洒洒十数韵,虽然名气大,却因说得太多太满,有点近乎套话,反而冲淡了“真”的动听。整首词语气愈沉着,读之愈觉沉痛。有时越想梦见越不得见,忽地某天就故人入梦,不期而遇——但你彷佛有点认不出我来了。你还是当年青春奇丽的样子容貌,我却沧桑迎面,这才惊觉,原来十年光阴呼啸而逝,而我们现在已是幽明两隔,永相暌离。可以想见,现实的十年间,苏轼经历了更多人生仕途上的弯曲险阻,他每次因脾气脾气受挫遇阻,大概都会一次次回忆起夫人的聪明睿智,深感她不在身旁的空茫。
下片意识流动场景又切到两人共同的故乡,那小轩窗边装扮的形象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朦胧美好一如当年的青葱岁月,再次目光相接,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仍一时痛惜无言,泪流千行提示着我们这个梦究竟会醒来。末了一句又像是一个空镜头,坟冈荒寒,去世生陌路,哪里可觅幽魂?梦短情长,梦醒后是更深的凄凉,关于肠断,不用再多着一字,而“真情隆盛,句句沉痛”。词本是一种多描写男欢女爱、脂粉味浓的文体,苏轼却用它来写悼亡之情。从来都是喷鼻香浓华美的艳辞易抒,而夫妻间平实深奥深厚的情绪难写,全词纯用白描,笔墨明白如话,毫无雕饰,却字字颤民气弦。一些后人诟病苏轼的词作,向来说他不谐音律,或是辞藻不那么文雅讲究,但他本人比起这种形式上的约束、追求,显然更看重细腻的生命感想熏染、内在情绪的传染力,实在才是重本舍末的代价取向。
治平三年(1066),苏轼与弟弟苏辙扶柩回籍,王弗被葬于翁姑茔墓之西北八步。守孝两年期满后,兄弟俩于熙宁元年(1068)第三次前往京师。他们没有想到,此生再未能回抵家乡,而王弗的宅兆也真的成了千里孤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