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药名诗词,历来是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很独特的文化征象。
药名诗词与涉及中药的一样平常诗词作品不同。一样平常诗词写到中药,要么因此药物为吟咏的工具,要么是把药物作为比兴的形象,中药构成了这些诗词的内容。
药名诗词则不同,如:
“祝愿儿曹添远志,白头翁更寿绵绵。”(清·朱望子《药名交岁诗二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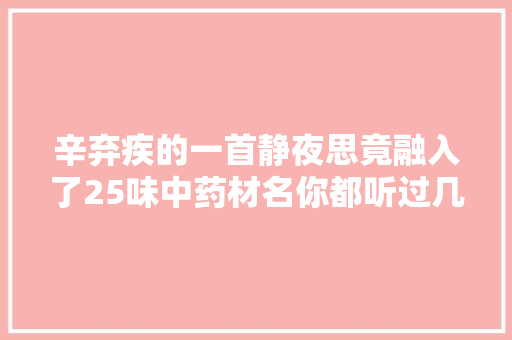
“远志”、“白头翁”是两味中药,用在这首诗中,只取其字面上“远大志向”和“白发老人”的意义,与药物本身并无丝毫关系。
也便是说,药名诗词纯粹从语汇的角度来利用药名,中医药在这里只构成作品形式。这可以说是古典文学与中医药领悟的一种分外征象。
关于中药诗词的起源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不雅观点始于《诗经》。
我们知道,《诗经》看重比兴,借助于景物的描写,如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等,在诸多描写植物的诗句中提到了许多用作中药的植物。比如:
《周南.芣苡》中的“芣苡”便是车前草,古人用来治疗妇女不孕和难产;《王风.采葛》“彼采艾兮”中的“艾”,便是我们本日所说的艾草。
第二种不雅观点是始于唐代。
据《全唐诗》记载,唐张籍确存《答鄱阳客药名诗》一首:
江皋岁暮相逢地, 黄叶霜前半夏枝。
子夜吟诗向松桂, 心中万事喜君知。
诗中共用了五个中药名,除“半夏”为直接嵌用外,地黄、枝子(栀子)、桂心,都是离合前句句首字而成,而“喜君子”则是中药名“使君子”的谐音。可见,药名诗至唐张籍时,艺术表现手腕已经比较多样化。
第三种不雅观点是始于南朝齐梁间。南朝时一些墨客出于游戏的生理,重视笔墨的技巧,故意识地把中药名嵌入到诗句中,匆匆成了诗歌和中药医学的结合,标志着一种新诗体的出身。
关于药名诗词的起源这个问题,虽然意见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那便是药名诗词的创作兴盛期在唐宋,尤其是宋代。
南宋辛弃疾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词人,而且还是一位填制药名词的里手。宋代药名诗词创作最盛。
宋代是词作最繁荣、造诣最高的期间,药名词就出身在这一期间。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如黄庭坚、辛弃疾、朱熹等也加入了药名诗词的创作行列。
他们的作品使药名诗词的题材有所扩大,思想内容变得较为丰富,利用药名进行创作的手腕更加奥妙自然,为药名诗词创作园地增色不少。
可以说,到了宋代,药名诗词才真正成熟了。
据传,辛弃疾在新婚之后奔赴前哨杀敌,疆场夜静之余,便用药名给妻子写了一首《满庭芳·静夜思》,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喷鼻香。离情烦闷,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堂。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
一钩藤上月,平凡山夜,梦宿疆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
茱萸熟,地老菊花黄。
这首词嵌入了25味中药的名称,依次是:
云母、珍珠、防风、沉喷鼻香、郁金、硫黄、黄柏、桂枝、苁蓉(从容)、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常山、缩砂(宿沙)、轻粉、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
这些中药名放入诗词中,有的是用背后的文学意义,如:云母(常用作屏风上的装饰)、当归(表示思夫),还有的是用谐音,如“防风”、“常山”、连翘(翘首以盼)等等,理解起来并不算困难。
这首词把一个深闺中的妇女,在战乱年代的更阑更深之时,独守空房,思念阔别家乡,征战在疆场的丈夫那种悲切悲惨的心情,抒发得淋漓致尽,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更有趣的是,辛弃疾的妻子接到信后,也仿照丈夫的笔触,也以药名回书字封,全文如下:
槟郎一去,已历半夏,岂不当归也。谁使君子,寄奴缠绕他枝,令故宅芍药花无主矣。
妻仰不雅观天南星,下视忍冬藤,盼来了白芷书,茹不尽黄连苦。豆蔻不消心中恨,丁喷鼻香空结雨中愁。人生三七过,看风吹西河柳,盼将军益母。
这里也用了16味中药名,比如槟郎(槟榔)、寄奴、芍药、忍冬、白芷、豆蔻、丁喷鼻香、三七等,也是用得恰到好处,令人佩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