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品读了总理欣赏的名句“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本期磋商第二个话题,这首游侠诗暗藏不露的潜在主题到底是什么?
(本诗上半篇的赏析拜会文章“全唐诗抄18A”,可直接点击作者名“怒刷全唐诗”进入,恕未便利贴链接)
【不求甚解】
开头“韩魏多奇节”,一贯到第五联“击筑游燕肆”,可划作诗歌的上篇,上篇紧扣“奇节”二字,刻画了一位特立独行的游侠少年。他风骚倜傥、纵情市井,言出必行、重视结交。上篇的天下里,主人公过着一种本色的游侠生活。而下半篇开始,风云生变——
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全诗的紧要处:溘然有一天,一位结识的客人远道而来、有事相求,而请托之事是“寻源博望侯”。“博望侯”,专指张骞。当初汉武帝齐心专心胁迫匈奴,张骞是奉命西行、志在打通西域,途中历尽磨难,终不辱义务,开辟了千载扬名的丝绸之路,本人也凭借卓著的功业获封博望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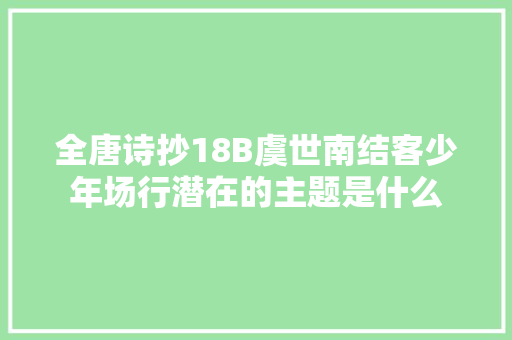
张骞以英年之姿于公元前139年第一次出使,当他再次回到长安,却是13年之后。率领的豪华百人使团,归来时只剩下身边的一个引导。可以说,张骞为君王、为国家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张骞这种开拓进取、热血为国的精神与盛唐气候符合。张骞为汉武帝准确描述过黄河的源头。后人就以“寻源”,特指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的大名也屡屡见诸唐代墨客笔端,他的功业和精神也连同这些光辉残酷的篇章一起成为我们民族永久珍存的影象。
回到本诗,我们的主人公收下的正是这样的拜托,原来快意逍遥的生活也就此被冲破:
少年怀一顾,长驱背陇头一顾,出自《战国策》,所谓伯乐一顾而马价十倍,意指承蒙知遇、受人提携陇头,即陇山,中原的西北门户,出了陇山,便是边塞的开始,系列第16期《陇头水》有详细诠释
少年感激结客的赏识知遇之恩,竟策马长驱,背向陇头往西北边陲而去。
焰焰戈霜动,耿耿剑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戈锋上晃动着灿灿的寒霜,剑身上浮显著刺目耀眼的虹光。天山,经冬历夏都是积雪;交河,自南向北流淌不息。
天山冬夏雪
天山,便是本日横贯新疆的天山。唐太宗的大唐,便是那么克意进取,大唐的军威进入西域直抵天山。持戈仗剑,兵事也,主人公从军矣。翩翩少年,不再浸淫于那种“举刀成一快”的血气之勇,其经受其历练换作了刀光剑影的边塞沙场、艰巨卓绝的军事生活。游侠的个人命运就此与开疆拓土的国家大业紧密地、长久地、坚韧地联系在一起。
云起龙沙暗,木落雁门秋系列至今描写边塞最俊秀的句子:飞云扬起全体龙沙大漠都阴暗下来,木叶零落全体雁门要塞都衰秋萧索。这两句不仅仅是对仗,而且是对仗中非常分外的“对举”,一“起”一“落”,精心择取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显得极具冲击力。并且由点及面,仿佛是“云起”带来了“龙沙暗”,“木落”导致了“雁门秋”,从一点散发成一片,浑然呈辐射之势。这两句真是力量贲张、气候恢宏,情绪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投射。
云起龙沙暗
轻生殉心腹,非是为身谋诗篇末了再次落脚到“士为心腹者去世”,这一游侠题材的正宗主题上来。游侠少年看重的,可能始终还是轻生重义、感怀心腹,这些游侠的特质。可实际上,从超越陇头走向边陲的那一刻起,少年的人生轨迹已然改变。以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民间奇人,而今今后却成为沙场上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杰。所谓的对结客的知遇之恩,本色上已不自觉地变成了对君王、对国家的知遇之恩。
所谓的“轻生殉心腹”,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寻源博望侯”。说透了,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也是一首“招抚诗”。留神诗中深藏不露的结客,正是这位“远相求”的结客,让主人公的游侠身份发生了关键性子的转变。试想,结客为何如此神通广大,能让放荡不羁的奇士心悦诚服,进而不自觉地变成了为国效命?他,又是不是背靠着一个强大的后盾,策划着某种国家大计?
寻源博望侯
招抚,正是本诗深藏不露的潜主题,游侠的主旨彷佛变得不再纯粹。不过,站在另一个角度,虞世南作为国家重臣,在一首游侠诗里为如日方升的大唐代言心声,通报出国家对这些江湖奇士的激赏和热望,却也无可厚非吧?再者说,从“轻生殉心腹”到“寻源博望侯”,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不也是一种人生代价的升华吗?
Anyway,洒脱倜傥的游侠也好,建功立业的战士也好,洋溢着的是浪漫的英雄主义。感谢这首唐初难得的五言乐府,写得如此铿锵有力,大气磅礴,让世间再见英雄!
【碎碎念】本诗的换韵
《结客少年场行》是一首五言古诗,上半篇五联末字“利、志、至、辔、肆”押同一去声韵,下半篇六联末字“求、头、浮、流、秋、谋”押同一平声韵。也便是说,“寻源博望侯”开始,平仄交替,诗歌的韵脚发生转换,而这一句又正是全诗剧情的分界,韵脚的转换与内容的迁移转变紧密结合,早在唐初就能够在古诗创作中如此超前地做到形意契合,虞世南不愧是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