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剑法高手,从不会依赖剑的锋利而取胜,以是曾国藩生平不打“巧仗”,而是老诚笃实施于拙朴,“结硬寨,打呆仗”,却让对手难以招架。越是大略的招式,就越是难以破解,由于功夫都在招式之外;可以被破解的,仅仅只是招式而已。
以是“大巧若拙”。当拙到没有招式的时候,就无法被破解,而只能硬接。这个时候什么计谋花招巧活儿都没用了,所谓“一力降十会”,一力破万法。故而最大的机动,便是拙朴,从巧到拙,已经是发生了质的跃迁。
只有质量上不来,才须要去取巧。战国期间,齐国大将田忌与齐王赛马总是失落败。后来他在孙膑的指示下,以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中等马对下等马,下等马对上等马,终于取胜。
齐王对这个结果很是意外,这时田忌把孙膑的计谋讲了出来,齐王以为孙膑是个人材,便在王宫召见孙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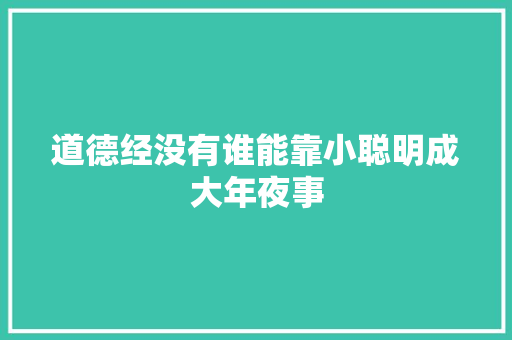
孙膑见了齐王,齐王向孙膑请教兵法。孙膑说,在双方实力相当时,对策得当可以降服对方;在双方实力相差很远时, 对策得当也不过能减轻丢失罢了。
也便是决定胜负的,终极还是实力。倘若齐王的赛马比田忌强出太多,已经到了中等马可以降服对方上等马的地步,那么孙膑就算再有妙招,也无计可施了。
况且双方赛马之前,已做生意定好上对上,中对中,下对下,孙膑使诈不守规则才得取胜。这种胜利,只是取巧钻了规则的空子,可一而不可再,并不值得推崇。
孙膑心知肚明,自己虽然赢得了赛马,但并不能粉饰田忌的马整体本色低于齐威王的马这个事实。故而他当面向齐王表明,只是为了提醒齐王:如果由于投契取巧取得了胜利,就去依赖智巧而忽略了马本身,这才是本末倒置的行为了。
以是极力表现出“巧”的,每每反响的是自身的毛病。拿中国古诗来说,真正的传世之作,都是意境取胜,又哪里会去依赖对仗的工致、笔墨的佶屈,什么“烟沿艳檐烟燕眼”之类的作品,不过是博一笑的杂耍而已。
中国古诗风雅的花样不少,比如诗里有“堆絮体”(将前句借作后句的前半部分,如迭棉堆絮、“联珠诗”(用前一句或前联的结尾词语,来做后一句或后联的开始)、“藏头诗”、“十二属诗”,再难有“离合诗”、“宝塔诗”、“盘中诗”、“连珠体”、“回文体”,更离谱的是还有“璇玑图”。
璇玑图作者苏若兰听说是魏晋三大才女之一,总计八百四十一字,纵横各二十九字,纵、横、斜、交互、正、反读或退一字、迭一字读均可成诗,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不等。整图回环反复读起来,可得诗3752首。明朝又有人推出4206首,今后竟有人推出7958首之多。
但众所周知的是,在诗坛里名垂千古的是李白杜甫苏轼,不是苏若兰。只管她将笔墨游戏玩到了极致,但究竟只是笔墨游戏。璇玑图得诗三千多首,却没有一首能比得上苏轼的《水调歌头》。
老子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路很平坦,人们却喜好去走小路,投契取巧走捷径。但捷径不是大道,以是很随意马虎走偏,遇险。喜好以小博大,喜好以巧胜强,喜好行险取胜,一次失落败便足以遭受灭顶之灾了。
人们为什么会以长于钻营,长于投契取巧为能力呢?所谓“聪慧出,有大伪”,智和巧的兴盛,实在是道和德的缺失落,是人们失落去了自然的心态、丢失了朴实的根基的结果。
丢失了自己的根基,以是会暴躁、急功近利;丢失了自己的根基,以是会心中不稳、不定,而走上偏邪小路。老子说:“不失落其所者久”,丢失了自己根基的人,就像无根之木一样平常,连长久都做不到,又拿什么来成大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