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数日告别激情亲切好客的朋侪后,进入湖南湘地界。二十九日,孙觌过湖南永州零陵,太守于澹山置酒待之。“孙仲益北归过零陵,太守赵君宰置酒于澹山,与时昌辰、李师武、王子钦同集。绍兴甲寅十月廿九日。”澹山乃湖南零陵名胜。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七十四:“零陵水石天下闻,澹山之胜难具论。”
孙觌被释北归,一起有当地官员为其迎送,忧心渐开。
过湖南永州,太守赵君宰置酒为其送行,孙觌写《北归过永永守赵君宰置酒万石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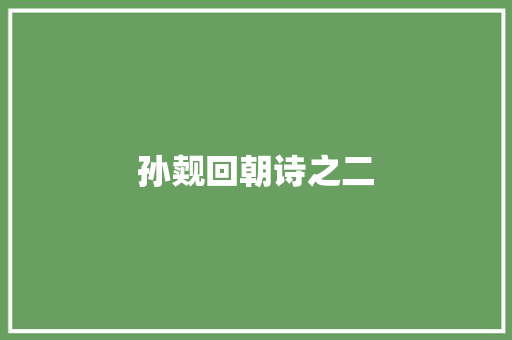
三湘陌上逐臣归,万石亭中送客时。拄杖披榛行莽苍,汲泉磨藓看魁奇。
天倾五色遗娲补,谷变千年出岘碑。何似溪边小桃李,向人膏面出风采。
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七十一载:“万石亭在零陵县城北,唐刺史崔某建,以多石故名,唐柳宗元有记。”按,万石亭当在澹山。
又见影印文渊阁四库本《鸿庆居士集》的《澹山岩题名》记载:“孙仲益北归过零陵,太守赵君宰置酒于澹山,于时昌辰、李师武、王子钦同集。绍兴甲寅十月廿九日。”此时的孙觌大概是“江湖一梦三年久,慰我漂零一杯酒”的无奈,或者,如《利见置酒燕超轩袭明赋诗次韵》中“杯行得手莫留残,忍听金钟吼更阑”, 又如“共惜分襟能几日,直须把酒罄交欢。”
酒成了这一期间孙觌诗歌最常涌现的物象。酒是孙觌与朋侪惜别的余味,也成了其回归的借口,当然,也变成了其暂时消解愁苦的一味良药:
落日投林去,低云贴水飞。江翻半嶂倒,帆健一风肥。
酒重倾蛮榼,歌清绕妓衣。城南多胜事,何比阆中稀。
在这首题为《即事》的诗作中,孙觌醉倒酒乡中,宽慰自己可在贬谪途中看遍大好风光。诗中虽言“城南胜事”与自己无关,却能看出这是自我宽慰之语。而沉沦究竟有酒醒之日,此时的孙觌既想说服自己,却深受湖湘之地的文人墨迹传染,诗歌中呈现悲哀与深奥深厚之感,显示出抵牾而纠结的感情。孙觌行至愚溪,作《愚溪》诗一首:
“群休眩鹿马,独觉办渑淄。虫鸟岂知道,断尾畏为牺。草木讵有灵,卫足不如葵。智囊樗里子,痴绝顾恺之。成坏系所遭,何必陋昨非。仪曹天下士,失落身蹈危急。一斥卧江海,南冠系湘累。不思蛇起陆,便作鸟择栖。匿智以为愚,更欲名其溪。溪山清可厉,溪上碧相围。石底行翠虬,烟中抹修眉。一朝纩息定,白日断履綦。丛祠翳篁竹,秋风生网丝。凛凛望千载,避世真吾师。故物不可寻,山川尚华滋。永怀西州动,兴言北山移。欣然解其会,明晰不复疑。独醒亦何事,誓将餔糟醨。举酒酹一觞,宛宛度两旗。蕉黄配丹荔,歌此迎神诗。”
湖南永州愚溪,是柳宗元谪居之地,孙觌借此地名表达自己的旷达,湘楚囚拘之人钟仪与爱国志士屈原给孙觌以灵感,有柳宗元的《愚溪诗序》。读了柳宗元的《愚溪诗序》,遭贬获释的孙觌感同身受的同时,也收成了答案,孙觌不仅表达自己对柳宗元的敬仰,而且,鼓起勇气做到超脱。诗中引“荔枝”“焦黄”也表达了自己年华逝去的无奈。孙觌入衡州城,馆于太守之斋,有《过衡州馆于郡斋时太守裴梦贶督役于城上》诗云:
万锸风雨集,三令霜雪严。适发半闾左,雅舂亦髡钳。
大事难虑始,掇龟宁复占。君看执扑者,端是邑中黔。
孙觌离开连续北上,到达湖南洞庭湖,浩渺无际的湖水,激起墨客的无限感慨,孙觌写下许多的“回朝诗”,个中以《过洞庭》诗为首:
“千尺银山屹嵩华,浪涌云腾天一罅。榜舟夜傍乌龟窟,杖藜晓入鸡豚社。处处人家橘柚垂,竹篱茅屋青皇亚。台殿青红坠半山,两腋清风策高架。牛羊出没怪石走,蛟蛇起伏苍藤挂。饥鼠窥镫佛帐寒,华鲸吼粥僧跌下。世味饱谙真嚼蜡,老境得闲如咽蔗。山灵知我欲归耕,一夜筑垣应绕舍。”
有一个遭贬的大墨客张孝祥(1132-1170)也因受谗毁被秦桧罢官后自桂林北归的途中所作洞庭诗。与孙觌相同境遇,相同的北归,大概心有灵犀吧。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也写了首《念奴娇·过洞庭》。只可惜,与八十九岁去世的孙觌比较,张孝祥三十八岁就英年早逝了,不该啊,这便是命。
零陵位于今湖南永州,从中可以得出,孙觌北归从象州,过桂林,经湘归晋陵。孙觌北归,经由湖南祁阳时,见到了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浯溪石崖,磨平刻碑,该石刻《大唐复兴颂》为颜真卿书。公元763年,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墨客元结履任道州刺史,在履新途中碰着一处良好之地,被美景所触动,撰写了《浯溪铭》以纪念之,浯溪之名由此来之。
八年之后,元结将自己最为著名的文章《大唐复兴颂》修正之后,请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后刻在浯溪摩崖之上。碑文是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所撰,文辞古雅遒劲。 石崖在北宋晚期就已经残损。北宋末年又有多种翻刻。宋朝皇室多精于书法,颂文亦非虚美。前代圣贤的手泽真迹,苍崖丹壁,点画犹然,于此便与古人亲接,衣冠音容,如在目前,光风霁月,通透和畅,千古圣法,会然于心。心绪渐开的孙觌大为感慨,写下《复兴颂》以纪之:
水部天宝复兴碑,浯溪摩崖天与齐。龙亡虎逝今已矣,太宗社稷犹巍巍。
泗滨九鼎不复出,陈仓石鼓今已非。岿然独立湘水上,每每或有神司之。
我亦系舟石壁下,老眼惊顾眩欲迷。星图错落树挂斗,云物黯淡天投霓。
遗忠寂寂閟千载,山颓木坏知河□。踟蹰对立三太息,风雨夜啸猩鼯悲。
宋黄庭坚诗曰:“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名崖颂复兴。”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宋洪迈《容斋随笔》云:“次山《复兴颂》,与日月争光。”清顾炎武《金石笔墨记》、王昶《金石萃编》等书著录。《大唐复兴颂》一篇,自唐人皇甫湜,宋人黄庭坚、孙觌、范成大、洪迈、岳珂、米芾、李清照以下,各有品题。
说到大宋的复兴,还得从孙觌莫逆之交的汪藻起草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基,在文告时首倡“复兴”话语:“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复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
康王赵构建立南宋,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汪藻不愧大手笔,以光武复兴、重耳复国等典故熨帖设譬,大意说,赵构出自康王藩邸,继续宋朝皇统,恰如汉朝之厄,虽在十代,理应光武复兴,晋献公之子虽有九人,唯有重耳幸存,这正是天意,岂能是人谋!
刚经历靖康之变的亡国之痛,朝野高下切盼赵宋复兴,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诉求与民族生理。北宋传九帝,国祚167年,国家结束了唐末五代军阀盘据的混乱局势,五星聚奎,文运大兴。此时南宋亦传九帝,国祚152年,南方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大宋又走向了文治的高峰。这是当时时期背景与节点。
绍兴制定条约前后十余年间,官僚士大夫议论政事险些言必说“复兴”。全体南宋朝廷的政治培植包括高宗天子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复兴”的历史阐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解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出息。
后来到了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时任永州通判的皇宋宗室赵不忧写下《皇宋复兴圣德颂》,即《大宋复兴颂》,盛赞高宗、孝宗两朝“揖逊之风,孝治之美,自唐虞以来未有盛于今日”。其父赵士圃被金人所俘,随宋徽宗北迁五国。金朝完颜烈来宋朝,赵不忧为使馆副伴,与金使相见,对揖抗礼。乾道七年(1171年)刻石于夔州,嘉定二年(1210年)再刻于浯溪,位于《大唐复兴颂》之侧。
孙觌此时写下《复兴颂》,一是感谢宋高宗的皇恩浩荡使得自己得以解除辑枷,其余,也是借此顺应官场“复兴”的舆论大流,为自己重回仕途做点舆论的准备。孙觌被一起迎来送往的酒酣应酬吹得有点由由然了,以为自己这次北归能重回朝廷,再现当年词臣之荣光,复兴是也。欲望总是美好的,万一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