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毫无疑义是有节奏感的,而且诗歌也讲究节奏感,不论是写作还是朗读,说一个人写诗写得差,可能就会提到“你的诗没有节奏感”。村落上春树曾提到的写作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不同于音乐性。音乐性在节奏方面是内含节拍感和节奏感的,当然音乐性包含更多的东西。
从音乐专业来讲,它包含四要素:节奏、旋律、音色、和声,这种节奏感便是作为类似于音符的诸要素在一个故事回环里的主次强弱模式,以及这种主次强弱模式在整部作品里按照主次强弱的行进关系进行的有机组合。
写小说节奏感比较好的像罗兰、沈从文这些人,他们的作品就洋溢着音乐感。沈从文的《边城》,整部小说就像翠翠在梦里折虎耳草时听到的儸送二老唱的湘西情歌,缠绵诗意,原始自然。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则是大气磅礴的十三乐章交响诗,饱含人情冷暖和人性变迁,这种错落的节奏感让不雅观者的心与情共振,一同颠沛,一同忧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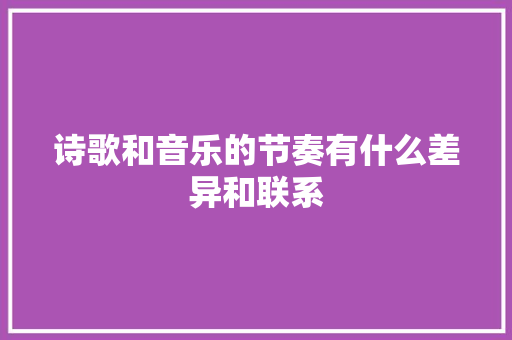
不论诗歌还是音乐,还是文学作品,其好的节奏感总是能打动人心,并能在不同情绪层面冲动民气的,这之间并没有太多神秘的色彩。
以音乐为例可以剖析一下为什么不同节奏感的音乐可以拨动心弦,而且会拨动很多人相似的心弦。
最原始的音乐样式是只有节拍的,节奏是节拍的发展,像和声、音色、旋律都是后来比较高等的产物,那些最原始的音乐便是不同节拍的组合,在现在的非洲原始部落音乐里,这种纯节拍式的音乐是仍旧能找得到的,有的乃至包含非常丰富的节拍模式,节拍可以以大略周期的办法把音乐扩展地很远,造成循环往来来往又稳定发展的效果,有点像音乐样式里的卡农。
最大略的节奏模式是原始的人在实践中对人,和人生活的自然的各种节奏的模拟,比如人的呼吸、奔跑、行进、做爱的喘息、呼呼的风声、鸟的啁啾、水流、海浪拍打岩礁、日月的交替还有四季冷暖等等,那时候的人类还处在未开化的无知之中,对付统统的感知是大略直接、原始朴素的,而人类现今繁芜的思维和情绪模式正是在此种原始的模式之上成长出来的,于是当人们听到某些节奏的时候,类似于这些节奏的情绪就会被唤醒,而原始的这种节奏模式即是在本能层面上触发人的情绪。
诗歌是有节奏感而没有节拍感的,只有节拍感时,诗歌中的那个迷思和情绪便被机器地切割了,连同诗歌的形式美也会荡然无存。
拿海子被改编成歌的《玄月》做例子:
眼见/众神/去世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两拍子按照强弱读,这首诗已经惨不忍睹了。周云蓬唱的《玄月》就很棒。
音乐是可以同时有节奏和节拍的。节拍本色上是固定的拍子模式,是最大略的节奏,但它却不是我们常日所说的真正的节奏。十九世纪象征派墨客魏尔伦说“夺覆信乐从诗歌那儿夺走的东西”,该当说音乐从未从诗歌那儿夺走什么,有些东西诗歌中压根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