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情节弯曲动听,哀婉凝绝,对封建礼教无情的反攻!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时年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去世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一片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哀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仗义执言,武断主见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见本来是对的,但由于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有僭越之嫌。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即本日的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期间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管监督扼守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革的迁移转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消磨,悲观感情日渐其多。
白居易《琵琶行》以细腻动听、凝练秀美的诗句被传颂千古!
白居易在旬阳江头送客之时,把酒叙谈,心中苦闷难抑,无法排解,这时偶遇一歌女弹琵琶抒怀抒怀,曲调哀婉动容,便不由自主相邀来船中坐下弹一曲。白居易毕竟是大墨客,听罢一曲生情扼腕,感触良多。不禁发出“同是天涯沉沦腐化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悲切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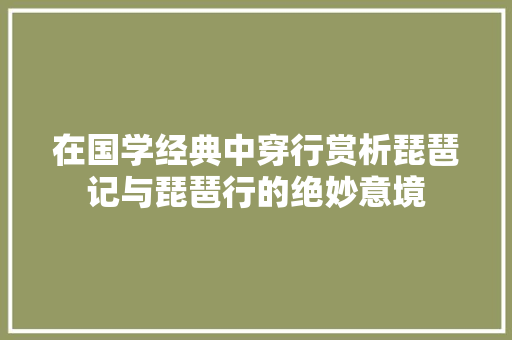
《琵琶记》内容动听,情节弯曲动人,情真意切。给后世的影响巨大,我们本日反不雅观这部作品中主人公蔡伯喈只封建知识分子的代表,活在夹缝中的那种内心的挣扎和痛楚,无法解脱封建礼教的从君从父”的愚蠢思想的束缚,对付父母的去世亡难辞其咎。一方面自己有思乡盼归的动机,一方面又害怕牛相的威信,内心抵牾重重,无法释怀。作品刻画了他的懦弱、胆小怕事的一副“伪君子”嘴脸,是那种把头扎进泥土里“鸵鸟式”的人物形象。而赵五娘的性情就比较光鲜。对公婆做到了“忠孝”,对自己的丈夫始终奉行一个“从一而终”的古代封建社会守节守义的女子角色。作品以更多的笔墨细化赵五娘在封建礼教下的守住伦理纲常的悲剧了局。
《琵琶行》作品借着阐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悲惨出生,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烦闷悲凄之情。在这里,墨客把一个倡女视为自己的风尘心腹,与她惺惺相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官场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和为一体,世态的冷暖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平凡的传染力。
如此巧合,如此相似的出生,经由墨客之手翻作一曲千古绝唱。我们本日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熟知《琵琶行》,也在传唱《琵琶行》,感想熏染文学魅力和艺术之美。
同为两部经典,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精神享受。一部戏曲,有传唱千古的神韵,昭示后人若何做人;一部诗歌,有波澜起伏,动听肺腑的神奇穿透力,措辞凝练,字字珠玑,掷地有声。他们的传世之功不禁让我们叹为不雅观止!
经典永传承,两部不休的作品永久闪耀着聪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