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紧张人物薛宝钗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一首词作,大概是《临江仙·咏絮》了。此前,笔者曾写有“咏絮词的翻案与断线的鹞子”一文,对薛宝钗该词翻陈出新的意义,受宋人侯蒙词的影响以及与探春放飞鹞子的关联,作了剖析。而有关个中一句“蜂团蝶阵乱纷纭”的版本差异及诸家的不同阐明,却未及展开谈论。由于此问题涉及诗词理解的多种可能,即传统所谓的“诗无达诂”,以是这里加以专题论述。
先看全词: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纭。几曾随流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年光时间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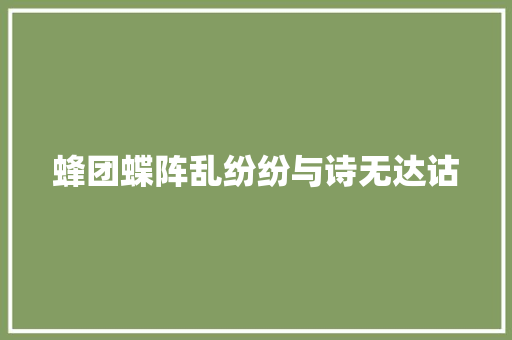
对词句“蜂团蝶阵乱纷纭”中的“蜂团蝶阵”这一短语,各家阐明存在颇多不合。
其一,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给出的表明,认为蜂蝶的描写并非实指,而是用来“比喻柳絮纷飞繁乱”。文化艺术出版社《红楼梦大辞典》中由徐匋、王景琳卖力的“诗词韵文”部分,对“蜂团蝶阵”的阐明,与红研所校注本基本同等,也认为是“意谓柳絮像一群群蜜蜂蝴蝶一样纷飞繁乱”。这两种阐明,不但阐明的指向同等,连关键用词也相同,或许出自同一人之手,或许彼此有过参考。
其二,不认为这里存在比喻,而把蜂蝶作为实指来阐明,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红楼梦鉴赏辞典》,由陈邦炎撰写的该词阐明,就认为写“蜂团蝶阵乱纷纭”一句,是作为对柳絮的一种衬托,“更给人以春意盎然的繁盛热闹繁荣之感”。既然说是衬托,就不可能再把蜂蝶与柳絮稠浊为一。
其三,既侧重于认为此句有关蜂蝶的描写是实指,同时也接管作为比喻的另一说法。比如,蔡义江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一书。但蔡著在看重蜂蝶实指的同时,对作者描写蜂蝶的浸染,给出了别样的理解,认为这是在写“成群蜂蝶纷纭追随柳絮”。蔡著之以是作这样的阐明,大概跟他依据的《红楼梦》不同版本有一定关系。蔡义江的“鉴赏”一书,引用临江仙词,依据的是程印本将“蜂团”改作“蜂围”,而脂本系统比如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乃至乾隆百廿回抄本,都作“蜂团”。针对程本从“团”变而为“围”,就须要在阐明中探求一个所围的工具,于是顺理成章阐明成蜂蝶对柳絮的追随了。
让人颇可玩味的是,《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是蔡义江从前的一部作品,后来,他推出“新评红楼梦”时,对这首词的笔墨,依据的是脂本,即写作“蜂团”的。不过,把“新评”与“鉴赏”中有关这首词的表明进行比对时,创造两书都是逐句表明,给出的阐明也险些一样,但唯独在“新评”中,略过了“蜂团蝶阵乱纷纭”这句表明。这是否在故意回避因依据的版天职歧而导致阐明可能涌现的抵牾?还真不好判断。
对付这几种不同的阐明,我们该当怎么看?特殊是最关键的问题,有关蜂蝶的描写究竟是写实还是比喻?有人从“诗无达诂”的角度,对不同的阐明一概予以收受接管。比如,蔡义江在他的“鉴赏”一书中,既提出了自己关于蜂蝶写实的理解,又说“或以蜂蝶之纷乱比飞絮,亦通”。笔者对这最关键的阐明歧义,不收受接管两可的说法。个人认为,以蜂蝶之纷乱比喻柳絮,是不通的。
虽然这样的比喻说,表面看可以让咏柳絮词,在主体物象这一点上,保持前后的同等,彷佛是通畅的,但其缺憾也明显。首先是去世盯住柳絮写,使得描写的境界过于逼仄,有点像喷鼻香菱学诗时写的第一首,叫她咏月,她就盯住玉轮去世缠烂打,连高下句重复描写的合掌之病也不管了。既如此,倒不如理解为是用蜂蝶的写实来荡开一笔,衬托柳絮,也是让春意的境界更开阔。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如果把这理解为柳絮的比喻,那么,同一描写工具的柳絮,在前后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由于前一句,正是在写柳絮被东风“卷得均匀”。
对付“均匀”,红研所的校注本出注“指舞姿幽美,平均有度”;而蔡义江的“鉴赏”,则阐明为“指舞姿柔美,缓急有度”。不管是“平均有度”也好,还是“缓急有度”也好,这种“有度”的整体性和节奏感,是跟蜂蝶的“乱纷纭”无法折衷起来,在描写上前后断裂的。而这种无法折衷或者说断裂,正凸显了词作者的比拟效果。看似不自主的柳絮,由于有“解舞”之春来掌控,以是,能够让东风打理得那么折衷而富有节奏感。比较之下,看似能够自主的蜂蝶,却在整体关系的“团”“阵”中,呈现了一派纷繁的乱象。由于写蜂蝶的紧张效果是比拟柳絮“卷得均匀”,以是,陈邦炎理解的所谓渲染春意盎然的热闹效果,也就不应是写作的紧张目的了。
因此,笔者对前列的三种阐明和干系版本,提出自己的判断是:在写实和比喻中,取写实说而舍弃比喻说;在写实说中,取脂本的“蜂团”而不取程本的“蜂围”。情由是,如果蜂蝶是在整体上“围”向柳絮的,又有了受外在统一目标掌控的嫌疑,纵然这种“围”上去也是乱的,但“乱”中,仍旧有目标不乱的同等性,与前句的“均匀”比拟效果还是不足强烈。以是,阐明为写实的蜂蝶“围”住、追随柳絮,虽可以被接管,但不应该是最好的阐明。
换言之,纵然笔者认同“诗无达诂”的说法,详细到某一诗词或者句子,不同的阐明,也可以在结合文本语境中,做出好与不好,或者较好与更好的差异性判断。
此外,由柳絮之平均和蜂蝶自乱阵脚的描写比拟,也可以延伸到对这首词整体脉络和主题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和薛宝钗的为人基调深相契合的。虽然《临江仙》这首词,是因结尾的“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而大出其名,但我们常常因此薛宝钗的勃勃野心,来理解这结尾。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我们忽略了,这首词在思维办法上的一个实质特点,便是薛宝钗始终把柳絮这一主体,同外在环境的和谐相处结合在一起。相形之下,林黛玉(包括她的咏絮)时时要突出主体的个性,把环境理解为与主体相冲突的客体。
薛宝钗正由于习气于从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关系中理解两者,以是就会时常考虑如何让主体从外在环境中得到支撑的力量。这样,她借助柳絮与东风的关系,明确表达了要把主体请托给一个明智的外在客体“春天”主导下的“东风”。这种请托的有利,在看似各各自主的群体相处时,比如“蜂团蝶阵”中,更能表示出不乱的上风。这首小词,说个中多少蕴含着作者的人生代价不雅观以及对社会群己关系的理解,未必是一种过度阐明吧?
末了须要解释的是,“诗无达诂”固然有理,但不论何种“诂”,都该当有基本的逻辑自洽。笔者所谓的逻辑自洽,是建立在文本本身该当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认识根本上的。同时,也并不绝对否认有些文本自身,本来就存在断裂的可能以及这种断裂带来的分外意义。不妨试想一下,如果薛宝钗当时填词的水平还不如初学诗的喷鼻香菱,那么写出前后脉络不贯通的作品,反而更为合理。这也不用除另一状况,如果当时薛宝钗的精神正处于崩溃时,逻辑的不自洽,倒是更能深刻揭示其精神天下。美国有学者,剖析莎士比亚名剧《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时,就曾以女主人公临终前一段独白的逻辑断裂,来解释她当时的精神已濒临崩溃。当然,这样的剖析理路,并不适用于《红楼梦》第七十回所着力刻画的一个才思饱满、头脑复苏的人物形象薛宝钗。(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