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姗姗的两本诗集《太阳小时候是个男孩》《玉轮小时候是个女孩》,让我面前一亮,带给我很多惊喜。
首先,李姗姗的童诗有破有立,敢破敢立。她冲破了当代儿童诗的贯有范式,冲破了儿童诗理论框框和规矩,不墨守成规,在艺术上独辟路子,写出了个性。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生猛,还有点我行我素的霸气。
诗历来讲究,“诗言志”。诗,心声也。诗要有诗意,要有诗味,不能太直白,要故意境,要有韵味,否则诗就不叫诗了。
《太阳小时候是个男孩》《玉轮小时候是个女孩》,李姗姗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9月初版,5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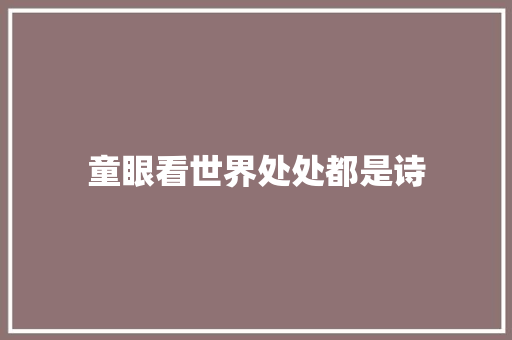
实在别人说的这些诗歌理论都对,我也都懂,但我就不想按你说的去写,我就按我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去写。这便是我从李姗姗这两本诗集中看出的最直接的心意表达,以是就有了《口头禅》这种诗。在一首诗里什么也没写,就写了13个“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可再想想,哪个小孩不是整天嘴里“妈妈、妈妈”一直地叫,一下子也不闲。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东西也叫诗。可是细看看,再诵读几遍,加上不同的标点,有了语气,有了节奏,有了感情,同时就有了活灵巧现的艺术形象。题材范例,表达形象,能说它不是艺术吗?不是诗吗?
还有这首《爸爸第一次做饭》:
菜在哪?盐在哪?勺子在哪?米在哪?醋在哪?盘子在哪?锅在哪?油在哪?碗在哪?我的天,你妈妈在哪儿,叫她快回来。
读着这样的诗,让我想起汉乐府的名句:“江南好采莲,莲叶荷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读她的诗,让我一下子想起很多经典的古诗。再比如唐施肩吾的《诮山中叟》:“老人今年八十几,口中零落残牙齿。天阴伛偻带嗽行,犹向岩前种松子。”最著名的是唐朝贺知章的《还乡偶书》:“幼年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实在都是很直白的生活描摩,但是很生动,很形象,很有意见意义和韵味。
以是,李姗姗的诗有破有立,破的是当代诗风,立的是传统诗意。也便是继续发扬古典儿童诗的传统,用传统诗法去表现当代少年儿童生活。
其次,李姗姗相信“儿童便是最好的墨客”。童言稚语,天真烂漫,童眼看天下,处处都是诗。其一,一些不起眼的,司空见惯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成了诗。
比如《一家人》:
咖啡,可乐,止咳糖浆,是一家人,一个个都长得那么黑。
《烟花》:
从地上,冲到那么高的天上,它们一个个都吓得大叫,怕怕怕怕怕怕---怕——
第二是“想天下”。他们在看天下,同时也在想天下,和我们看到的,想到的不一样。
《担心》:
妈妈,每天那么多挖掘机,挖呀挖,地球还是圆的吗?
《大熊猫》:
大熊猫冲我吐舌头,咔嚓一声,我终于给他拍了一张彩色照片。
第三,不但是看,不但是想,还有自己的情绪、感情的表达。
《爸爸在看新闻》:
爸爸,嗯。阳台上来了一只小鸟,嗯。它在喳喳叫,嗯。它在看我,嗯。它一定想和我做朋友,嗯。我可以摸摸它嘛?嗯。小鸟我来了。谁叫你上去的!
试想如果这首诗把爸爸的心不在焉的6个“嗯”去掉,这首诗也成立,不过那就逊色多了,少了生活情趣。
再次,这两本诗集不但是作者的虔诚记录,题材非常丰富,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态度、情绪。
第一是作者的儿童不雅观:尊重与欣赏。没有对孩子的尊重,就不可能出身这样的诗。每一首小诗都在彰显著一个妈妈对付孩子的欣赏,她以一种美美的、幸福的心态在“秀”她的宝贝。
第二是阳光与爱。可以有很多词来形容这两本诗集的风格:暖暖的,有趣的,愉快的,好玩的——都是妖冶的,阳光残酷的。
第三是警示。不说教不即是没有教诲意义。通过她的诗,让我们走近孩子的天下,走近孩子的内心,让我们更加理解孩子,不武断、不粗暴地打断孩子、干涉孩子的生活,就让孩子们永久保有纯洁与阳光,就像《会飞的大楼》里写的:
推开两扇窗,大楼伸开了翅膀,当我们睡着往后,大楼就会飞行。
帮助孩子们伸开抱负和想象的翅膀,才能让他们在自己的天地自由地飞行。(徐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