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敕令建筑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是唐宋期间连接经济中央(江南地区)与政治中央(北方洛阳、开封),并进一步辐射到全体中国的交通大动脉。而这一期间,又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词创作的繁荣期间,因此,这一期间的诗词创作中,一定会涌现为数不少的反响、描写运河的作品,也一定会有受到运河开凿与通航影响的文学征象的发生。
唐宋诗歌对运河开凿与运行功过很早就给予了关注。运河开凿的紧张决策者是隋炀帝。作为一个曾既壮大、统一又很短命的王朝,隋朝的灭亡与隋炀帝开凿运河有很大关系。因此,反思运河开凿的历史,就不能不联系到隋炀帝。
最早涌现的这类诗歌作品是白居易的《隋堤柳》。在这首作品中,白居易对隋炀帝开凿运河持彻底否定态度。他认为,正是由于隋炀帝开凿汴河(运河)而用之“南幸江都恣佚游”,才使得“海内财力此时竭”,终极“上荒下困势不久”,导致个人身丧江都(扬州),隋朝亡国的结局。
在白居易同时及前后,写这类题材的墨客逐渐增多,涌现了张祜的《隋堤怀古》、李商隐的《隋宫》、胡曾的《汴水》、罗隐的《汴河》等代表作,这些作品对隋炀帝的开河都持否定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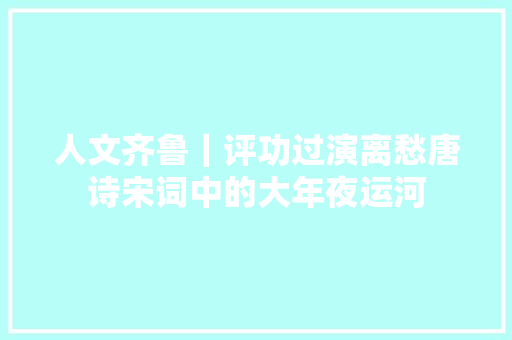
但随着韶光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想熏染到运河的开通对南北经济及文化的互换,对全国的统一和中心集权的掩护有着不可替代的浸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出行带来巨大的便利。
至晚唐,开始有了一分为二的认识与评价。代表作品是皮日休的《汴河怀古》: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诗歌认为,如果没有“水殿龙舟”的荒诞与奢靡,单就开凿运河而言,隋炀帝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这实际上是指出,运河开凿不为过,荒诞嬉游才是过。
随着对运河开凿的认识与评价越来越一分为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人们也就愈来愈能辩证地看待。于是,晚唐还涌现了一首更为新奇的谈论运河开通功过的诗歌作品,即李敬方的《汴河直进船》:
汴水通淮利最多, 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 取尽脂膏是此河。作品认为,运河通航对朝廷是利,对百姓却是害,由于东南地区的“民脂民膏”都是通过这条河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廷的。这种对运河功过利弊的剖析更进了一层,也更加全面。
北宋时,运河的浸染比唐代更为主要,它是南粮北运的最紧张水道。在谈到运河时,宋代墨客就不再只是着眼于写运河本身的功与过,而是完备着眼于现实,就北宋运河的畅通及管理等问题揭橥自己的见地。
这些诗篇中有的主见停罢漕运,如石介的《汴渠》;有的主见不能罢漕运,但朝廷要节俭开支,如梅尧臣的《汴渠》;有的主见其余疏凿秦汉期间通往关中的旧渠,如郑獬的《汴河曲》。
大运河和唐宋期间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人们的仕宦、游历都离不开这条水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运河是唐宋人的一条生命之河,在其上不断展示着唐宋人为生存,为出路,为空想而奔波、奋斗的生理脉动,也不断上演着他们送亲别友的离去图像。
这是条能牵动思乡之愁的河流。如崔颢《晚入汴水》:
昨晚南行楚,目前北泝河。 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 晴景摇津树,东风起棹歌。 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作为开封人的崔颢,一进入运河,离家乡愈近,人的感情也就愉悦起来,连景致都让人觉得到惬意。
这是条引发客愁的河流。如欧阳修的《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
阳城淀里新来雁, 趁伴南飞逐越船。 野岸柳黄霜正白, 五更惊破客愁眠。这是条能给人以精神追求的河流。如孟云卿的《汴河阻风》:
清晨自云牛马形,梁宋挂席之楚荆。出浦风渐恶,傍滩舟欲横。大河喷东注,群动皆窅冥。白雾鱼龙气,苍茫迷所适,危安惧暂宁。信此天地内,孰为身命轻。丈夫苟未达,所向须存诚。前路舍舟去,东南仍晓晴。面对着这滔滔流水,有人会有惆怅与失落意,但也有人会如孟云卿那样,虽已有多次的不快意,但仍能武断信心,矢志不渝地追求下去。在孟云卿看来,人生和自然界一样,有阴就有晴,狂风过后将是风平浪静的美好出路。
这也是条不断消散、消磨人道命的河流。如王安石的《汴水》:
汴水无情昼夜流,不肯为我少淹留。 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 州州人物不相似,处处蝉鸣令客愁。 可怜南北意不就,二十起身今白头。数百年来,这条河上有无法计数的人走过,个中许多人应是多次来回。无论是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杜牧,还是宋代的王安石,他们的觉得是相通的。
这更是一条送别的河流。在这条河上,唐代就曾上演过无数次送亲别友的剧目,也留下大量写离去之情的作品。北宋期间,以许多送别与离去都是发生在开封城外或沿途的运河(紧张是汴河)上。如柳永那首著名的离去词《雨霖铃》,词中所写的送别地点是在汴京都门外的汴河边,其“执手相看泪眼”的送别场合是在汴河上,其“念去去”而登舟远行的路程是延伸向漫漫“楚天”的汴河水。
隋唐大运河故道
因开河而形成的运河水系中的一些河名、地名及干系景点成了唐宋人在创作诗词时常用的文化符号。特殊是隋堤、汴水,成了唐宋诗词中常常提到和描写到的景象或意象。
在宋代,“隋堤”不仅是代称隋朝遗迹,最能代表隋朝特色的文化符号之一,成为评论隋炀帝功过是非的一个聚焦点,“隋堤柳”也不仅仅是一种亡国的象征,更成了人们心目中能展示汴京繁盛景象的主要组成部分。
进而,“隋柳”、“隋堤柳”、“隋堤絮”在唐宋人那里,逐渐成了泛指“柳树”与“柳絮”的代名词。
汴水(汴河)更是诗词中常常利用的景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汴水(汴河)每每成了墨客描写该地景象的主要组成部分;描写和这些城市有关的历史遗迹或人物事宜时,汴水(汴河)也多成了主要的抒怀元素;写到沿运河南归与北上的情景时,汴水(汴河)也成了人们一定要提到的景象。
到了南宋,汴水(汴河)更成了沦陷金人之手的汴京故都的象征,如朱敦儒的《浪淘沙》:
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在朱敦儒的心中,东流不尽的汴水是他对故都最难忘怀的范例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