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诗词的境界
文|张凤军
关于诗词,古往今来论述者很多。锺嵘认为,诗歌的产生缘于“摇荡脾气”,必须具有“感荡心灵”的效果;袁枚认为,脾气是诗歌的第一要素,“脾气之外本无诗”;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对诗词的批驳进行了阐发。下面,我着重从诗词的创作过程来谈谈诗词的境界:
一、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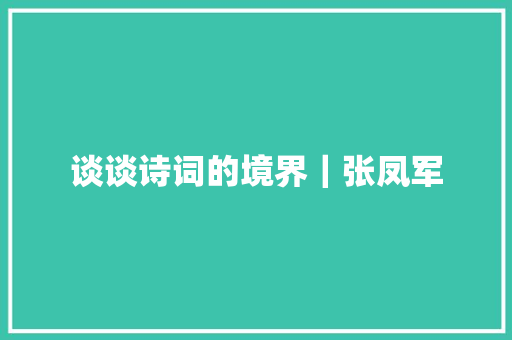
便是佛家讲的坐禅。这一过程,诗词不雅观还没有形成,紧张学习节制诗词基本知识,打牢创作根本。正如贾岛的诗句,“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我不雅观当代诗词创作军队,大多都处于这个阶段,反思自己应该也是。《小楼听雨》诗词平台聚拢了许多诗词名家,每天我都在这里熬炼诗词功夫。记得前几天,自己回顾半生军旅,偶得“吉林河北到京城”句,遂行绝句:吉林河北到京城,立业安家用半生/今看杨花忽喟叹,我原故土一漂蓬。后来,叶子湖畔老师建议把起句放在结尾,我感到很道理,末了诗改成:故宅流落一身轻,立业安家用半生/今看杨花忽喟叹,吉林河北到京城(《乡思》)。虽算不得好诗,但诗境得到很大提高。
二、达境
便是佛家讲的通达。这一过程,诗词的创作方法已经闇练节制,重点是涵养情操、涤荡胸襟。正如陆游的诗句,“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当代诗词名家,大多应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小楼听雨”的王志伟老师,善于创作绝句,节制了绝句的各种葵花宝典。对他来说,写一首不错的诗已经很随意马虎了。每次打仗,我都能感想熏染到他在存心打造佳构,每每有好句见诸群里,他一有韶光也很热心帮助大家熬炼诗句。我记得他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句子:老牛驮上毛毛雨,走进烟村落水墨中。(王志伟《江南春日(新韵)》)/听到夜深皆散去,街头唯剩曲中人(王志伟《临窗,听流浪艺人拉琴有题》)。当然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
三、喷鼻香境
便是佛家讲的清闲。这一过程,诗词创作已进入大成之境,重点是常不雅观自我、感想熏染自然。正如夏元鼎的诗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从当下诗词创作军队来看,百万人中不敷二、三,杨逸明老师应该位列个中。平时,学习杨老的诗词文章很多,他的好诗好句和诗词理论对我启示很大。记得张金英老师的《21世纪诗体八家试论》,专门论述了杨逸明老师的“晚风体”。“每到人间波折处,满崖都是放歌声”/“何妨也学寒冬样,做个删繁就简人”/“不将生命磨成墨,几个真能写出诗”,常常阅读当代诗词的读者,对这些诗句该当很熟习。没错,这些都是杨逸明老师的金句,你从中能否体会诗词的大成之境?
张凤军 笔名飞雪红英,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世纪文化艺术社秘书长。从军三十余载,尤爱“楼船夜雪、铁马秋风”的铮铮诗骨,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诗词中国》《红叶》《解放军报》和中心军委机关网等多家报刊媒体,偶有获奖。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正/冯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