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如洗,洒落在雕梁画栋之间,映照出一幅幅绮丽而梦幻的画卷。
这是属于女子的时期,她们以曼妙的身姿,轻盈的步伐。
穿梭于繁华与寂寞之间,留下了一串串或深或浅的足迹,也在无数文人墨客的笔下,绽放成永恒的芳华。
“云想衣裳花想容,东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笔下的女子,犹如天边最残酷的云霞,又似春日里最娇艳的花朵,让民气生神往,却又遥不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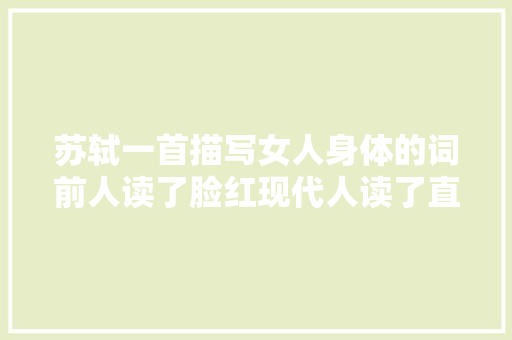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白居易的这句诗,则将女子的回眸一笑描述得淋漓尽致,那一刻的倾城之姿,足以让世间万物黯然失落色;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韦庄的笔下,女子之美,更在于那份温婉与纯净,犹如月下安谧的清泉,清冷而又动人。
苏轼,他的诗词中,不乏对女性之美的赞颂,但那份赞颂,却每每超越了时期的束缚,触及了人性的深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骚人物。”这是他的豪迈,但“十年死活两茫茫,不斟酌,自难忘。”则展现了他深情而细腻的一壁。
在苏轼的诗词里,女性之美,不仅仅是外在的容颜与身姿,更是那份内在的坚韧与柔情。
然而,提及苏轼那首《菩萨蛮·咏足》,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这首词,以女子的足为题材,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女性身体美的独特欣赏,却也因其直白的描述。
让古人读来不禁酡颜心跳,而当代人则可能因时期的变迁,对个中的“恶趣”有所责怪。
涂喷鼻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宋·苏轼《菩萨蛮.咏足》
“涂喷鼻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开篇两句,苏轼便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女子足部的俏丽与宝贵。
这里的“涂喷鼻香”,是女子为了保持双足的芬芳而涂抹的喷鼻香料。
而“莲承步”,则因此莲花来比喻女子行走时的轻盈与优雅。
接下来的“长愁罗袜凌波去”,更是借用了曹植《洛神赋》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典故,表达了词人对女子足步之美的无限留恋与惋惜。
“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这两句,进一步描述了女子在舞动时,双足仿佛与风共舞,轻盈得险些看不见行走的痕迹。
这种超乎平凡的轻盈与灵动,不仅展现了女子身体的柔美与力量,也寓含了词人对美好事物易逝的感慨。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裹足所带来的痛楚。
这里,“偷穿宫样”暗示了女子对美的追求与模拟。
而“并立双趺困”则暗想换穿宫廷贵妇人的鞋,得当是得当的,便是没办法并脚站立,更没办法走路。
宋代残酷的裹足审美,是很多古代女子生平的痛。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结尾两句,是词人对女子足部之美的极致赞颂。
在他看来,这种纤妙之美,难以用言语尽述,唯有亲手触摸,方能体会个中的奥妙与韵味。
彼时人们认为脚缠的越小越“纤妙”。
而“须从掌上看”既是表达了苏轼对缠脚陋习的批驳,但是基于文化的局限性,又是对这双“纤妙”小脚的喜好。
在历史的尘埃中,我们总能找到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它们或哀怨,或坚韧,或温顺,都是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苏轼的这首《菩萨蛮·咏足》,或许正是这样一声被遗忘的呼唤,它让我们在欣赏女性身体之美的同时,也不忘思考那些隐蔽在俏丽背后的悲苦与挣扎。
蒋勋老师有说过:“去世去的叫苏轼,活过来的才叫苏东坡”。
苏轼生平针砭时势,驳斥权贵,几经遭贬,踏遍尘凡,始终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