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中的法布尔。
《昆虫记》不仅是一部昆虫学的科普著作,也是法布尔对付生命的追忆、记录和沉思。其主角有昆虫和植物,还有守在寂寞的荒石园,生平都浸淫昆虫天下的法布尔:从贫寒却好奇的童年,到执着却酸楚的中年,再到沉静却依然激情亲切的老年。
法布尔将心力投注在昆虫研究上,他乃至认为,若没有昆虫的陪伴,自己绝不可能挨过人生的起伏与悲痛。他像一位墨客,用拟人化的笔触讲述昆虫的故事,同时表达自己五味杂陈的人生感悟。因此他既被称为大博物学家,又被称为大文学家,并在1910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1925年往后,《昆虫记》几次再三以选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如今它在中文图书市场上是有名的儿童读物,每到寒暑假都会被一些中小学列为必读书籍推举给学生。名为《昆虫记》的书数不胜数,每一本在将原作中的哪些昆虫选入个中上都有细微不同。还有些版本只把它当成纯粹先容昆虫的科普书,删除了里面与昆虫无关的笔墨,但这种打薄式做法很可能伤及其文学性,令对昆虫并不理解的读者没有兴致打开它。还有的版本加入了语文传授教化式的解读,令其看上去更像一本语文阅读理解题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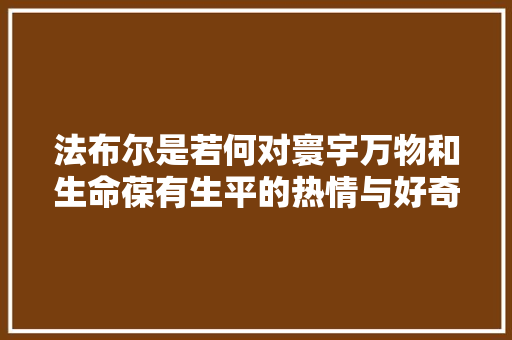
《我的〈昆虫记〉:基于法布尔的重述》,马俊江 编译,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6月版。适读年事:12+
在马俊江的书中,他修正了原作中较为冗长的段落,让它读起来更轻松有趣,也在编译中将自己的一些感想融入原作。虽然是按照原作的顺序编译,但他也将法布尔在原作的十卷中相同的话题进行了归纳整理(法布尔从56岁完成第一卷到84岁写完第十卷,《昆虫记》的写作韶光持续几十年,有些相同的话题散落在十卷的不同地方)。原作的章节很多,在选编时马俊江选择了为人所知的昆虫和文学性与思想性更强的篇章,使读者更能理解法布尔是如何对天地万物和生命葆有生平的激情亲切与好奇的。
下文是这本书的书评,作者把它推举给了刚刚结束中考的儿子。她说,读书这件事像在沙滩上寻宝,在数不清的细沙里捡出一个又一个宝贝,马俊江老师则做得更多一些,他把宝贝草蛇灰线串起来,把一个神完气足的法布尔和妙趣横生的昆虫天下呈现在我们面前。
撰文 | 黎亮
掩卷闭目,
那些被照亮的时候依次闪过
这本书带给我的惊奇喜悦真不少。比如,当法布尔提及大蓟那“蓝色海胆一样的,不起眼的蓝色小花”,我回忆起在封控中创造家门前长出一朵不起眼的小花,按名搜图果真便是大蓟,原来小小的象鼻虫就住在那小小的花托里!
生命的赐予神秘丰硕,不经意就有回响。前阵子驱车去看萤火虫,小朋友捉捉放放,大人拿脱手机拍照录像,也算心满意足。不久便收到《我的〈昆虫记〉》,序言读过看目录,第一篇是《圣甲虫和它的粪球》,末了一篇是《萤火虫》,此中有何真意?一眼瞥见小引开篇“和生命一样,一本好书该当从春天开始,结束的时候,要有光”——很像一句赠予读者的咒语啊。脑波也随着荡漾了。
《我的〈昆虫记〉》目录。
在春天的原野里推着粪球的食粪虫,“闪烁着青铜、黄铜般的光芒,还有祖母绿和紫水晶的光泽”,在法国记录片《小宇宙》里看到过,导演拍出了法布尔眼中俏丽发光的小虫。
“萤火虫的光宁静、柔和,像从玉轮上掉落的小火花”,但我怎么也想不到,萤火虫是食肉昆虫,居然吃蜗牛。捕猎用的是麻醉术,干净利落,风过无痕:两片钩状颚在蜗牛壳上轻轻一夹,把毒液注入蜗牛体内,蜗牛立即安静下来。独乐不如众乐,萤火虫呼朋引伴,一起啜饮肉汁,吃完了,蜗牛的空壳还留在它最初被攻击的地方。月光般柔和,刺客般迅捷,这是我所不知道的萤火虫。法布尔在萤火虫母亲的肚子里瞥见了发光的卵,他说“萤火虫的生平是有光的生平。从生下来到去世去,它们的灯始终亮着,不熄灭”。
读罢末了一篇,再从头读,经由去芜存菁的《昆虫记》,每一篇都令人精神愉悦。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提到,高明的编者,一次标点符号的重排,也会拥有化腐烂为神奇的效果。我无心比较《我的〈昆虫记〉》与原版以及浩瀚删节改编的选本之间有何不同,但阅读体验老实不欺,这本书有光,掩卷闭目,那些被照亮的时候依次闪过。
《我的〈昆虫记〉》实拍图。
首先看到的是孤寂的小孩法布尔。在祖父母居住的荒野,在一群牛、羊、鹅中间,小法布尔闭上了眼,阳光消逝了。他正在做人生中第一个突发奇想的实验,他睁开了眼,阳光再次迎面而来。他创造了眼睛的功能,却受到家人的嘲笑——“他们都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事”。这件小事的正反两面同样主要。从此,未来的昆虫学家开始真正看天下,在人们习焉不察的平凡之处,他将一次又一次叩响宇宙生命的大问题,让万物开口讲自己的故事。
第二道光来自樱桃树。法布尔在樱桃树身上看到了生命的炼金术。“白色的樱桃花像雪一样开着,落着……”多美啊!
樱桃红了,麻雀翠雀和黄鹂鸟叽叽喳喳,各种长翅膀的小虫翩翩起舞,那些没长翅膀的小虫也来分享美味,一个个都吃饱醉倒,在叶子下睡着了。到了夜里,田鼠把蚂蚁鼻涕虫吃剩下的果核搬走,冬天来了,它们在果核上钻个洞吃里面的果仁。
树下的法布尔,问出了两个问题——如果所有的果子都无缺,所有的种子都抽芽,它们全都长成了树,地球将会若何?一棵树老了,要让它的孩子长成大树,只须要一粒种子,为什么樱桃树每年都要结满一树果子?
满树的樱桃果和种子,绝大部分都另有义务——那便是养活别的生命。在利他的冲动中,法布尔带着我连续向前,指给我看造物的安排:泥土养育了青草,蝗虫吃青草,螳螂吃蝗虫,蚂蚁吃蝗虫的卵,蚁䴕伸出大舌头,就卷下黑压压一群蚂蚁……而我们人类,把蚁䴕做成了喷鼻香喷喷的烤肉。不便是食品链吗?
绘本《最美的法布尔昆虫记》插图,[日] 小林清之介 著,[日] 松冈达英 等 绘。(图源:爱心树)
对付食品链,人类还能若何?法布尔的认知总是贴近人的觉醒,他说“螳螂、蝗虫、蚂蚁,还有更小的昆虫,它们通过繁芜弯曲的路子,都给我们的思想之灯添了一滴油。它们的能量,一代一代逐步加工、积蓄、通报,终极注入我们的血管,滋养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生命的炼金术,炼出了人类的大脑。法布尔不愿辜负如此来之不易的赠送,终其生平不雅观察探究寻求精神知足,贫贱不移,乐在个中。
第三道光,要从蜘蛛网提及。法布尔在蛛网中瞥见了对数螺旋曲线,一个无限靠近却永不抵达极点的旋转。他看着蛛网上的扇面和平行线,惊叹它们的有序与和谐,还说几何学教会他简洁地写作。
法布尔彷佛对统统人类精神活动都表现出好奇与激情亲切。他身上有种浪漫特质,在昆虫天下创造的诗与美,在数学的天下里他也能悟到。他随着同事学几何,评论辩论数字与艺术相接的幽美,被同事贬为“无稽之谈”。但他坚信他这么做是“在精神天下里点燃思想的炉火”,坚信“让那些抽象的公式充满人生的阳光”无比美妙。在《从蛛网几何学说到我的数学往事》这篇故事里,法布尔写道:
“做了十五个月的解析几何练习之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蒙彼利埃大学的考试。于是,在文学学位之外,我又得了一个数学学位。文凭是我差错学习的终点,他精疲力竭,再也不想连续学解析几何这些劳什子了。而那张文凭却只是我的开始。”
诗意的召唤和阳光下的漫游,让他在光阴隧道里走得越远越有滋味。他评论辩论起每一只小虫,都像在引领读者做“精神的闲步”。
法国记录片《小宇宙:微不雅观天下》(1996)画面。
发自内心的热爱带来了“十万个为什么”
读法布尔的日子,瞥见路边小花花心里爬着一只小虫,像清风送来——这只我不认得的小虫会对法布尔讲故事。
“如果我们长于讯问,它就会给我们讲述它的故事。”法布尔如是说。他教会我对眇小的生命发问:你吃什么?食谱会变吗?你在哪里居住?如何筑巢?若何捕猎?如何战斗?又若何找到回家的路?如果用石头挡,用报纸盖,用水冲掉路上的气味,总是原路返家的蚂蚁还能回家吗?人类在地球上修建房屋之前,爱在屋内筑巢的长腹蜂住在哪里?苍蝇啊,物质如何聚拢,又如何得到生命?物质的生命结束,是如何分解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带来了十万个为什么,法布尔不雅观察、提问、设计实验,教我们不要以讹传讹,不做应声虫,自知无知而求知。
在《蝉和蚂蚁的寓言故事》这一章,法布尔回嘴了伊索寓言和拉封丹寓言,让读者理解故事与事实的差异。
这只圣甲虫在帮另一只圣甲虫推粪球?不不不,它是在抢劫。蝉向蚂蚁借粮?活生生的蝉就在伊索身边,他没有负责去理解。事实正相反,蝉对蚂蚁无所求,倒是蚂蚁抢了蝉在树枝上开掘出来的水。蝗虫吃庄稼,只管消灭光?千万别为了保护几只李子,打乱全体宇宙的秩序。要知道,吃庄稼的蝗虫,也给人类送上了美味的火鸡。寄生虫好吃
在一个讲教诲的短视频里,一位中科院毕业的硕士提及她为什么没有连续读博做科研。她说,她创造自己对研究工具并不热爱。她有个同学才是真的爱,后来果真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她那位同学,看着显微镜下的细菌,亲切地喊它们“亲爱的小可爱”。真正的喜好藏不住,人做着喜好的事,一言一行都会流露出生命的欢欣。读《我的〈昆虫记〉》,这样的欢欣会传染——
“欢快的法布尔带着几个孩子走上高原,他们要去和天地万物一起庆祝生命的复苏”;“不管是蝗虫的琴声,还是雨蛙的风笛,或者蝉的铙钹,在我看来,都是为了表达生命的欢快而奏响。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表达生命欢快的办法”;“蟋蟀有不幸的家庭生活,但便是那样的家庭,延续着蟋蟀种族的生命,延续着野外草丛间动人的歌唱”;“生命,彷佛便是步步危险,能存活下来便是幸运。而千辛万苦幸存下来的若虫在阴郁的地下生存了那么多年,当它来到阳光下的时候,生命已靠近了尾声。但这更增加了阳光里生命的宝贵,这‘生命的锦缎’多么值得歌唱啊”;“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歌,但歌声都是一样的,庆祝着生命的欢快”……
万物都唱同一首歌,生命的欢歌也在法布尔心中回响,我听着这回响的回响,记下他在黑夜中写的话:“科学,不是阳光,是我手里阴暗的灯笼。”法布尔是独一无二的法布尔,人类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类。阳光下歌唱,黑夜里提灯,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值得每个人拥有。法布尔指给我们看灯光照亮的部分,也提醒我们阴郁更为浩瀚,“我们依然被阴郁里的未知事物包围着。我们这些被好奇心和求知欲引诱的人,能提着灯笼东走走西看看,驱散一点阴郁,能多瞥见一点本来隐蔽在阴郁里的事物,就很快乐知足了”。如此快乐这般知足,值得每个人拥有。
科学研究与有我之境
《我的〈昆虫记〉》的编者马俊江说:“那些只看到昆虫的读者忘却了,记下这些昆虫故事的是人,而人的天下里怎么可能只有昆虫!
”他让我们把稳法布尔“浸淫昆虫天下的生平:从贫寒却好奇的童年,到执着却酸楚的中年,再到沉静却依旧激情亲切的老年,所有他经历的热爱的统统”。
法布尔用激情亲切探索和鞠问慎思轻轻弹走了贫穷和孤独蒙在命运之上的灰尘,过出了饶有生趣的俏美人生。他的昆虫记既是科学,也是文学,能见到科学的方法和创造,也能见到作者的生活与精神。科学和文学领悟无间,或许是由于法布尔不雅观察虫子也不忘与人类天下呼应,与生命意识关联。
绘本《最美的法布尔昆虫记》插图。
食粪虫推粪球能有多奇异?法布尔展开了历史想象:在尼罗河边弯腰劳作的古埃及农人,第一次撞见这个场景一定木鸡之呆。他们不雅观察这只小虫,传说不翼而飞——食粪虫把粪球埋在地下二十八天,月缺月圆回到最初也是二十八天,在新天下出身的第二十九天,食粪虫回来,挖出粪球扔到尼罗河中。多么了不起,这只推粪球的小虫与天地精神往来,开启了一个新生命的循环。因此埃及人授予食粪虫至高无上的光彩,称它为“圣甲虫”。法布尔看待传说像演习有素的人类学家,在那些荒诞不经真假殽杂的言说中,他看到了“人类崇高的心灵和诚挚的崇奉”,即“对天地有所迷惑,但也有所敬畏”。
一只被人带到远处小屋的石蜂从窗户飞走,飞回了蜂巢,能有多么激动民气?法布尔说它是“昆虫中的奥德修斯”,做了许多实验来证明,放黑盒子也好,往反方向走再折回目的地也好,被迁徙改变的盒子弄晕了也好,石蜂总能飞过大片麦田和玫瑰红的野外回到自己的蜂巢。回家的奥德修斯,是否和回家的石蜂一样,也受到某种神秘而强大的本能召唤呢?
法布尔对自己的探究领域有非常清晰的定位——“我做的统统便是向昆虫发问——生命的本能到底是什么?”在科学研究之上,法布尔赞颂本能的伟大,也唏嘘受缚于本能的悲哀。
切叶蜂会在现成的隧道或其它蜂类留下的旧巢里做窝,它把树叶切下做成正方体的小盒子,把它们一个个连在一起,在里面装花蜜生宝宝。在蚯蚓钻出来的隧道里,它用叶子堵住可能带来危险的通道。在生命即将闭幕时,它已经完成了生平该做的事——宝宝已经终年夜,屋子依然坚固,无需再造叶子防御工程,它就要告别这个天下。意味深长的怪事发生了,它开始毫无必要的事情,一直地用叶子砌墙,“唯一的目的便是用它爱了一辈子的叶子添补生命的末了阶段”。
粪蜣螂则用惊人的母爱呵护蜣螂宝宝,她放弃了统统乐趣,守在卵宝宝安睡的粪蛋边,一刻不歇地劳碌着,整整四个月,什么也不吃。匆匆狭的法布尔在别家的粪蛋上挖开一道口子,扔给蜣螂妈妈,她总是不辞费力把粪蛋补好。不管塞给她多少,不管重复多少遍,蜣螂妈妈守护修补粪蛋,从不懈怠。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是,它只是分不清孩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绘本《最美的法布尔昆虫记》插图。
昆虫只拥有在特定时候做特定事情的本能。泥蜂拥有精准的麻醉术,天牛幼虫为成虫钻出树干事先准备好统统,红蚂蚁能记住只走过一次的繁芜道路……令我们不得不惊叹造物的神奇,可是,若把狼蛛从浅浅的洞穴搬出来,它便不再挖洞,不会造塔,没了洞口的小塔,它不会捕猎,只能活活饿去世;若取下长腹蜂的蜂巢,墙上只剩轮廓,长腹蜂依然会衔着泥巴,乐此不疲地修补不复存在的蜂巢……
对此,法布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论断:“它们的全体生命只是实行本能,而不会理性地思考,也不会对本能做出调度。无论发生什么,天下有若何的改变,它们只是无意识地、机器地、按部就班地实行本能规定好的程序。就像一台水磨,一旦轮子被发动起来,就再也无法停滞旋转,纵然没有稻谷,它也旋转着,坚持着一项没故意义的事情,一贯到它报废,再也无法迁徙改变的时候。”
人类则拥有理性,会学习,懂教诲。书写昆虫,法布尔也回答了人的终极问题——“我是谁”。他认为,本能的领域是有限的,小虫子拥有的仅仅是浩渺空间中的一棵草,人类的聪慧却可以延伸到全体宇宙。我们可以听,可以看,可以言说我们心中所想。
可是,法布尔啊,你瞥见松毛虫总是首尾相接,列队出行,它们口吐丝线,标出走过的路,不管走多远,总能回到松毛虫的家。你制造了意外,在它们爬上花盆时截断了它们身后的丝线,造成一个闭环的怪圈。你想知道它们能不能走出来。整整五天,围成大圈的虫子在花盆圆口上走啊走,疲倦,饥饿,被寒夜冻僵。军队多次陷入停顿断裂,有几只走出圈开辟新路,终归不果,返回旧路。
你说它们盲从,注定走不出怪圈。你说“如果没有极度疲倦引起的停顿和军队断裂,如果没有轨道之外的几根丝线”,它们会在走不出的怪圈上冻去世饿去世。你把它们的走出归功于有时,好吧,我和你一样为“走不出怪圈”而嗟叹,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光彩有时带来的不愿定,赞颂为在绝境中求生而首创的道路呢?
难道说人类就没有走不出的怪圈吗?一个人可以拥有理性,那么一群人呢?人类全体真的比虫子更理性更自由?
绘本《最美的法布尔昆虫记》插图。
“热爱天地万物的人,
血脉里都有神圣的火种在燃烧”
人到中年,法布尔终于拥有了一座他朝思暮想的荒石园。废墟中一堵断墙,在他看来像是“艰辛的生活和命运也未能打败的热爱”。多年往后,上了岁数的法布尔,仍旧有滋有味,感想熏染到求知的热望。一位老人,捉着虫子,好奇、愉快、兴致勃勃,天下宛如初见……如此幸运,大概都源于他生平屈服发自内心的热爱。
法布尔在荒石园的研究室。
年少时为了谋生去求学,法布尔一度放下钟情的博物学。大概是命运的安排,他碰着不少启迪和引领他的学者。一位激情亲切欢畅的植物学家对他说——“去研究虫子和植物吧!
如果你确实像你表现的那样,对付植物和虫子,血管里有无限的热心,就不必担心将来没人谛听你讲述它们的故事”。法布尔认识到自己的天赋与定命,认识到人不是“听凭风吹雨打的薄弱麦秸”,遂决定“把生命献给真正热爱的东西”,让自己达至“平凡之上的高峰”。
他迫在眉睫地求知,身处困难内心笃定。为填补知识构造的毛病自学代数,像蜘蛛织网一样不知放弃。深奥的知识天下像坚固的岩石,只对不惧失落败的勇者打开。他一遍又一遍敲击岩石,探求进入的门径,支持他的是内心的低语:“岩石上的大门很难打开,但一旦打开,我就能听见真理悦耳的声音”。有时候,居然考试测验自认为注定失落败的实验,没有信心,也没有激情亲切,但便是想考试测验——这是什么样的神灵在主宰?结果预想失落败的实验却大得胜利。
触及心灵的美,洞见天下的真,让名利变得不主要。腰酸腿疼,口干舌燥,头痛欲裂,法布尔浑不在乎,只因心中别有天地。他写下《昆虫记》,分享昆虫的故事,也分享岁月赠与他的快乐。他谈起杜福尔的书在漫长的冬夜点燃了他的生命,也希冀他的故事能让读者鼓起勇气去学习和探索。而我,怀着对儿子的爱,记录下我与这本书的相遇。愿有书为伴,岁月赠与你快乐。
荒石园,现为法布尔博物馆。
撰文/黎亮
编辑/申婵
校正/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