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政
我干生产队长实属有时。
下乡那年,我干小队司帐。到了第二年麦收前,我们生产小队的生产队长撂了挑子。不管公社、大队领导如何做事情,如何说破天,这个老牛筋铁了心的不干。就算摘除他党员的帽子,把他打成反革命,他也不干。用他的话说,“俺再干,俺的孙子就没腚眼了!
”
大队、公社无奈,就目撒新的生产队长。结果我就成了眼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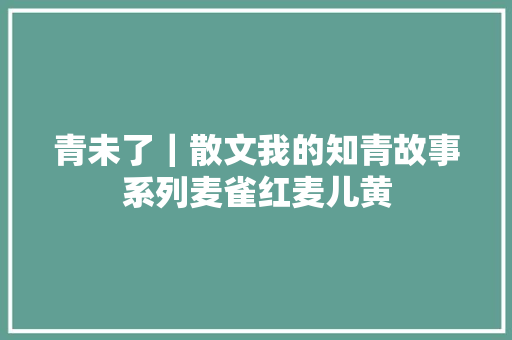
那天晚上,初夏的风儿暖暖悠悠,月儿早早地就出来了,那样的圆,那样的亮。
大队初司帐住我们知青点西邻。他隔着墙头吆喝我:“小毕!
于主任叫你下黑客岁夜队部!
”
“知道么事儿吗?”
我端着饭碗回问。
“不知道!
”
隔墙回答的很干脆。
我立时蹲下急急扒拉碗里的稀粥。
那天晚上遇上我民兵看粮库。我背着大杆枪,走过村落中央广场,远远就瞥见大队部亮着灯光。我踩着淡淡的月光,来到大队部门前,忽地有两个黑影窜到我的面前。我知道这是民兵连养的那两条狼狗大虎二虎。我把手中的地瓜扔了过去,大虎二虎就相互撕咬起来。大虎二虎是民兵连长抱养的,他是在老虎窝部队讨得这两只狗。民兵连长抱来家时,还是两只狗崽子,虽然是有些淳厚,但是出身却是有些正宗,是隧道军犬。连长把大虎二虎抱来家时,它们还小,还不能吃食,得喂奶,连长就逼着他老婆给狗吃奶。连长的儿子虎子猛地添了这两个狗弟弟,那奶水就不足。连长老婆无奈,就叫大虎二虎去咂猪奶子。猪圈里的老母猪对这突来的猪崽子很是陌生,就用鼻子去拱它们。连长老婆就把猪尿涂在大虎二虎身上,老母猪这才不去拱它们了,而且很是惬意地眯缝着眼睛,把个身子神得老长。就这样,大虎二虎在猪圈里终年夜了,和那些猪弟猪妹们玩得很愉快,冒死地抢着猪食吃。大虎二虎好喂,这是村落人共知的。可是,大虎二虎的确不像它们的同类那样吃屎。于是村落人就挑大拇指赞声:“好狗!
”
好狗该当不咬道,他奶奶的,大虎二虎便是咬道!
我常得备好地瓜准备着,要不那个凶劲儿,我的头发梢都发麻。
我重重地咳嗽一声,目的便是叫屋里的人引起重视。实在,我这是多此一举,大虎二虎的狂叫,屋里的人肯定就知道有人来了。这咳嗽是我的毛病,也可以说是一种生理胆怯的表现。用大春的话说,我这是“探雷器”。我也不知道我是在探测什么,胆怯什么,反正只假如进办公室,不管是多大的办公室,我都要犯这个毛病。大春还说,“你这是自卑!
”
是不是自卑不知道,反正是进门都要犹豫一阵子,心里茫茫的一片,或是芦苇,或是乱草!
我又咳嗽了一声,并轻轻地敲下门。
“门没关,进来吧!
”
屋里传来粗重的声音。
我推门而入,大队革委会于主任和大队妇女主任相对冲着罩子灯坐着。我创造他们俩人的脸都是红晕落面。我看眼罩子灯,心忖:“该是这灯火把他们烤的吧?”
“小毕,坐!
”
于主任的声言变了调,有些颤音。
我把一个腚尖坐在椅子上,就显适合心翼翼。于主任把一支葵花喷鼻香烟扔给了我,我惊诧地双手接过,很有些受宠若惊。虽然那只是一支劣价的喷鼻香烟,那可是于主任给的,大敬意呀。
我趴在罩子灯上把喷鼻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两口,就喷出一团浓浓的白烟,我分明创造,妇女主任的脸腮微微跳动了几下,显然是有些生气,由于我进门来她一贯是绷着脸。
“主任,是你找我?”
我创造我的声音竟然不是胆怯的,由于那话出口溜达。
“嗯哪。”
于主任吐出的那团白烟比我的又浓又圆,许久没有散开,就那样滚动着向上走去。我瞥见他的耳朵眼里还冒出两股烟。
“弄么个?”
我问,这会儿椅子坐的踏实了,由于我瞥见于主任他在朝我笑。
“你到咱村落来干的不错,人也诚笃虔诚。”
于主任说着,又对着罩子灯去吸烟,结果把个灯熄灭了,屋里顿时黑了,我急忙刺开手电,那光柱直刺于主任的脸,那脸上就青光四射,很是森人,妇女主任竟然打了一个哈欠。
妇女主任擦着洋火,点着罩子灯,于主任把手中那半截喷鼻香烟扔在桌子上。
“这烟,跟不上这个!
”
于主任亮亮手中的长烟袋说。
我看着他装好烟,妇女主任扯块报纸的边沿,卷了一个筷子样的细筒筒,伸进罩子灯里点燃,给于主任点燃烟袋锅。
“主任,你刚才说的么个?”
我只管听了于主任说的话,我还是不眨眼地盯着他的眼睛看,我分明以为他的话里还有很多话。
于主任只顾吸烟,竟然是抽的那么有滋有味。
“主任他说要你干九队的生产队长。”
妇女主任接过话,笑着对我说。
我好是五雷轰顶,挨炸弹地蹦了起来,惊咻咻地问:“说么!
要我干队长?!
”
于主任很是微笑地点了点头。
“玩笑!
”
“这能玩笑吗?”
“便是玩笑!
”
“这笑在哪儿?”
“笑在我不懂队长。”
“说你懂你就懂不懂也懂!
”
“这不是说顺口溜的事儿。”
“那是么事儿?”
“二百多口人用饭的事儿。”
“不为了用饭还不找你呢!
”
“我哪能管得起他们用饭!
我下乡插队还不到一年,农活还是二把刀。”
我争辩说。
“庄稼活也不是两篇文章三篇诗,你诗都能写那么多篇,这队长还不能干?”
于主任显然是在野蛮无理。
“我是接管再教诲的知青!
”
我的声音高了八度。
“已经两年了,接管的差不多了。看你现在多庄稼。”
于主任说着,手中的烟袋竿高下指示着我。
“我庄稼吗?”我四下看了自己,没以为自己庄稼在哪儿,只是那件小大衣补丁多点而已。比起于主任那件青棉袄,还洋气了许多。
“我看不出来。”
我回敬了一句,于主任又去抽他的烟。
我真有转身走的意思。
“这个队长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这是公社党委果见地!
”
于主任把烟袋锅朝鞋底磕了磕,语气武断地森人,那两点豆眉高下跳动的很是厉害。我看到他的腮肉都在跳。
“主任,你,你们这不是赶着鸭巴子上轿吗?我能干队长,那西南河的鸭巴子也能干队长!
”
于主任脸腮上的肉不跳了,那对豆眉也耷拉到了原位。他怔怔地看着我,显然是没弄懂我说的话意。
好一下子,于主任侧头问妇女主任:“他说的么个儿?”
“彷佛是他还不想干队长。”
妇女主任一脸讯问地看着我,有些迟疑地回答于主任。
“你要想入党就得干!
”
溘然间,于主任就冒出这样一句很原则的话把我定住了。我感到此时的心在忽悠忽悠的逛荡,像是要离了位子。在那个时期,对付入党,那可是每个青年梦寐以求的大事儿。倒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入党做官,那时入党的动机绝对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于是,我开始反省自己: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你?就看他能不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我干队长九队的社员能赞许吗?”
“你不用担心,公社调查组已经对社员摸底了,他们一贯保举你干队长。”走进来的公社党委尹布告说。
我们急忙起身让座,尹布告在于主任坐过的椅子上坐下。
到了此时,我不好再推辞了,我斯艾地说:“我,我想还是搞个民选,我要全队社员来选,他们选了我我就干!
”
“你下决心了!
”
尹布告追问一句。
那感情很是严明。
“说话算话?”
于主任也紧跟一句,那感情很是欢畅,仿佛是当年在朝鲜沙场,捉了一个鬼子舌头。
真的就开九队全体社员会议,为的便是选队长。在那个时期的屯子,这种做法是很少的,村落里的大小干部多是上级指定和委派的。
选队长那天,天下着小雨,从早上开开门就下,淅淅沥沥的没有间断的意思。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彷佛吸足了水的棉纱,攥在手里就会嗱出水来。
不知为啥,我顶草鸡这种景象,我的脑袋很大,仿佛戴了一顶很沉重的铁帽子,压得头生疼。那感情是心烦意乱的。心里彷佛被塞进一团乱草,刺囊的难熬痛苦,憋得要命,切实其实就有点在鬼门关前挣扎,活不出来去世不明晰。
选举是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在场,大队贫协主任主持。这种选队长的办法是水道村落开天辟地的。
三抽桌上放了两只大海碗,阁下放了一只条笸箩,笸箩里放了许多黄豆,大海网上贴了一张红纸条,条子上写了候选人的名字。我看了欣喜,原来挨选的不但是我自己,我肯定是陪忖。我那悬起的心放回了肚子,心里的那团乱草也瞬间荡然的无影无踪。我环视大伙儿,无论男女老少都是正襟而坐,样子容貌又是那么严明的风趣严明的可笑。
于主任公布了选举的规则,他的那种正经事儿又显露出来,你看他说的话,是不正儿八经?
“选队长不是粑粑麦子的问题,他关系到大伙儿吃粑粑麦子的问题,大伙儿一定要碾砣压碾盘石打石,选错了你们就没有粑粑麦子吃!
”
于主任说这话时不是那么口吃。我突地创造,从昨天于主任同我发言到本日,他就没有口吃过,由于全牟平县都知道,于主任是个结巴。记得,那年我们一起出席地区屯子事情会议时,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上午,这么说吧,一个五个首先他就做了半个小时,这里我学学他当时的场景:
他举着毛主席语录说:“首,首,首,啊,首首首,先先,先先……”结果是一跺脚狠声说了:“首先!
”
那劲儿谁看了都为他难熬痛苦。
地委朱布告提醒他说:“老于呀,你就唱吧。”
于是,于主任他就唱。别说,他还真能,他把我给他准备好了的稿子,扔到一边,就那么唱出互换履历。
“各位听了。”
这句道白也是唱出来的。
“牟平县有个水道村落,
它是牟平的大村落队。
东西南北四座桥,
两条河流串村落绕。
南边有座桃花山,
北面躺着峁陇岭。
……
表面的雨还不才,已经是滴滴答答地下出了声。这场雨是真的好,雨过了就可以种麦茬子豆了。
于主任一声开始,大伙儿竟然没有一个动身的。他们是谁也不看谁,只是木木地看着桌子上的两个大海碗入迷。
好一下子,社员们彷佛忽地醒过来似的,一下子就涌到桌子前面,把个桌子围的严严实实的。
“主任,选了算数吗?”
“对毛主席赌咒言,算数!
”
于主任晃动动手中的长竿烟袋武断地说。
形形色色的手往笸箩里伸,不是去抓豆,而是去捏豆,看是手伸得很急,但是捏豆时却很轻,轻的很有些郑重。捏到豆的手又挪到大海碗上,就听到当啷一声,那豆就落到碗里。人就这么用手捏着豆,就这么当啷地落到碗里,那坠豆的声音虽然是很轻,但是却是很清脆。那笸箩里的豆逐渐见底,那碗里的豆却逐渐起了尖,很像座小山。
捏豆终于结束了,人们又正襟危坐,悄悄地等待好是神圣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是目不斜视地盯着那两只碗。两只碗显然有许多差距,属于我的那只满了而又上尖,险些要往外流。我突发奇想,如果是轻轻一动桌子,那豆肯定就会滚落下来,哪怕是打上一个喷嚏,说不准也会落豆。
“哈哈,”于主任笑的很爽快,他立马站起来,却没有习气地往鞋底磕烟袋锅,把烟袋斜插在后背的衣领上,说:“不用说了,这结果明了了,小毕当选生产队长!
”
“大家鼓掌。”公社尹布告带头鼓掌。
继而,全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队长给俺们说两句吧!
”
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声,接着众口哄起。我好一番的摇摆,浑身在发热,那时我感到我的脸很烫,肯定很红。后来,尾月见告我,那天我的酡颜得像是下蛋的小母鸡。
说什么呢?
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一个动机,我往后怎么干这个队长?
我只记得那时说了一句话:“既然大伙儿相信我,我就和大伙儿摽着劲儿一起干!
”
壹点号 周政文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