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发展的可能
第二季“朗读者”开始时,我焦虑得不得了,由于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我还能怎么去改进?但末了决定还是咬牙要做。
由于有很多人在等。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以为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便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改名贵了,这个是我该当倾注所有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高朋采访大约是2小时,2万字。
我要把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由于删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了很长的韶光。然后我还要再回顾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我要进入他讲话的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彷佛还在我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删稿,把2万字删成2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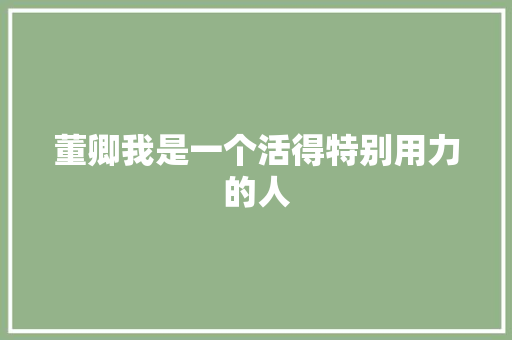
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靠近强制症,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删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以为不舒畅。
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高朋丘成桐——天下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是哈佛大学教授,现在依然生动。
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字一行一行涌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率永久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丘成桐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结束之后,我当时特殊愤怒,怎么可以这样去摧残浪费蹂躏大家的韶光?没有敬畏心,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丘成桐的韶光因此分秒来打算的,却由于我们延误了。
我们末了一场录制完成后,是凌晨2点。末了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
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这一年多的韶光,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很腼腆,但我依然以为,走完这个过程,终极的收成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发展是最主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成绩是你创造自己还有发展的可能。
“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
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种话,实在每个人依然有发展的可能,这个发展不但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朗读者”请过吴孟超,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年夜夫,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
“你须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若何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往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实在任何职业都要戒备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碰着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韶光蛮痛楚的,所有交到我手上的节目,以为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做无谓的花费。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停息。
2013年下半年,我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没有安全感。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便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由于这个行业的竞争很激烈。为了这个位置我花了差不多20年韶光,只有我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少。曾经在我心里,只有事情是最主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
我父母武断反对,他们的情由是你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做的事情。
很多人说,你在海内学学弗成吗?你停下来,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还在海内,就会有事情派下来。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实在便是战胜那种恐怖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沉着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由于我要自己做饭。
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有规律,不管在教室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在美国读书时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事情5天,周末一定关机。我刚去的时候差点被他们逼疯,周末租屋子联系不上一个房屋中介,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答你,一定要等到星期一。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逐步地就切换到了非事情模式。
冲破沉着的是哈文。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以为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扮装,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以是我就谢绝了,后来她又打了两个电话给我。
那年主持春晚觉得很神奇,以为很愉快,就像是久别相逢。
你创造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10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节制了某种措辞,可能你良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
我当时还有一种觉得,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大略地重复过去。以是才有了后来的“寻衅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勤奋刻苦才能改变命运
我爸爸是屯子终年夜的孩子,爷爷过世很早,奶奶是屯子妇女,家里特殊贫穷。
我父亲骨子里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不雅观深深地影响了我。
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磨炼所有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诲可能曾经侵害过我,让我以为不太自傲,我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才有自傲心。
还有一个便是,不喜好依赖任何人,只靠自己。以是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由于我不喜好去埋怨别人做得不足好,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事情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
我以前累到一年主持130多场,累到摔到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全体脸全都是痘痘。我不知道怎么松弛。你得到的越多,你的包袱也越大。
由于不想辜负来之不易的机会,以是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预期去完成。我并没有以为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落望。
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但我不会完备按照这个台本说,我以为照台本读稿是我的一种失落职。
我的影象力非常好,一个10页纸的台本,我大概2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这样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但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好,从哪儿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以为,这样对吗?
现在的危急感可能来自于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是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劲。
这一季“朗读者”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殊喜好的话。比如:
“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么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由于我们生而为人。”
我是一个活得特殊用力的人,用力不足的话我自己会以为不过瘾,会以为日子彷佛白过了,多可惜啊。(来源:《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