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绩、“初唐四杰”到陈子昂,大唐帝国的诗歌才真正唱出了属于自己时期响亮的唐音。
史籍上说,陈子昂“奇杰过人”,不仅是个英雄豪杰,还以诗歌有名于盛唐。
他在“初唐四杰”的根本上,彻底摆脱了齐梁颓靡诗风的影响和束缚,以风雅之音,开唐代诗文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先河,奠定了唐诗波澜壮阔的万千气候。
本日先容的是他最著名的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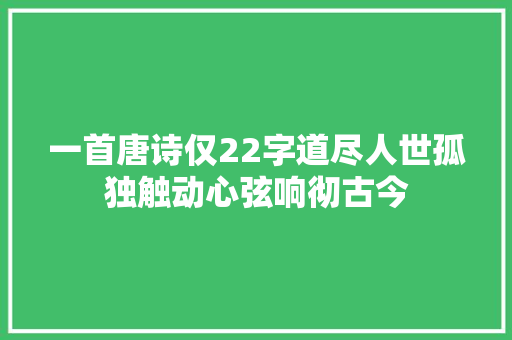
《登幽州台歌》
唐•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公元697年契丹叛乱攻陷营州,陈子昂奉命出征,可带兵的将领昏聩无能,丝毫不采纳陈子昂的善策,国家危在夙夜迟早,自己却报国无门,他登上幽州台,悲愤地写下了这首诗。
幽州台:即黄金台,又称蓟北楼,故址在今北京市大兴,是燕昭王为招纳天下贤士而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里的古人是指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
陈子昂登上蓟北楼,首先想到的便是那个群雄盘据的时期,面前的原野上曾活动着燕照王、乐毅等一批精彩人物,那时君臣和谐,英才荟萃,可谓圣贤相逢。墨客不禁为自己出世太晚,未能遇上那个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期惋惜。
陈子昂是个年夜方任侠的男人,心怀天下,志在济世,入仕后支持武则天的改革主见和方法,受到武则天的重视。
但陈子昂后来对国家涌现的问题直接提出批评,对涉及武则天的也不加隐讳。他常常借古喻今,在诗里表达自己的政治主见。
这引起了武氏集团对他的仇恨,也让武则天烦懑。他们安了个“附逆”罪名把陈子昂关押一年,出狱后,陈子昂想通过立功让武则天重新重视自己,适逢契叛乱,陈子昂主动请缨,随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出征。
贪恐怕去世的武攸宜,致使前军落败,丢失惨重。陈子昂主动进谏,上阵杀敌,但武攸宜以诗人轻之,不纳。
陈子昂空有善策,空怀年夜志,知罹难逢,壮志不酬,只能登高怀古,当登台远眺时,只见茫茫宇宙,矢志不移,不禁感到孤单寂寞,悲从中来,怆然堕泪了。
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日子,今后大概还会有。然而墨客又感到去日苦多,恐怕自己等不到那激动民气的未来。“后不见来者”写出生不逢时的孤独和悲哀。
“念天地之悠悠”,墨客面对空旷的天宇和莽苍的原野,不禁生出人生易老、岁月蹉跎的痛惜与凄凉。有一种如万箭穿心般的孤独,大概便是空有空想而无法实现,心有锦绣,却无人赏识。
这无限的时空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结句逼出一个“独”字,令墨客百感交集。于是在前三句的无垠时空背景上,涌现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年夜方悲歌,怆然出涕的墨客形象。让人深感其内心的孤独与无奈。
这首诗直抒胸臆,表达了墨客失落意的境遇和寂寞苦闷的情怀,这种悲哀常常为古代许多怀才不遇的人士所共有,因而得到广泛的共鸣。
在用词造语方面,这首诗深受《楚辞》、特殊是个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有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本篇语句即从此化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
它有力地表现了一种义士的惨怀,一个先驱者的苦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与代价的人所说的话。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耀古人。
宇宙犹如万物的旅社,短暂地容纳着每一个生灵;而光阴则是百代的过客,匆匆地带走了统统。
这首诗不仅情绪深奥深厚,还深刻地表达了一种哲理思虑。短短二十余字绝妙地展现了人在广袤的宇宙空间和绵绵不尽的韶光中的孤独处境。诗的意蕴探究的不可穷尽,充分解释了它在艺术上的博识成绩。
全篇前后句法是非不齐,音节抑扬变换,相互合营,没有华美的辞藻堆积,只有短短四句22字,便展现出震荡民气的悲壮之美,境界高远,极具阳刚之气,触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令人叹为不雅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