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调池州
杜牧在黄州待得不愉快,由于他想家,更确切地说,他惦记长安,惦记朝堂,齐心专心一念地想以自己的有用之身(刚过四十岁的他竟然发自己已经满头白发)替国家做点事,以是他更加焦急。乃至不在其位也要为国分忧,他无数次地写信给李德裕,替他出主张,对回鹘用兵时,他上书,对泽潞用兵时,他又上书。
(杜牧像)
历史上没有李德裕采纳杜牧打算的记载,由于归根到底,杜牧是“牛党”的人(至少不是“李党”),这一点,他在牛僧孺幕府里任判官时就已经定了下来,在党争为祸甚烈的期间,这样有“牛党”背景的人,李德裕是不会让他冒头的,纵然他有经天纬地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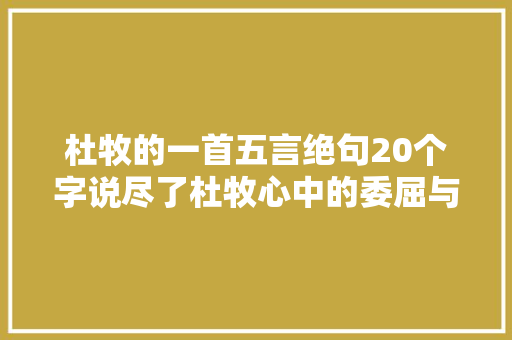
杜牧在黄州“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喊声究竟是喊给了空气,他只能一边思念故乡,一边在黄州的旷野里做点闲诗,他的匡扶社稷之心,只能在日升月落中消磨。他乃至感叹说自己“闲人似我世间无”(《重送绝句》),但临风洒泪也好,对月长吁也罢,“消磨”是他这一段期间生活的主旋律,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池州杜牧像)
844年玄月,秋风已起时,杜牧的职位发生了变革:好友李方玄的池州刺史任满,杜牧奉诏去接任。前面说过,两地相距不远,池州在长江沿线,下辖四县,比黄州多管一县,分别是秋浦、青阳、至德、石埭,秋浦是池州治所所在,便是现在的安徽池州,这个地方也是文化名城,李白曾在这里写过《秋浦歌》十七首,最有名的是个中的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实在这首诗所写的李白的状态,正是杜牧在池州时的状态。
(白发三千丈)
他来池州他不宁愿,由于这仍旧是京外官。但如果我们仔细剖析池州与黄州的城市级别,就会创造,这并不是刺史到刺史的平调。前文我们说过,唐时的州是分等级的,不同级别的州,刺史的官品也不一样(上州刺史是从三品,中州刺史是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是正四品下)。黄州是下州,而据《唐会要》记载,到会昌四年五月(便是杜牧接任前几个月),池州已经升为上州(缘故原由很可能是由于这里盛产铜铁,朝廷要在这里铸钱),也便是说,杜牧实在当选拔了。
缘故原由可能有三个:1、杜牧一直地给李德裕上书,虽然李德裕未加答理,但很显然,他看到了杜牧的态度(杜牧的态度当然不是为了靠近“李党”,他便是想做点事),以为这个人并非无可救药的“牛党”;2、杜牧的堂兄杜悰刚刚从淮南入相,他一定起了一定的浸染,虽然不能把杜牧召回朝中,但多少改进一下杜牧的现状,把他换到条件好、熟习的地方,还是可以出点力的;3、杜牧曾经两次在宣歙幕中,他熟习这里的风土人情,有利于事情(这是官面上的情由)。
(立在池州的杜牧诗意牧童像)
无论如何,杜牧的官品由正四品下升到了从三品,他也不得不沿着驿路,态度悲观地赶往池州任上。虽然驿站提高了他的报酬,但他仍旧不高兴,集中表示在《秋浦途中》:“萧萧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看似只是想家,实在很明显,他想回长安,对付他来说,家乡也意味着朝堂。
对白居易的评价
杜牧曾经在洛阳担当过一段期间的监察御史。在此期间曾经交过一个朋友,名字叫李戡。
李戡这个人很有个性,依照唐时科举考试规定,参加进士试的士子在进场时,都要搜身检讨,李戡认为这切实其实便是人格侮辱,武断反对,末了索性打包回家,不参加考试了,称甘心终生布衣也不受此辱。
(白居易像)
其他士子虽然忍辱参加了考试,得到了功名,但对李戡却十分敬仰,杜牧也敬其德行,结交为友,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李戡去世得较早,托杜牧写了墓志铭,问题来了。
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所毁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授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撤除。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铭中所记,可能是李戡的话,但墓志铭却是杜牧所作,且全文也不长,这段话占了很大的比重,大意是说:元稹、白居易的诗实在不好,是纤艳不逞之作,是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作品,流毒危害世间,意志力不强的人随意马虎被教坏。他自己是没有能力,如果有,一定“用法以治之”。幸亏他没能力,要不然元、白的诗要毁于另一种“笔墨狱”了。
对付杜牧来说,白居易、元稹都算是诗坛前辈。但杜牧却在替朋友写的墓志铭中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就算这些不是杜牧的原话,至少他该是认同这种说法的。这实在让元白的拥趸看不过眼,最让人不服气的是,杜牧自己也常常写男女艳情的诗,跟元、白有什么差别呢?五十步笑百步吗?
(杜牧的风骚诗意)
元白有元白的地位,杜牧有杜牧的地位,诗与诗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人赞颂,就会有人批评,我们无法准确的评判二者的笔墨官司,但至少,这段往事,也对杜牧的仕途产生了些微的负面影响。
连续在刺史任上窝着
会昌六年,唐武宗病去世,宪宗之子李忱(初名李怡)继位,是为唐宣宗。
唐宣宗不喜好李德裕,以为在他跟前不清闲,于是让李德裕出镇荆南,白敏中(白居易的从弟)接过了相印,牛党的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五人同日北迁,回朝任官,牛党要执政了。
(唐宣宗像)
杜牧当然以为高兴,总算换天了,看着被李德裕打压的旧人们一个一个回到朝堂。他也满心欢畅地等着诏令的到来,可等来却是让他调任睦州刺史,睦州虽然也是上州,但距长安更远了。
牛李换政,并没有给杜牧带来急速的好处,表面看似不对,实在深层缘故原由很清楚:1、杜牧算是牛党的人,但牛党失落势时,他不断地上书给李德裕,牛党失落势的人都看在眼里,这一次风水轮流转,牛党也不喜好他了,党争很惨烈,杜牧恰好夹在缝中(文人总是不喜党争的,后来的苏轼也是,他跟两边都不对付);2、此时秉政的是白敏中,他与白居易感深甚殷。白敏中自幼丧父,基本是在白居易的照料下发展起来的,对白居易如此不敬的杜牧怎么可能得到重用。
更何况,就在这一年,白居易去世了,韶光也是玄月,便是杜牧调任的时候。以是,他这次调任多数是他自己“作”出来的,怪不得别人。
(《清明》诗意)
人是要受点委曲的,特殊是文人,杜牧有两首精彩的诗,一首是《清明》大致写于黄州或池州任上(肯定不是山西杏花村落,杜牧没有去过那里);另一首《泊秦淮》写于从池州向睦州转徙的途中。如果不是这前后连三赶四的“挫折”,这样的好诗,恐怕就不会出身了。
(《泊秦淮》诗意)
倘若真是没有这两首诗,怕是杜牧的诗坛地位都会受影响吧。
一首五绝小诗
杜牧的代表作多是七绝,《山行》、《泊秦淮》、《清明》,首首叫得响,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其他诗体写得不好,本日我们就来读一首他在睦州写的五绝,诗的标题是《盆池》,全诗如下:
(石头上的《盆池》诗)
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白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
所谓“盆池”,即埋盆于地或挖地成池,引水灌溉而成小池,用以栽种可供不雅观赏的鱼类与水生花草等。唐诗中写到盆池的诗很多,一个人被扔在边州过平常日子的杜牧,心里不甘,但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委曲着丁宁日子,他在自家的阶前空地上挖了一个池子,装了水,或者是为了浇花卉菜蔬什么,总之,他有了一个类似盆子大小的一池水。
但妙就妙在这盆子大小的沼泽,让墨客用20个字创造出了另一番天地:
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这是平淡浅易的写法,当然,也只有大师级的墨客才能写出这样平淡却又隽永的的句子,这首诗的创作年代文集中没有记载,但放在睦州的心境与条件,十分契合。门前遍铺苍苔(为什么是苍苔呢,或者便是实写,或者便是人迹罕至,墨客孤独得紧),的地上,被墨客凿了一个盆池,这是很平常的小事,但到了墨客笔下,却用来表达心志,池水中映出的上苍白云是属于我的,谁也夺不走,这是我的一片天,是“偷”来的。虽然也落落寡欢,但终归并未屈从,还敢“偷”,乐意“偷”,细思语气,又象个调皮倔强的孩子,真真妙不可言。
(池水映白云)
白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池水如镜,映出上苍白云,到了晚上,天边的明月也彷佛一下子来到了我的阶前。这是字面意思,但我们相信一定还有深层的隐喻,杜牧通过这样的语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江湖之远,但处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之下,天下所有的事,不都在我的面前吗?你看,他有多么想回到朝堂上去。
诗的好处便是意思都在字面之外,我们相信杜牧借这首小诗有更多的话想说,但也可能他便是想写一写门前的一池水,可能是我们过度解读了?
有人认为这是杜牧恬淡自然生活乐趣的表示,说他超然物外,说他热爱自然如斯,我们并不赞许,此时,他还远没有到那种生活状况。至少我们认为,这一首五言绝句,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说尽了杜牧心中所有的委曲与不服。当然了,“诗无达诂”,各自按自己的理解便是了。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无法说假设杜牧真在朝堂之上,晚唐的气候会不会为之一新,但真正一个向上强力发展的国度,须要一大批正能量满满、身怀济世安邦之才的人,这是肯定的,
可惜了,有才华的杜牧没有遇上适宜他的好时期。
(【唐诗闲读】之203,图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