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池凝碧,天河流远,天水滔滔。今古千年,松花江向被视作来自天庭的圣水,歌之咏之,瞻拜以礼,诗章残酷,而浩瀚题咏里灿灿生辉的诗眼,又总不脱天水回护的吉林乌拉……
1吴兆骞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春走上流放宁古塔(今宁安)之路的。望着吴兆骞北去的身影,顾贞不雅观等一班朋侪顾虑不已,此后不久即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营救,纳兰性德是个中最力者。该当是由于这些交情的鼓舞吧,吴兆骞在流放之地的诗作竟多有年夜方旷达之气,气度开阔,纵览八荒,很少衰飒悲音。
松花江天水南来,万古滔滔不歇,是千百年来东北的黄金水道,也是吉林城母亲河
过吉林城时,吴兆骞宿于松花江边的尼什哈站。驿站又紧邻龙潭山,由于山上的龙潭和山下的小河生有满语称之“尼什哈”的小鱼,驿站也就顺俗而取此名。在这大江之侧,吴兆骞曾于晓星迷茫里赋得《早发尼什哈》。康熙二十年(1681),在诸位朋侪的营救下,吴兆骞终于遇赦南还。归途中,又一次途经松花江,身后,是即将拜别的古之不咸山;身边,是千古滔滔的松花江,多少历史曾在此演绎。吴兆骞因之感慨而作《混同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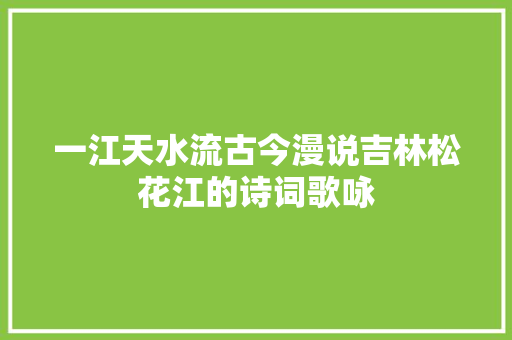
混同江水白山来,千里奔流昼夜雷。
襟带北庭穿碛下,动摇东极蹴关回。
部余石砮雄风在,地是金源霸业开。
欲问鱼头高宴处,冷落遗堞暮潮哀。
清初流人们的诗作里,多称松花江为混同江。混同江之名,乃得之于辽代,《契丹国志》记载,松花江“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混同江之名,由是沿用数百年。吴兆骞此诗,是本日已见清代最早抒写松花江的作品之一。天水浩瀚,远从长白山奔驰而来,穿云裂岸,涛声澎湃如雷;一起苍龙样襟带北庭,摇撼东极,和长白山一同凝集了东北山河的魂魄。这里,曾是肃慎故地,楛矢石砮记录着一个民族历史的雄风;却又是金源文化肇基之地,是一代雄主的霸业崛起处;而一代一代辽主的鱼头高宴处,称之春捺钵的金帐地,又到哪里去寻?指示那冷落遗堞,只有那不息的潮声仿佛在诉说着往事……
吴兆骞画像
吴兆骞从宁古塔回京时,曾特意带回几支石砮。传说中的楛矢石砮有一尺八寸之长,不知他带回的是什么样子,但可见那时它还不是绝世之物。在向顾贞不雅观、纳兰性德等朋侪展示这来自北地的石砮时,吴兆骞一定讲过孔子过陈辨识讲授肃慎石砮的掌故,该当也吟咏过这一篇《混同江》诗作吧?
杨越是因帮助郑成功反清流放于宁古塔的,韶光比吴兆骞稍晚。其子杨宾曾两次奔赴宁古塔,后来将见闻写作《柳边纪略》。他也有诗《混同江》:
浩浩此江流,万古争昼夜。
我来独非时,但见寒光射。
雪埋高岸头,沙涨层冰下。
顿辔驽马奔,杖策车轮过。
自昔戒垂堂,况复骑衡坐。
来者纵莫欺,履薄还愁破。
东行出塞垣,百川此为大。
千山更临江,崩奔争一罅。
虎踞与龙蟠,形势良非假。
莫漫数金陵,渤海亦其亚。
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月,杨宾出塞探父,至吉林城时,已是冬月,大雪茫茫,千山俱白。因此,诗中所见,尽是冬日景象,“雪埋高岸头,沙涨层冰下”,人与车都从冰封的大江上走过,几疑冰面会不会踏破。虽然时为冬季,万物肃杀,已不得见大江奔流的壮阔,可是江山形胜却都隐然在目,“浩浩此江流,万古争昼夜”,乃历史时空之下的畅想抒怀;“千山更临江,崩奔争一罅”,则是目中所见的山河胜境;“虎踞与龙蟠,形势良非假。莫漫数金陵,渤海亦其亚。”却是对此江山形胜的评价,有龙蟠虎踞之势,控塞垣百川之要,恐怕金陵、渤海也在其次。
杨宾独具慧眼,在《柳边纪略》中多写山河地理,趋近于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朴学之风;此诗亦是从地理形势点破诗眼,见出墨客于此心有戚戚焉。也恰是以,他的诗文日后成为研究东北史地的案头之书,非只是抒怀之作可比。
康熙五十二年(1713)春,流人办法济踏上去往卜奎的遣戍之路。到达吉林城过松花江时,是端午节前一天。办法济临流有感,赋诗《五月四日渡混同江》:
边江新涨急,浩浩一舟过。
高泻白山雪,横连黑水波。
近松午风落,倚岸夏云多。
竞渡来朝事,临渊怆汨罗。
市价北地春汛,江水新涨,一舟横渡,但见天水浩荡。一句“高泻白山雪,横连黑水波”,将松花江源头之壮阔与浩瀚千里的气概信笔抖落而出,令民气神为之一爽。倚岸之夏云则非是夏云,乃是一片又一片的松林望之如云。办法济过吉林城时,还曾赋诗《稽林》,内中有句“对岸干冈峦,林木密如棘。栝柏大十围,苍皮翳山黑”,便是这“夏云”的实写。但墨客此时的心境,却因自身的遭际,想起受谗被逐的屈原……
两年之后,办法济之子方不雅观承不远千里前来探父,也曾于大江之侧赋诗《稽林渡松花江》,感叹关东山河之寥廓:“荡涤存荒远,微茫接混同……”是自然的荒莽,也是历史的荒莽。
在这一期间流放文人的诗作中,大多将松花江名之以混同江;在他们的文学视野里,又多将松花江与长白山比并歌咏,显见这一片山河在南方文人的视域里并不陌生。
2康熙、乾隆东巡吉林,为抒写松花江的诗情添增了一份历史的波澜。
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东巡吉林之旅,是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时,虽然西南之祸乱已经平息,但东北来自沙俄的外祸却搅扰边陲不得安宁。这一年,康熙仲春十五日从北京出发,三月二十五日抵达吉林,刚好四十天韶光。在盛京(沈阳),康熙祭告了祖陵,途中又不断行围打猎,一起走得甚为从容。从在吉林期间一系列反击沙俄的支配来看,有关的计策方案该当都久已擘画完善。松花江上,康熙中流放船,随后又校阅阅兵吉林水师。阅毕,即兴作《松花江放船歌》:
松花江,江水清,
夜来雨过春涛生,
浪花叠锦绣縠明。
彩帆画鹢随风轻,
箫韶小奏中流鸣,
苍岩翠壁两岸横。
浮云耀日何晶晶,
乘流直下蛟龙惊,
连樯接舰屯江城。
貔貅健甲皆锐精,
旌旄映水翻朱缨,
我来问俗非不雅观兵。
松花江,江水清,
浩浩瀚瀚冲波行,
云霞万里开澄泓。
浏浏亮亮,大气如虹,雄姿英发的豪迈气候,经略山河的超绝气概,都席卷个中了。一段江干,“苍岩翠壁两岸横”之壮美景致,江面“浪花叠锦绣縠明”之宁静秀美,以至吉林水师“貔貅健甲皆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之威武雄壮,都如画页般一幅幅展开;结句“松花江,江水清,浩浩瀚瀚冲波行,云霞万里开澄泓”,则展示了对即将进行的反击沙俄侵略的必胜信念。诗作不乏浪漫,更充满豪情。在抒写松花江的诗篇中,康熙的这首《松花江放船歌》,可称神作,这并非由于康熙是一代帝王,实因其记录了历史。在诗语里回望,松花江上,旌旄映水,水师健儿皆貔貅之士,风帆迅发,浩浩瀚瀚,冲波而行……那便是松花江的一段历史景象啊!
由于康熙的这一次东巡,松花江又留下了一幅图画。东巡的军队中,有身为御前侍卫的曹寅,又有翰林院侍讲高士奇,两人皆词采丰茂。在乌拉街的几天里,竟多逢阴雨,四月四日,从乌拉动身返回吉林城,才上路时,还是晴光蔚然,走过不到十几里时,却溘然风雨大作,“骇水腾波,江烟泼墨”,船不能行,只得靠岸停泊。
曹寅后来写下《满江红·乌拉江看雨》,记录了这风雨时候:
鹳井盘空,遮不住、断崖千尺。偏惹得、北风动地,呼号喷吸。大野作声牛马走,荒江倒立鱼龙泣。看层层,春树女墙边,藏旗帜。
蕨粉溢,鳇糟滴,蛮翠破,猩红湿。好一场莽雨,洗开沙碛。七百黄龙云角矗,一千鸭绿潮头直。怕凝眸,山错剑芒新,斜阳赤。
高士奇则作《水龙吟》:
晓峰新翠飞来,锦帆半渡春江楫。恰才回顾,碧落天净,弱云微抹。咫尺苍茫,狂飔骤卷,怒涛喷雪。讶盆翻白雨,松林转黑,红一线,雷车掣。
如此风波怎去!
急回船渡头刚歇。野炉争拥,征衫未燎,薄寒犹怯。辽日遗墟,金源往事,断垣残堞。有当年献纳,埋钱满瓮,听渔人说。
两人的词作,皆大气磅礴,畅快淋漓,富于想象。且看曹寅笔下风之狂猛:“大野作声牛马走,荒江倒立鱼龙泣。”雨云之厚重:“七百黄龙云角矗,一千鸭绿潮头直。”再看高士奇诗中那惊天掣地的巨雷:“咫尺苍茫,狂飔骤卷,怒涛喷雪。讶盆翻白雨,松林转黑,红一线,雷车掣。”大风、大雨、大雷,真可说触目惊心。在康熙东巡路上,这是罕见的一幕,是松花江上风雨气候的历史写真,且又是两位词人不约而同一起来写,这在词坛上也可称罕见的奇不雅观吧!
乾隆曾自称“墨客天子”,几日不作诗,便觉手痒。乾隆十九年(1754)东巡吉林,自然也多有诗赋。其诗作《松花江》气候开阔:
滚滚遥源出不咸,大东王气起龙潜。
劈空解使山原折,接上那辞雾雨添。
两岸参差青嶂印,一川菜蓼碧波恬。
地中呈象原檐鼓,石辨支机孰是严。
首句“滚滚遥源出不咸,大东王气起龙潜”,即是破空之语,滚滚松花天水,源出古之不咸,山为圣山,水亦是圣水。天水萦绕之区,原是潜龙之地。其从天而来,故称“劈空”,源在天池,可谓“接上”;劈空而山原摧折,接上则不辞九天雾雨。两岸青嶂千里,一川碧波恬然。“檐鼓”是为牵牛之星,“支机”乃是织女天河边浣纱之石,原来,这一条亘古长流的松花江,便是大地上的天河呀!
在吉林城,乾隆还留下诗作《松花江捕鱼》:
松江打鱼亦可不雅观,潭清潦尽澄秋烟。
虞人技痒欲效悃,我亦因之一放船。
施罟濊濊旋近岸,清波可数鲦鲈鲢。
就中鲟鳇称最大,渡以寻丈长鬐轩。
波里颓如玉山倒,掷叉百中诚何难。
钩牵绳曳乃就陆,椎牛十五一当焉。
举网邪许集众力,银刀雪戟飞缤翻。
计功受赐即命罢,方虑当秋江水寒。
这里记写的是在松花江捕鱼的情景,绘影绘声,维妙维肖。虞人(捕鱼牲丁)“技痒”,欲在乾隆面前一展长技,乾隆也便因之“放船”,而捕得的大鳇鱼仿如玉山倾倒,钩牵绳拽才得上岸,要十几条大牛才拉得动,场面何等壮不雅观!
此处须要补充的是,康熙在三十七年(1698)时,曾又一次东巡吉林,在舒兰法特地方,康熙亲掷网纲,一网获鱼一万四千余斤,一天获鱼数十万斤,渔获堆积如山,康熙因之赋诗《松花江打鱼最多颁赐从臣》:
松花江水深千尺,捩柁移舟网亲掷。
流洄水急浪花翻,一手提要任所适。
须臾收处激颓波,两岸奔趋人络绎。
小鱼沉网大鱼跃,紫鬣银鳞万千百。
更有巨尾压船头,载以牛车轮欲折。
水寒冰结味益佳,远笑江南夸鲂鲫。
遍令颁赐跟从臣,幕下然薪递烹炙。
天下才俊散四方,网罗咸使登岩廊。
尔等触物思比托,捕鱼勿谓情之常。
这种“小鱼沉网大鱼跃,紫鬣银鳞万千百。更有巨尾压船头,载以牛车轮欲折”的场面,与乾隆记写的捕捉鳇鱼“钩牵绳曳乃就陆,椎牛十五一当焉”情景,俱是当年松花江上渔产丰富的历史写照。虽是诗语,却非虚言。乾隆生平,极是崇仰祖父康熙,日常行事,也多以祖父作为楷范,看这两首诗,康熙于结尾处陡然一转,由捕鱼说到网罗人才,不可使“天下才俊散四方”;乾隆则是写捕鱼方罢,忽念及当下已是仲秋时节,“方虑当秋江水寒”,一丝体察民瘼之心油然而生。此一结尾,笔法何其附近!
在历史上,这一对祖孙天子同为松花江作歌,又为松花江捕鱼留下各自的诗证,是那一时期松花江自然生境的诗意写真,是松花江历史的一页记录,本日读来也还是令人浮想联翩。在中国诗坛几千年的历史上,这该当也是一桩罕见的诗话趣事吧!
明清时期的船厂之设,使吉林城有“船厂”别名。20世纪40年代,民间许多人仍呼吉林城为“船厂”,可见老地名在影象里是多么顽强的存在。由于康熙的《松花江放船歌》,一句“连樯接舰屯江城”,又使吉林市有了“江城”的别称。这一别称,本日的利用频率则远超“船厂”之名。
吉林本名吉林乌拉,是为满语,意谓沿江之城,是松花江流域最早的城市。从本名到别称别名,皆系于江,源于江,一条江孕育并滋养了东北的这一座城市,因此,许多诗篇在咏赞这一脉天水时,也融入了吉林乌拉,他们是母与子,没有松花江母亲河,也就不会有吉林乌拉……
乾隆东巡吉林,曾作《驻跸吉林将军署》,计得诗三首。虽然后来者多说其诗作诘屈难懂,这几首诗却可称晓畅:
星汉南来直北流,萦回漭沆卫神州。
城临镜水沧烟上,地接屏山绿树头。
辐辏闾阎市中日,往来舸舰织清秋。
设教图入图画画,应拟宣城谢氏楼。
启句之“星汉”,非是天上之星河,乃松阿里乌拉天河也。天水一脉南来,苍茫辽阔,迂曲萦回,正是神州大地之护卫。一座城,就在天河怀抱之中,临于镜水沧烟,遥接屏山绿树;江上舸舰往来,市中闾阎辐辏,这便是李白于宣城谢朓楼所见之“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的风景,是“天涯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的江山图画,是可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上苍揽明月”之壮想的胜境啊!
城在画中,画在诗中;一幅画卷,又都在天河星汉、镜水沧烟的背景之中。
张光藻画像
同治九年(1870),曾任天津知府的张光藻以教案事被遣戍齐齐哈尔。将入吉林城时,张氏口占一绝《过欢畅岭》:
西来峻岭苦难行,欢畅心偏到此生。
十里江城如画里,行人立时看分明。
诗虽作于欢畅岭,一句“十里江城如画里”却点明诗眼,将如画江城投入读者眼眸。从此诗作看,吉林的“江城”之别名在那时便已广为人知了。张光藻又有诗作《吉林省城》:
扶余国小旧称王,圣代山河此发祥。
雉堞环山冰作路,雁行筑室板为墙。
民风自昔如京国,贸易曾闻到海航。
自是我朝根本地,盛衰关系在边防。
这首诗将江城吉林的历史与风貌做了简洁注释,汉代初年,在龙潭山、东团山、帽儿山三山之地,有夫余人立国于此,尚有遗墟宛然。之后岁月播迁,此处更为清王朝发祥之地。这时已经大江冰封,一条江即成冰路。城市沿江而建,随江流婉转之势呈扇面状辟路建房,在山上了望仿若雁行之状,而城中人家皆以大木板围做院墙。虽然远在边外,民风民俗却一如京国。遥想大唐渤海与明代,依赖松花江黄金水道,航运发达,海航贸易通过松花江远达库页岛一带,大批货船都是从吉林出发。张氏在这里写下的,是吉林城一个时期的历史光荣,当然,伟大的历史背景,也是天水滔滔的松花江。
宣统二年(1910)春夏之交,浙江仁和人沈兆禔“浮江渡海,走幽燕,入辽沈,远游肃慎故墟”,来到吉林之后,“颇爱此间山水,以为大似江浙风景”,每有空闲,即搜求吉林之历史地理、源流沿革、风土人情,撰著了有韵志乘《吉林纪事诗》,有《船厂》二首,个中之一:
山映夕阳分五色,水流明月荡重光。
门前即是西湖景,船厂天然避暑乡。
山映夕阳,水流明月,诗语即是画境。在此画境下推出的赞语“西湖景”“避暑乡”,便直入心底。无疑,这也是一座城市风华气质最好的名片了。
1920年秋,刚刚从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即奉父命来吉林剿匪。这是张学良第一次领兵作战。从陆军讲武堂毕业之后,张学良即获任卫队旅旅长。这次出征,众将瞩目。张学良亦不负所望,带兵从沈阳出发,一起不做勾留,直赴一壁坡(今黑龙江省尚志市)沙场,奇兵突袭,五战皆捷;随后,收复已被强盗霸占一个多月的佳木斯,全歼匪帮“老占东”;又抚恤灾民,规复农商,引得官民赞赏。
1929年,张学良又一次来到吉林。这一次,是来吉林察看。此时,张作相主持吉林军政事务,甚有作为。数年之间,吉林城面貌一新,建筑了松花江十里长堤,办起了自来水厂,创建电话局,开设电灯厂……张学良不雅观览市容市貌,甚为感奋,遂欣然赋诗:
四面皆山三面水,十里江堤分外美。
欲问天国在何处,不在苏杭在东北。
诗句朴素,却饱蕴浓情,本日已是歌咏吉林松花江风光的佳句。
浏览这些诗作,曾经暗自悬想,若是将这些诗篇雕凿以碑铭,直立松花江岸,那该当是松花江的又一道风景吧?是历史的风景,自然的风景,当然也是文化的风景。
4天河流淌,潮鸣水唱。由于松花江的卓异禀赋,一座江城也孕育了自己独占的风情。
每年一俟冬深,大江冰封,统统彷佛都沉寂了。这时,城下的江岸却热闹起来。江面的冰层厚达两尺有余。载重数千斤的大车,也压它不垮。城内旅店的店主们,这时一起劳碌起来。在附近城区的江面上,他们凿冰成沟,然后在沟内竖以木板或树桩,再搭以院门,如此,就形成一个开阔的院落。由于建在江上,以是俗称“水院子”。院落内有大略单纯的牲口棚,又有草料库。那时,上江、下江的商家和庄家都赶在这一时段进城。此刻,一年将尽,粮进仓,菜入窖,木柴出山,各种山珍特产也都收装整洁,只待入城售卖,獐、狍、鹿、豕、雉、鱼之属,无不尽有。但见白茫茫的大江面上,大车和爬犁缕缕行行,一天内进城的爬犁有几百张,大车也有上百辆。民国初年旅居吉林的湖南籍墨客黄兆枚以诗记之:
经由寒冷十月霜,凿冰排栅别开场。
水缸压得重阳菜,更买鱼豚雉鹿獐。
墨客沈兆禔也在他的《吉林纪事诗》里写下这一种风景:
连朝风雪水冰坚,立栅江沿受一厪。
凫雉獐狍朝列市,居人争购度新年。
待到冬尽春初,冰面开解,松花江上便是又一番景象了。大江冰解,谓之开江。开江又有“文开”“武开”之分,“文开”平平常常,“武开”却是触目惊心,场面极其壮不雅观。常常是江面的一处冰体突地訇然解体,接着十里百里的冰面都随着砰然倾圯,仿佛天崩地裂般发出轰隆隆的雷鸣之声。这时,大大小小的冰排拥挤碰撞,浩浩荡荡,争相夺路向下贱而去,冰排相互撞击,声音恍如夏日天空的响雷,纵然在阔别大江一二里的地方,也能听到好似千军万马奔赴沙场一样的隆隆之声,闻之震荡夺人。墨客刘化郡赋写了这一江上奇不雅观:
昨宵江上雾溟蒙,雷辗冰开雨趁风。
应是老龙春睡觉,翻身撑破水晶宫。
松花江上,风情无尽;在诗篇里阅读这些风景,风景也就都有了浓郁的诗意;而经由诗笔润色的山河,便便是有条有理的历史画卷。
两岸山河走日月,一江天水流古今。在古人歌咏松花江的诗篇里,这些风景是不会老的……
本文选自2021年民生读本,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拓立项项目《木城往事》,作者高振环,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版权所有,未经容许严禁通过任何办法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