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个思路和原则,我试着写了几首诗:
东梁锄谷到西头,沟上村落容似蜃楼。
沐浴斜阳无限爽,转腰踢腿逞风骚。
冬去春来必早起,出工不管睡多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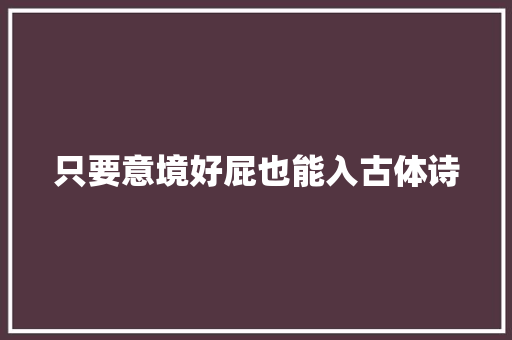
雨浇汗臭风刮脸,饭罐腰身尽是泥。
思念母亲的句子:
近乡情怯步无绪,沟窄崖昏探母急。
曾几松柠发冢外,再无小脚待村落西。
老来励志的句子:
日远东窗网已上,山乡归罢改时章。
年年煮字年年淡,每每收摊每每忙。
我有个明确的目标,写诗是为了揭橥,以得到社会的考验和认可。先是在地方主流媒体揭橥了十几首。后来有点“一发而不可收”,索性将自己60年平生都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吧,一气之下写了248首,数易其稿,然后发到《山西文学》邮箱。没想到2015年第5期给全文揭橥了,标题被改为《诗记年表》。如此快速的成功使我大喜过望。可是,后来看到墨客臧克家说的一句话:“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就动摇了连续写诗的信心。接着又读到鲁迅师长西席一段话:“我认为统统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今后若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算夜圣,大可不必措手。”直译成现在的口语,便是:如果不能在唐诗宋词顶峰之外增长新的东西,就干脆别再动手了。
我翻来覆去思考这段话,以为这样理解也大体不差,但是如果每个文化人都照此行动的话,那就太悲观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诗词艺术就断不会再向前推进一步甚或萎缩。鲁迅师长西席只管那样说,可他还是写了几首诗,如“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等。现在看来,他是恰到好处,便是那么看似随意的几首古体诗,也足以万古长青。
时期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日时期,作为文化复兴主要组成部分的诗词复兴,已成势不可挡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为了不使自己业已节制了的一点古体诗写作技巧趋于沉寂、消亡,我便寻思着在诗论方面做点磋商。我的最大体会是,切莫把平水韵作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金科玉律。写诗是许可变通的,恪守格律的繁文缛节,不许一字“出律”,那样势必限定人的思想。实在,所谓的“三仄尾”“三平调”乃至“孤平”等说法,并不是古体诗成熟期的唐宋时期禁忌,而是明代往后格局不大的诗家故弄玄虚陆续添加的禁条,不敷为据。古体诗发展到唐诗阶段,局势大开,样式完备,以近体为主,古体不废,百花齐放,空前繁荣,因而成为之后人学写诗词的圭表标准。本日的诗词复兴本意是继续唐代的优秀传统,并在唐代根本上继续创新,这同鲁迅“我认为统统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的判断是同等的。比如“东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非常符合“平平仄仄平平仄,(甲)仄仄平平仄仄平”的七言绝句正格,“岸”和“还”并不相挤。
有人妄加评论,说毛主席的“独占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不合律,“虎豹”与“熊罴”合掌,这实在是不理解毛主席当时的不同“特指”,这样写是故意而为,不可能是无心之错。毛主席还一反常态,将凡人认为不雅观观的字眼“屁”入诗:“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谁规定不能这样写来?没有。从未有人规定,那就可以试一试,以发泄当时的激愤心情于万一。
一句话,诗词复兴,不是马首是瞻地回到过去,而是要删繁就简、适度宽松、承前启后、守正创新,既“复”又“兴”,这才是中华诗词与时俱进、实现繁荣的要义。如果能这样理解,看似回环往来来往、深奥难解的“平平仄仄,粘粘对对”,实在一点都不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