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中年期间,他践行的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空想,通过大量的讽喻诗,以期能纠正时弊,积极入世。而晚年身兼儒家“独善其身”与佛道理论影响,安适保和的心境,以享养生之道,得遐龄之福。
34岁的白居易写下《感时》“朝见日上天,暮见日入地。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将至。白发虽未生,朱颜已先悴。”这一年唐德宗去世,顺宗登基,启用韦执谊、王叔文等人实施变革,加强中心集权,反对藩镇盘据和宦官专权。八月,唐宪宗登基,韦执谊、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贬,永贞变革失落败。白居易将人生衰老将至的忧虑与政治变革的无常结合,故有此感。
真正感想熏染到衰病的影响是白居易43岁。先患眼疾,分别写了4首眼疾的诗,分别是《眼暗》、《得钱舍人书问眼疾》、《病眼花》、《眼病二首》等。
“从前勤倦看书苦,晚岁悲哀出泪多。”白居易因从前勤奋苦读和悲哀多泪而危害了视力。虽积极诊治,但疗效并不好。“春来眼暗少心情,点尽黄连尚未平。唯得君书胜得药,开缄未读眼先明。”因眼疾疏肝补血错用清热的黄连,白居易的眼病是逐渐加重的,从眼暗发展到了眼花,“大窠罗绮看才辨,小字文书见便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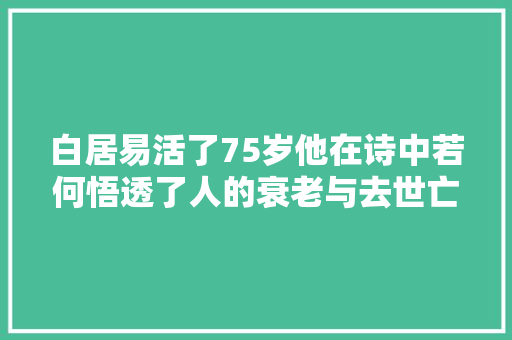
68岁白居易再患风疾,写《病中诗十五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朽株难免蠹,空穴易来风。肘痹宜生柳,头旋剧飘蓬。”“风疾侵凌临老头,血凝筋滞不调柔。”“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头晕眼花、枢纽关头疼痛麻痹,白居易未寻医问药,而是采取顺其自然的生理疗法“今幸乐天今始病,不知合要苦治无。目昏思寝即安眠,足软妨行便坐禅。身作医王心是药,不劳和扁到门前。”以乐不雅观的态度对待疾病。
白居易在《叹老三首》中写道:“晨兴照青镜,形影两寂寞。少年辞我去,白发随梳落。万化成于渐,渐衰看不觉。但恐镜中颜,目前老于昨。”真的是一每天变老了。“吾闻善医者,今古称扁鹊。万病皆可治,唯无治老药。”即便神医扁鹊也只能救治疾病,面对朽迈也束手无策。在《渐老》、《任老》、《览镜喜老》等诗中,白居易逐渐接管了变老的现实,完成了对朽迈的超越,乃至以自嘲的口吻来应表述:“昨因风发甘长往,今遇阳和又小康。还似远行装扮服装了,迟回且住亦何妨。”
白居易70岁写《逸老》诗:“去何有顾恋,住亦无忧恼。死活尚复然,别的安足道。”这时,他以达不雅观的态度对待死活,已经完备参破了死活,去无顾恋,暂住人间亦无烦恼,真正达到了超然的境界。
办理了死活问题,晚年的白居易更是学会了享受当前的生活。能像白居易晚年生活安适保和的作家并不多,墨客对身体状况的敏锐感知和生命状态的诗意呈现,也蕴含着墨客对仕途和人生的深刻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