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初始孕育的春天,江海合归一体,回答到混沌未分的状态———天地归位、万物造始。那是盘古开天地时、发轫这洪凶年夜流的、老子“有生于无”的状态。
这如《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般的磅礴气势,由中唐墨客张若虚于空灵寂静的月夜中,凭海望月地吟咏出来。吞吐太息间,便已将几百年的魏晋绅士风骚,与自己士大夫的幽古怀乡之情,通盘寄托个中。
这一句短短七个字,个中有两个词与空间秩序干系:“连”与“平”。仅这两字,便将“江”与“海”汇入宇宙的洪凶年夜流中。
相互依存即为“连”,没有差别即为“平”。在这个万物平等、相克相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洪荒天下。江与海合为大流,江即是海,海即是江,又有江又有海,既非江也非海。这是《道德经》般 “抵牾对立又统一”的聪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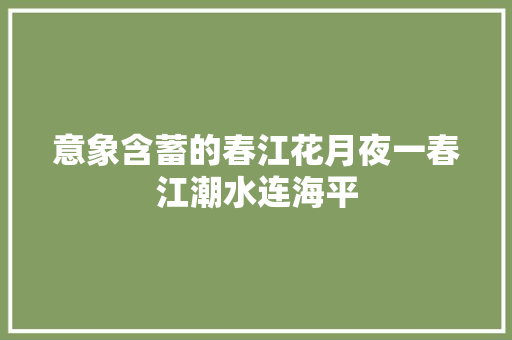
能有这样形而上的领悟,张若虚彼时,该当已有相称的人生阅历,不会是“不识愁强说愁”的青葱少年。
中唐墨客张若虚,大约经历过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前期。这是唐朝励精图治的壮大期间。有承继“贞不雅观之治”的“永徽之治”和“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期间。
《新唐书》云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彼时之吴中是现在的江浙一带,张若虚是江苏扬州人,江苏地处沿海。
《旧唐书》提及张若虚曾任“兖州兵曹”,兖州离海边城市也不远。
张若虚在家乡也罢,在任上也好,都有看海的可能。
兖州与孔子故乡曲阜相临,离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也附近,都离海边不远。但孔子和孟子对海的兴趣都不算大,极少提及。
像张若虚这样正面以海为题材的诗作,在浩繁的古诗中也不算多见。
但即便如此,整篇诗36句中,只有三句提及海:“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斜月沉沉藏海雾”。
而提到江的则有12句之多:“春江潮水连海平”、“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江天一色无纤尘”、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落月摇情满江树”。
可见其对“江”的关注还是远远多于“海”的。这封闭广袤的要地本地沃壤,治农于本的农耕经济,对江河水域灌溉的依赖,犹对母亲般的小儿百姓之心。
看到海的张若虚,与看到海的古希腊墨客荷马,是截然不同的心境。他们一个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是海洋文明的。一个是映照内心的寂静无为;一个是勇于寻衅的冒险奇遇。
以是同样是乡恋:
张若虚是望月思乡的公共精神———“可怜春半不还家”,这种触景生情和李白的“低头思故乡”、王安石的“明月何时照我还”、杜甫的“月是故乡明”……,一模一样地倾诉精神欲望;这种乡恋是一种文化情结、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感性的。
荷马是个人的英雄主义———奥德修斯海上流落十来年,历尽千辛万苦,只为与妻儿团圆的私人目的,他拼了老命也要身体力行地回籍。这种思乡是一种实践、改造、履行的详细行为,是付诸实际的,方向理性的。
以是,《春江花月夜》末了问道“不知乘月几人归”。张若虚毫无例外地,像李白一样“昂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如张九龄一样平常“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地想而不得、恰到好处、不愠不火取个中的中庸之道。
月在这文化里的意象便是故乡,是许许多多这农耕文明下的士大夫的乡恋。那里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出发点,也是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是“孝父侍君”的出发点,这儒家伦理之下,孝有多努力,忠就有多卖命。
孝是父子自然关系,忠是君臣社会关系。
月与故乡,就这样通过推此及彼的搭桥,把“孝”的自然情绪,与“忠”的社会伦理暗合起来。
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比,就潜移默化地将自然法则代入社会法则了。
封建文官的集体感情是如此同等,他们即便“此时相望不相闻”的空间异位,“人生代代无穷已”的韶光相错,但只要一举头看到明月,就能超过时空的“江月年年望相似”,就可以引发相同的意识形态出来。
这文化共性大过个性。
由于,这文化绵延未曾断过,一以贯之地在同一种文教中浸淫,没有另一种教诲资源供应选择的可能。
毕竟,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之后,封建制度之下,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掐断了,此后诸子百家的盛况在封建王朝再没涌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