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雪花如糖,简书签约作者
\公众东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为一个\"大众绿\公众字,他绞尽脑汁,从\"大众到、过、入、满\公众等十几个字中,反复考虑,末了才确定\公众绿\公众字。把形容词奥妙地活用为动词,整首诗变得灵动而富有活气,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
诗的作者,便是大家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同时也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
可是谁又曾料到,这样一位名垂青史的一代文豪竟然由于生活中不修边幅,而被后人称为史上最邋遢的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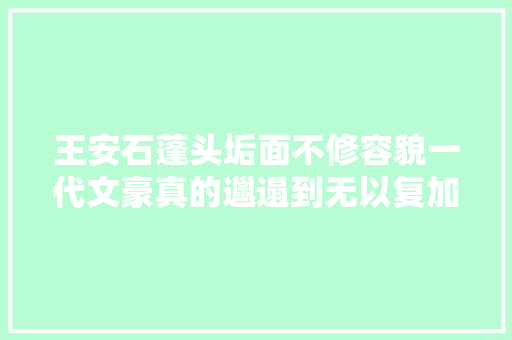
01.
关于此,正史野史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宋史·王安石传》中说他\"大众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公众,意即衣服脏了,用肉眼都能看得到污垢了还不脱下来,脸上都蒙了一层灰了也不洗一洗。
虽然史官对此着墨不多,但就凭这八个字足以让王安石邋遢、不讲个人卫生的形象深入民气。如此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纵然举止不风骚有点不修边幅,但也不至于连脸都不洗去上朝吧,他可是大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堂堂宰相呢。
还有南宋朱弁写的《曲洧旧闻》也有类似的记载:王荊公(王安石)性简率,不事润色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不无有择,自少时则然。
这样的言语还算客气的,最毒辣的莫过于同朝为官的苏洵(苏轼的父亲)。他对王安石的穿衣饮食可谓嗤之以鼻,在《辨奸论》中这样写他的政敌: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大臣俘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意思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现在有人却不是这样,穿仆众的衣服,吃猪狗的食品,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心情吗?如此不近人情之人,很难说不是奸邪狡诈之徒。
不过,据清代学者的考证,此作并非苏洵所写,而是后人的假造。但无论如何,该文用词之毒辣,已经远超客不雅观的描述,完备变成了人身攻击,凭什么说不讲究吃穿用度的人便是不近人情,便是奸邪狡诈之徒呢?
还有一些野史传闻,言辞更为夸年夜,现略举一二。
比如说他常年不沐浴,身上的虱子竟然爬上了胡子,而此时的王安石却浑然不觉,还在朝堂上专心地给宋神宗申报请示事情。
唉,大宋的子民可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会享受生活的人,据史籍记载当时公共沐浴池各处着花,洗一次澡不过花10文钱而已。可是当朝宰相却不沐浴,这让皇上的脸往哪搁?
假如换作我是皇上,必须下这样一道诏书:特赐王爱聊一池温水,着人脱去其衣冠及鞋袜,令他在池中好好沐浴,须体有余喷鼻香,方可进朝。钦此。有了天子的诏书,谅王安石也不敢违反。
还有说夫人看到他肤色黧黑,脸庞干瘪,担心他生病,便请来大夫看看,结果年夜夫尴尬地说大人没......没什么病,只是该沐浴了。
这种生活中的
这种心不在焉的习气在家如此,在朝廷中也一样。
北宋学者邵伯闻在《邵氏闻见录》里记载:大臣们应邀参加宋仁宗摆的\公众赏花钓鱼宴\公众,王安石不领情,坐在那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吃个精光。
对此,仁宗大吃一惊:如果没把稳到是鱼饵,误吃几粒也就罢了,竟然连一整盘都吃了,此人必定有诈。
02.
除了宋史,其它的记载是否属实呢?我个人以为夸年夜了,情由如下:
其一,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对付沐浴一事,并不仅仅是大略的个人卫生问题,而是一项主要的礼仪,官员必须遵守。
历朝历代,都有关于沐浴的记载。西周时规定官员必须沐浴后才能见天子,以显示自己的忠心。汉代还有沐浴假,官员每隔五天就要回家休沐。到了唐代,则将休沐从五日改为旬日一次。
生活安逸清闲的宋朝,该当对沐浴的重视比前朝愈甚。如有个资政叫蒲传正,此人在沐浴方面可谓奢华,讲究颇多。每天洗两次脸、两次脚,隔天洗个小澡,用百来斤热水,五六个人奉养。再过一天洗个大澡,用一百六七十斤热水,八九个人奉养。洗完还要涂脂搽粉,熏喷鼻香什么的。就连洗个脚跟都要两个人奉养,换一次热水,洗大脚要四个人奉养,换三次热水。
一个小官员沐浴竟然如此讲场面,摧残浪费蹂躏水资源。堂堂宰相王安石若长期不沐浴,不换衣服,难道皇上没有被他身上发出的酸臭味熏得掩鼻屏气吗?没有向他问不敬之罪?
可见,一些野史的记载不敷为信。
其二,沐浴业在宋朝已相称发达。
对付爱干净、懂享受的宋朝人来说,沐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城中各处是浴池,每天凌晨就挂牌业务,场中皆有男女家丁赞助泡澡搓背,形同本日的桑拿。
其三,如果王安石真的有
王安石由于实行变法,在朝中得罪的人不少。如果他的个人卫生真的到了脏、乱、差的地步,那些政敌岂能放过他?还能让他在朝堂上慷概陈词吗?就连出身官宦世家的窦元宾,由于体味不雅观观,彼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便在《归田录》大加讽刺,并为其取外号“窦臭”。
而对付王安石的不讲卫生,同朝文人的诗词中并沒有留下对他的讽刺。
可见,野史中的加载并不属实。宋史中说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性,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公众。这样的描述估计更客不雅观公道些。
崇尚俭朴生活的王安石不讲究吃穿用度,有点落拓不羁和不修边幅,但这样的毛病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后人放大,于是有了吃完一整盘鱼饵,让虱子高攀到胡子上的荒谬之词。想来这不过是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对他的恶意诋毁和以泄私愤罢了。
同为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对王安石的遭遇深表同情,他说作为百年不遇的精彩人士,却生前被众人求全谴责,去世后数代都不能洗刷骂名,在西方有英国之克伦威尔,在中国则有宋代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