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期间,一位叫孟郊的墨客留下一支千古传唱的《游子吟》,重新鲜的角度发轫,却唱出所有游子的心声: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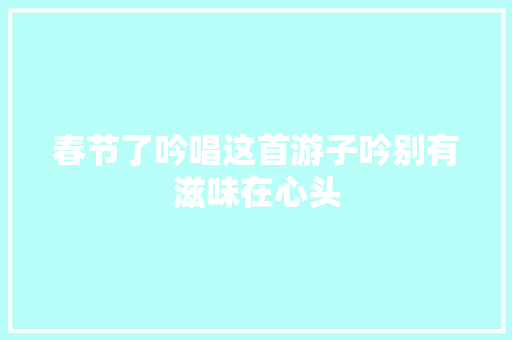
游子,看上去那么放浪不羁,洒脱豁达。而当表面精彩的天下不再引发他发达的豪情,当矢志追逐的梦想遭到现实无情的打击,他便开始体会出“出门一时难”的不适,加倍留恋“在家千日好”的温馨畅怀。
孟郊,字东野,不知是否应了人如其名的宿命,他的名和字,饱蘸太多荒郊野外的玄墨苦水,谱写了他客居他乡、贫苦潦倒的生平。因而,纵然拥有“郊寒岛瘦”“韩孟诗笔”等雅称的孟郊,诗才得与同时期的韩愈、贾岛等齐名,却多作苦吟之歌,内容多涉情面冷暖、民间苦难,又得“诗囚”一名。
一代诗囚,没有诗仙的飘飖轻举,没有诗佛的淡泊闲雅,更没有诗圣的端方肃穆,只有坎坷人生路上的凄风苦雨,困锁住一个失落意文人苦难重重的身心。
他于天宝十年出生于湖州武康的一户清贫人家,父亲任昆山县尉,仅是个俸禄微薄的小吏。寒门小户,更须要当家女主人的辛劳操持,吃穿用度都要亲力亲为。孟郊看父母为生活费力,从小就乖巧懂事。而物质资源的匮乏,更加重他性情孤僻的一壁,少与人交往。终年夜成人后,孝顺的他加倍感想熏染到,留在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人支撑,他必须出门探求空手发迹的道路。作为寒门士子,心中所思所想都更贴近大地。齐家方能治国,他的远游更多的是探求改进家境的路子。他游历四方,却无所遇合,无奈过了一段隐居生活。四十岁之前,他从河南流浪到江南,行踪不定,除了作诗之外没有其他行迹可考,也险些不可能真正照顾父母。“生平空吟诗,不觉成白头”,他写下的这一行名句,正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论语•里仁》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说的是父母健在的时候,子女应在家侍奉,纵然要出远门,也要有适当的情由。恪守家园、恭顺双亲的孝子固然有,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把目光投向了远方。虽然远游在外的儿女,做不到晨昏定省,时候照料父母起居,然孟子也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人作注:“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儒家贤人正好是在鼓励男子们走出家门去首创奇迹,为禄取士,从而光宗耀祖,更好地为父母尽孝道。
到贞元七年,孟郊四十一岁时,他回抵家乡湖州,举乡贡进士,动身进京参加科举,于次年和贞元九年两次下第。人到中年,却一事无成,第二次落第的孟郊倍动听生的挫败,满心的失落落困顿让他悲愤而叹:“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看到及第士子欣喜若狂又少年得志的风光无限,他早已失落去振作的信心。在他最失落意的时候,是母亲敦促他连续上京,重燃他生活的希望。十二年,孟郊奉母命第三次到长安应试,终于得进士及第。苦尽甘来的他留下生命中难得一见的快诗:
“昔日邋遢不敷夸,目前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春风得意”这一针言就由这位老夫子创始,这样一个略带轻佻炫耀之意的辞藻,背后却承载了数不尽的酸楚。登科的孟郊第一次感想熏染到了长安城的善意,这里的繁华美景,终于也有他的一份。欢畅过后,他不忘家中省吃俭用的老母,旋即东归,告慰父老乡亲。
孟郊没有想到的是,中举并非他否极泰来的人生迁移转变点。许是缺少显赫的家世,或者权贵的提携,他又开始常年流寓他乡,直到五十岁才得到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他的官位与父亲相较,没有任何进步,更谈不上光耀门楣。但他的收入也能让他置办陋室一间,薄田一亩,从此安居乐业,不用再漂流无依。
这时他想到远在故乡的母亲,母亲现在身体还康健吗,她还在为远行的儿子缝制冬衣吗?五十年的卑微,换来一朝衣食温饱,究竟不负父母殷殷栽培之苦心,拳拳哺育之恩典。在欢迎母亲到溧阳奉养的路途中,孟郊含着朴拙的温情和感愧,写下那一首五言古诗,赞颂了母爱的无私和深厚。
母亲,永久是儿女收成爱的源泉,她总是无微不至照顾她的骨肉,宁肯自己耐劳也不让子女受到一丝侵害。儿行千里母担忧,分别,应是母亲和子女最痛楚的时候,而游子离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作为母亲不能阻挡儿女远行的脚步,却又害怕他在表面受饿受冻,担心相逢之日遥遥无期。临行前,母亲只好不辞昼夜地缝制新衣,让儿女在远方也能感想熏染到家乡的牵念和温暖。子女,就像是路边微不足道的小草,如何能报答母亲如春光温暖和煦的大爱呢?
《游子吟》展现了平凡而伟大的人性之美,千百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推崇和共鸣。清朝,溧阳又涌现两位墨客延续孟郊的主题,再现母爱的动听:“父书空满筐,母线萦我襦”(史骐生《写怀》),“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彭桂《建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时至今日,母爱的颂歌还在连续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