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溪藏》的刊印发起人为密州不雅观察使王永从、弟崇信军承宣使王永锡等,主持人为思溪圆觉禅院方丈怀深、平江府大慈院方丈净梵、湖州觉悟教院方丈宗鉴(晒台宗人)等,《[嘉泰]吴兴志》载:“圆觉禅院在思溪,宣和中士人密州不雅观察使王永从与弟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创建,赐额为慈受(案:受,原文作爱)和尚道场。寺有塔十一层及有藏经五千四百八十卷,印板作印经坊。” [③] 刊印地点为宋两浙道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归安县松亭乡思溪村落(即王氏家乡)圆觉禅寺。
据《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载,宝庆二年(1226)“改湖州为安吉州”;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亦载“宝庆二年改湖州为安吉州”。南宋理宗时期,思溪圆觉禅院升格为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后,经版又经由修补,形成资福禅寺大藏经,并有目录《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传世。这个期间的印本称之为“思溪资福藏”,又俗称“后《思溪藏》”。而于圆觉禅院期间所刊,则称“思溪圆觉藏”,或俗称“前《思溪藏》”。《思溪藏》的圆觉藏部分每册经卷首尾两叶天头上均钤有一长方形墨印“圆觉藏司自纸板”。资福禅寺之施资补刊者紧张有“安抚大资相公”赵氏及当地的善男善女如大师祖印、陆六庵主、闵道超、李万十一娘等近200人。据《昭和法宝总目》所载《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的著录,其末了一个千字文号为“最”字,即《大藏经目录》二卷《大藏经律论等目录》下卷。资福禅寺期间,紧张对刊于圆觉禅寺的旧版进行了修补完善,李际宁通过勘对原刻及补刊,供应了例证,云:“该藏实在只有一套版片,只是后来经板破坏,故有后代修补经板一事。2001年之后的两三年内,中国国家图书馆先后从韩国私人手中转购到357卷'思溪藏'本《大般若经》。在鉴定这批《大般若经》的时候,我们以日本增上寺本为对照,比勘的结果,创造本经的版次与增上寺本基本相同,比如卷第四百零四,版心中刊有'卢道开舍''沉道禅舍'刊记,这样一些补版刊记,在增上寺本中保留了许多,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品中表示出来,解释它们与增上寺版全同,是一个版次。”“其余,中国国家图书馆原藏一册'思溪圆觉藏'本《大般若经》卷一百三十一,卷首卷尾钤有'圆觉藏司自纸版'墨印,这是当时圆觉禅院期间开版印刷的记录。而本次收藏 韩国本中,恰有卷一百三十一,两本相同卷次的印本,恰好为我们作比较研究供应了数据。比较往后创造,两卷的版本相同,惟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入藏者有补版,而原藏没有补版。由此,也为我们就'思溪藏'两版的关系,供应了主要实物证据,证明即'思溪资福藏'该当是在'思溪圆觉藏'根本上修整补刊经板而成。”[④]
至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蒙古大军南下,寺院、经坊被烧毁,《思溪藏》经版亦毁。虽然其详细的补版下限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修补下限韶光肯定在版毁之前。而至于详细修补何卷何叶,则须要校正多本才能定案。
《思溪藏》继续《崇宁藏》的装帧形式和版式,经折装,就全藏而言,基本版式为每版三十行,五半叶,半叶六行,行十七字;早期的圆觉藏亦间有每版三十六行折为六半叶者,每叶亦为六行,行十七字,每版四周单边。卷首多无题记,但仍留有空行;各册之末有音释(与《崇宁藏》随函音释办法不同)。版片号,凡每版六半叶者,皆在版缝间,凡每版五半叶者,皆在版端。其版片号次序,依次为千字文号、经名简称、卷次、版号。刻工姓名一样平常鎸刻于中缝下,间有鎸于卷首开篇篇题之下者,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五》之首篇顶格题“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三”下题“魏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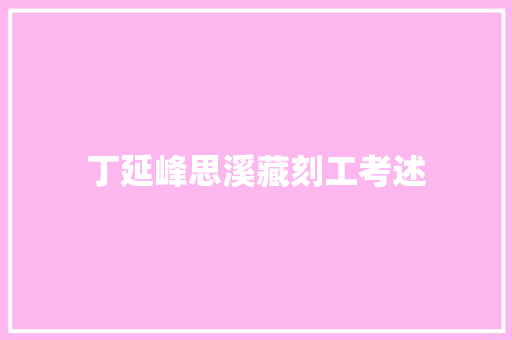
在对《思溪藏》的研究中,刻工是较故意义的研究内容之一。参与刊印《思溪藏》的刻工不仅人数多,且刊印了多部大藏经及其他书本,于南宋末北宋初浙江一带非常生动。刻工本来用于记录工钱的,但从版本研究的角度看,还具有鉴定版本之功效,借此可以鉴定零本及其他版本。有鉴于此,本文探源发微,力争摸清《思溪藏》刻工概况,使干系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刻工统计
今据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⑤] 、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野沢佳美《宋版大藏经刻工——宋版三大藏经刻工一览(稿)》[⑥] 及笔者目验部分卷次后,共辑录刻工564名,撤除疑似重名者(如虞集、毗陵虞集,陈世明、世明,付先、傅先,等等),亦有550余名。个中有不少单字刻工,这些单字险些全部包含在双字或三字、四字刻工姓名中,当是全称刻工的省称,故未再录。详细如下:
常秀、建州东阳陈异、陈意、陈璿、陈华、陈虞、建州东阳陈兴、陈达、陈哲、陈法、陈庚、陈高、陈杲、陈亨、陈景、陈具、陈吉、陈亮、陈六、陈立、陈明、陈宁、陈笵、陈起、陈全、陈文全、陈其、陈琪、陈玘、陈玘六、陈睿、陈山、陈绍、陈升、陈世、陈世明(世明)、陈皙、陈相、陈宣、陈轩、陈宵、陈印、陈植、陈彦、陈翊、陈沼、陈浩、陈诏、建州东阳麻川陈至、陈质、陈出、陈廋、陈沔、乘由、乘印、崔林、蔡吉、蔡子、蔡超、蔡迪、成安、成海、大王昌、道朗、董明、董奇、董玘、董阳、董旸、董珍(珎)、董羽、董济、董祥、杜海、杜济、丁禾、丁和、丁禾一、丁宁、法明、范间、范闿、范瑞、方广(広)、方浩、冯成、冯珹、冯立、冯立成(立成)、冯辛、冯芯、付里、付全、付先(傅先)、付忠、付奕、付充、富宗、高 、高桂、高起、高杞、高氏、高异、葛部、葛方、葛古、葛谋、葛韶、葛玘、葛洗、葛璋、葛诏、公安、公海、公禾、公咊、公聚、公宁、公荣、公升、公说、公天、公谐、公宣、公悦、公和、贡禾、官石、光说、浩吉、浩先、何全、何言、何中、何忠、洪吉、洪先、洪允、胡旦、胡明、胡升(升)、华才、华禾、华弈、华元、黄常、黄虞、黄官、黄俊、黄觉(斍)、黄文、黄文全(?)、黄奇、黄宪、黄祥、黄徐六、黄廿八、黄廿六、黄六、黄念六(念六)、黄旸、黄攸、黄元、黄珍、黄志、黄寿、黄俊、惠立、惠祥、惠志、吉涣、吉彦、吉元、渐立、蒋昌、蒋成、蒋城、蒋谔、蒋讫、蒋岳、金大、金华、金二、金荣、金义、觉奇、赖安、李陈、李成、李冲、李谔、李恭、李海、李羽、李胡、李加、李加谋、李嘉谋、丈人李九郎、丈人李四郎、李元、李茂、李湈、李谋、李妙、李敏、李明、李其、李竢、李询、李翊、李攸、李志、李艸、李仲、李孜、李秀、林宏、林济、林禾、林志远、林志道、林森、建州蒲城林和、刘祥、刘庚、刘仲、刘邦、芦(芦)典、卢(芦)广、芦(芦)王、卢兴、芦(芦)震、马明、马玘、马青、马寿(寿)、马辛、马珍(珎)、马志、马宗、马宗颜、马成、迈明、毛道、茂 、末林、谋吉、谋先、米信、米佖、牛吉、牛实(実)、牛贤、牛志、潘氏、裴浩、裴颜、裴中、裴忠、奇珍、钱明、钱竦、钱旸、钱晞、全荣、青二、青祥、青一、荣氏男屠、萨昌、思彻、孙佖、宋富、宋祥、宋华、宋俅、宋荣、宋庠、孙高、孙遘、孙立、孙莲、孙王林、孙轩、孙正、沉成、沉端、沉昴(升)、沉二、沉尚高、沉升、沉一、沉乙、沉益、沉监、沉益、盛立、施宏、施明、施宗、施门、石端、史才、史方、术立、竦睿、汤成、汤立、滕民、殄立、童济、童明、屠有、屠宥、屠宗、万成、万祥、万(万)澥、王补、王昌、王城、王成、王珹、王得、王德、王迪、王端、王二、王二秀、王官人、王桓、王仅、王茂、王玫、王明、王玭、王奇、王瞿、王荣、王睿、王三、王孙、王显、王雪、王雅、王义、王用、王宥、王有、王圆、王 、王珎、王震、王政、王宗、王祖、王益、王宽、王玖、王戌、王正、王相、王仲、卫昌、卫立、卫祥、魏信、翁禾、翁和、翁咊、吴安、吴安仁、吴庚、吴仁、吴伸、吴申、吴谐、徐阿四、徐高、徐杲、徐高阜、徐阜、徐庚、徐恭、徐光、徐广、徐贵、徐果、徐华、徐黄、徐朗、徐立、徐亮、徐免、徐民、徐明、徐玘、徐申、徐升(升)、徐瓦、徐辛、徐轩、徐雅、徐颜、徐义、徐秀、徐□秀、徐庸、徐载、徐珍(珎)、徐真、徐忠 、徐愿、徐宗、徐景、徐氏、徐茂、许亮、宣唐、玄祥、薛昌、严昌、严二、严六、严申、严氏、严明、严先、严信、颜行、颜宣、严言、严用、严志、杨宝、杨宾、杨迪、杨立、杨亮、杨明、杨实、杨寔、杨通、杨彦、杨益、杨茂、杨垓、羊宥、羊实(実)、羊寔、夭明、夭竦、夭晞、夭旸、夭渊、姚珍、叶迪、叶印、叶由、叶右、叶元、建安叶元、叶才、叶秀、叶宗、印祷、印蒋、印祥、印志、于成、于珹、俞成、俞原、俞尚、于迪、俞迪、虞集、毗陵虞集、虞俊、虞広、虞黄、虞宣、虞典、鱼保奴、鱼大娘、鱼李九娘、鱼李氏、鱼母唐三娘、鱼十八娘、鱼念六、鱼乙郎、鱼宗、鱼大宗、鱼宗亮、鱼大唐、翟完、章浩、章亨、章祥、章珍(珎)、章弼、章敏、张安、张帛、张伯中(伯中)、张海、张浩、张吉、张聚、张宁、张三、张升、张锡 张宣、张易、张悦、赵昌、赵宋、赵宣、赵宗、郑昌、智德、智得、中立、周富(冨)、周奇、周琦、周氏、周唐、周宣、周育、朱端、朱富、朱华、朱集、朱林、朱荣、朱寿、朱竦、朱王、朱五、朱宪、朱庠、朱一、朱乙、朱珍、朱寒、宗立、昊安、戋赐、枕一、郊昌、荀宪、唐宣、前昌、晋日、余宗、彬立、诃老、竦璿、熊伸、寸先、天澥、片全、正三、立徐忠、列伸、希晞、言周。
刻工如此之多,固已成为《思溪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概言之,这些刻工具有光鲜的特点。
首先,《思溪藏》刻工的刊雕生动韶光及籍贯等大致可以确定。根据以上刊记韶光及修补韶光的下限,这些刻工该当紧张生动于北宋末南宋初,而补修刻工则持续韶光较长,如果以版片毁掉之时为下限,则已至南宋中后期。但修补部分是鎸修补刻工姓名,或不鎸修补刻工仍存原版刻工,须与原版对勘方能逐一辨出。限于条件,不能逐一对勘,故只能将所见刻工一并移录,立此存照。由于版毁不存,如果修版时改换了刊工,也可以确定这些刻工生活在北宋末至南宋期间。
从《思溪藏》的刊记可知,其刊地为浙江湖州,这些刻工的籍贯该当紧张为浙江地区。但从某些刻工姓名所冠籍贯来看,亦有来自其他地区的,虽然数量不多,但毕竟存在。姓名前署籍贯的有6位,个中署建州的有四位,即建州东阳陈异、建州东阳陈兴、建州东阳麻川陈至、建州蒲城林和;署建安的1位,即建安叶元;署毗陵的1位,即毗陵虞集。
宋代的建州即今福建南平建瓯市,位于福建省北部,闽江上游。唐武德四年(621)始置建州,“福建”之名即为福州、建州各取首字而来。五代开运二年(945)改建州为永安军,旋改忠义军。宋开宝八年(975)改忠义军为建州,治平三年(1066)析建安、浦城、建阳县地置瓯宁县,绍兴三十二年(1162)以宋孝宗旧邸,升建州为建宁府(府衙驻今建瓯市),属福建路。从这些刻工署建州而不署建宁来看,可以判断其刊梓韶光当在绍兴三十二年以前,这与刊记所记韶光之下限至绍兴二年或稍后基本吻合。这四位刻工来自建州东阳、麻川及蒲城三地。两宋建州下辖建安、瓯宁、浦城、建阳、崇安、松溪、政和等7县,个中蒲城即今蒲城县,处于建州东北。东阳、麻川亦为建州所属,东阳既属建州,则非浙江东阳。建安亦属建州。可见,福建的这5名刻工集中来自于建州。宋代的毗陵即今江苏武进县。
可见从刻工属地来看,虽然以浙江地区为主,但至少有来自福建、江苏南北两地的刻工参与刊雕。尤其是福建刻工,在宋代北上参与浙刻本的不少,如宋淳佑六年(1246)姜文龙湖洲頖宫刻本《论语集说》十卷,版心鎸“建安余良”“建安游熙” ,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6053)。南宋绍定间明州刻本《[宝庆]四明志》,版心鎸“建安吴洪”“建安范□之”,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2360 )。亦有一些北上江西刻书,如宋淳熙九年(1182)丘崈江西漕台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版心鎸“建安周祥刊”,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6577 )。江西间隔福建建州更近,来往方便,这是地理上风。但由于整体上江西远不如浙江刻书多,以是北上浙江的刻工更多。
其次,统计刻工数量可知,《思溪藏》不仅在宋代五大藏经中利用刻工最多,也是所有宋刻本中刻工最多的。《开宝藏》仅存零卷十二卷,只记印工,不记刻工。《崇宁藏》刻工有440余人,印工有30多人。《毗卢藏》刻工及补刻刻工510多人,个华夏版刻工505人,补刊刻工10余人。《碛砂藏》刻工亦有500多人,但有不少是元代的。而现存其他非释家类宋刻本中更无5000余卷以上的大型丛书刻本,因此刻工数量亦远低于大藏经刻工。除此之外,《思溪藏》该当还有数十位印工以及大量的写工等,因不鎸其姓名,无法录出。如此数百人参与刊印这样一部特大型佛经,可以想见当时其场面之壮不雅观伟大。
饶故意味的是《思溪藏》刻工中,虽以男性居多,亦不乏女性刻工。如鱼大娘、鱼李九娘、鱼李氏、鱼母唐三娘、鱼十八娘等,当皆为女性。在百家姓中,鱼姓少见,《思溪藏》中涌现了10余人,如鱼保奴、鱼大娘、鱼李九娘、鱼李氏、鱼母唐三娘、鱼十八娘、鱼念六、鱼乙郎、鱼宗、鱼大宗、鱼宗亮、鱼大唐等,这是很值得关注的征象。这些鱼姓族人很可能因此家族形式共同参与。从鱼母唐三娘与鱼大宗、鱼宗亮、鱼大唐等姓名来看,他们或为母子关系。他们之间肯定还有其他关系,因无法供应进一步的证据,不敢妄语。信徒或普通百姓施帮助刊佛经,是一种虔诚、膜拜以求福禄龟龄消灾除难的行为,以求达到为长辈祈福、为家族其他成员祈求安然、或祝延圣寿的目的,因此每每以家族集体团队形式涌现,这在其他藏经及宋刻本中亦常常涌现。《思溪藏》中还有不少其他同姓刻工,是否存在某种血缘关系,亦待研究。
二、《思溪藏》刻工参与刊雕了《崇宁藏》《毗卢藏》
有些《思溪藏》刻工参与了《崇宁藏》《毗卢藏》的刊刻事情,今据野沢佳美《宋版大藏经刻工——宋版三大藏经刻工一览(稿)》及笔者所辑,将参与三藏刊雕的刻工致顿如下:
统计上表可知,三藏刻工有关联者96人,个中三藏悉同者3人(陈立、付先、林志远),《崇宁藏》与《毗卢藏》同者65人,《思溪藏》与《崇宁藏》同者14人,《思溪藏》与《毗卢藏》同者19人。
三藏的初刻或补刻韶光有接续或交集,因此同一批刻工参与刊刻是正常的。《崇宁藏》刊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政和二年(1112),刊地为福州东禅寺,东禅寺位于福州闽县易俗里的白马山上。此后在南宋高宗绍兴间、孝宗干道、淳熙年间、光宗绍熙间,又有修补、重刻和增刻。福州为宋代刻书重镇,聚拢了大量精良刻工,《崇宁藏》的刻工紧张来自于福建是天经地义的。《毗卢藏》刊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福州开元寺,此后在隆兴、干道、淳熙年间有过续刻,又在嘉熙、咸淳及元成宗大德年间有过修补。由于两经接续刊印,刊地皆为福州,以是先后参与两经的刻工达65人之多,实属正常。
《崇宁藏》刊刻之末了一年为政和二年,距《思溪藏》始刊年——靖康元年(1126)仅有14年,如果一位刻工有大约30年刊龄的话,先后参与两藏的刊雕是完备有可能的,但是由于浙江湖州与福州间隔尚远,因此数量当不会太多,检两藏刻工中姓名相同者只有14人(王昌、官石、叶元、叶才、沉端、石端、张海、陈宁、陈立、陈六、付先、刘仲、李其、林志远),个中只有付先一人参与了南宋初曾噩补刻本,其他皆为《崇宁藏》原刻刻工。这批刻工究竟来自于福建抑或浙江?须要进一步考证。如叶元,《思溪藏》鎸刻为“建安叶元”,则属建安无疑;沉端为南宋初杭州良工,曾参与刊刻南宋初刻本房注《管子》,等等。但由于《思溪藏》在后,故这批刻工该当紧张来自于福建。相较而言,《思溪藏》与《毗卢藏》的刊印韶光更为靠近且重合时间较长,因此同刻两藏的刻工相对较多一些,达19人(王荣、王觉、王成、王宗、王仲、王得、叶宗、张宁、陈彦、陈达、陈立、丁禾、郑昌、付先、杨寔、杨茂、李秀、林森、林志远) 。
从三藏的刊地及刻工籍贯来看,刊工自然当以福建、浙江两地为主,且两地皆为刻书重镇,刻工颇多,间隔较近者,流动方便,短韶光内聚拢大量刻工是一件非常随意马虎的事情。这些刻工以此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当然讲求本钱及效益,就近选择是自然而然的。但同时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刻工,《思溪藏》刻工参与前两藏的不多,仅有21人,远不如前两藏重合刻工多,紧张缘故原由是前两藏刊地间隔较近,而湖州与福州较远,刻工往来本钱较大。在参与《思溪藏》的刻工中,那些同时参与福州两藏的刻工有可能是北上的福建刻工,但也有可能是《思溪藏》刻工南下参与了两藏的刊刻,因此它们究竟是福建抑或浙江刻工似不易判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刻工并非固定一所,而是流动的,虽然北上或南下流动的数量不多。
三、《思溪藏》刻工刊雕其他刻本
《思溪藏》刻工集中生动于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浙江地区,因此在现存一些大部头的同期间浙江刻本中险些都能见到《思溪藏》的刻工,而且皆为多人参与,多者20余人,少者数人。同时,通过钩稽《思溪藏》和其他刻本的相同刻工,可以彼此进行旁证、互证、鉴定。下面列举一些实例。
(一)尚书正义二十卷,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撰。
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元修本,8册。今藏日本史迹足利学校图书馆。
原版刻工有王珎、王林、洪先、浩先、徐亮、徐茂、徐颜、李询,补修刻工有王政、王明、徐义、张升、陈浩、李仲、李其,先后共有15人同时参与刊刻《思溪藏》。
案:此本卷末有宋黄唐刊跋,云:“《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彚,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古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道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原版宋讳缺笔至“构”字,补版叶可见“慎”字缺笔。据黄唐跋,“壬子”即绍熙三年(1192),其刊年已靠近南宋中期,故这批刻工很可能参与了《思溪藏》的修版事情。
(二)礼记正义七十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撰。清惠栋跋,民国李盛铎、袁克文跋。
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40册。卷末有黄唐刻书跋,同足利学校图书馆藏《尚书正义》。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8640)。
原版刻工有王宗、王茂、李成、高异、陈彦、张升、严信、杨明、李茂等9人,参与刊刻了《思溪藏》。
(三)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
南宋初杭州地区刻宋元递修本,24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2353)。
刻工有徐升(升)、徐杲、徐茂、陈彦、王政、徐宗、宋俅、徐秀、余宗等9人,参与刊刻《思溪藏》。
案:此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着录为“宋初进本”。《中国版刻图录》着录为宋杭州刻宋元递修本,曰:“卷中刻工约分三期。孙勉、徐茂、徐升、陈明仲、徐政、张清、徐杲、余集、骆宾、毛谅、陈彦、陈锡、骆升、顾渊、包正、葛珍、张谨等南宋初叶杭州地区良工为第一期。石昌、金祖、丁松年、方至、朱春、童遇、曹鼎、凌宗、金荣、金嵩、陈寿、庞知柔、徐珙等南宋中叶杭州地区补版工人为第二期。元时补版工人张富、何建、余友山、滕庆、沉贵等为第三期。因知此书确是宋元两朝递修本。古人因卷七后有干德三年开宝二年订正官衔名,定为北宋监本,绝非事实。元时版送西湖书院,《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有《经典释文》一目,盖即此本。世传叶林宗影宋抄本与钱氏绛云楼藏宋本,均已亡佚,毛氏汲古阁旧藏宋刻本但存《春秋左氏传音义》一卷,此为今日仅存宋刻全本。” [⑦]《宋版书叙录》又有详考,“字体端庄,刀法严整,颇具浙刻风格……(据避讳)表明此书原刻、补版更未到宁宗赵扩之时。上述所有这些避讳征象可以使我们推断此书之刻和修补,大概都在南宋高宗至孝宗朝,即公元1127年至1189年之间,还处在南宋初中期。”“这些征象,解释南宋原刊时可能是缺笔避讳,而到递修时已嫡黄花,无须再避。”“……卷六'有敦'之敦亦不缺笔,表明光宗嫌名也不回避。解释此书之刻当在孝宗之时或更早。”又于刻工考曰:“个中毛谅、陈明仲、陈明忠、余集、余永、张清、徐政、孙勉、徐茂、徐杲、徐升、包正、顾渊等,都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的良工。徐政、徐升在绍兴九年(1139)为绍兴府开雕过单疏本《毛诗正义》;张清、徐政在绍兴二年(1132)为绍兴两浙庾司开雕过《资治通鉴目录》;包正、孙勉、毛谅在 宋初于杭州开雕过《礼记注》;顾渊、孙勉、毛谅、徐杲、包正在绍兴间参与过北宋本《史记》的补版;徐茂在绍兴间参与过两浙东路茶盐司《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的雕印事情。这些刻工又都在《经典释文》上涌现,表明《经典释文》亦应在南宋初年开雕,且开雕在杭州地区。” [⑧] 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丁瑜跋曰:“字体方正严谨,犹是南宋初年风格。间有板框大小不一,字体较松软者,为后世补版。” [⑨] 在《思溪藏》中,这9名刻工未署他籍,当皆为浙籍刻工无疑。
(四) 群经音辨七卷,宋贾昌朝撰。
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学刻宋元递修本,6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2355)。
刻工有金荣、李敏、李茂等3名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据宋绍兴十二年(1142)汀州宁化县学刻本卷末绍兴九年临安府重刊记云:“临安府府学今将国子监旧本重雕,逐一校正,即无舛讹,绍兴九年五月日。”可知临安府确曾刊印过此书,且临安府本之祖本即北宋国子监本。又,宁化县学刻本卷末所载王不雅观国后序云:“绍兴己未夏五月,临安府学推明上意,镂公《音辨》,敷赐方州……”“己未”即绍兴九年(1139)。此本在流传过程中,有关临安府刻书证据均已佚去,借汀州本可证此事。此本于三刻中既非首刻,亦非汀州本,故当即此绍兴府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郡府学本”下即题“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皕宋楼藏书志》及《仪顾堂续跋》题同。故各家著录是本为绍兴九年刊印,确为可信。据此,这3名刻工生动于南宋初期,很可能亦为浙籍。
(五)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民国曹元忠、郭蛰云、沈曾植跋。
北宋刻宋元递修本,40册。今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A921.13 066)。
刻工有张宣、张安、张聚、陈浩、陈吉、陈彦、许亮、赵昌、吴安、孙立、金荣、汤立、徐雅、徐真、沉成、牛贤、牛实、王珎、宋荣、赵宗、徐忠、徐升、徐杲、徐高、徐茂、陈哲、陈全、印志等28人,参与刊刻了《思溪藏》。
案:《双鉴楼善本书目》着录为“北宋淳化本”。赵铁寒《北宋刊五种〈史记〉版本辨正》定为“淳化初刊,景德复校,南宋补刊本。” [⑩] 沈曾植跋又有详考,曰:“此为北宋最初监本无疑,而或以避讳至仁宗,疑为景佑本;又以老子升列传首,仞为大不雅观往后本,实在不然。检全书刑字刓行修正极多,若景德、景佑校后重刊,不应有此痕迹。据《玉海》'淳化校三史'条,具列淳化分校、咸平覆校、景德刊误、景佑校正诸诏令,而标题曰'淳化校三史',后注云'今所行止淳化中定本';'景德群书漆板'条云'太宗朝摹印司马、班、范诸史'。但是此为淳化监本,屡经刊正后之印本,即世所称景佑本。《汉书》亦是淳化监本之经修正者,景佑诏明言改旧摹板,不言重刻。若咸平重校四经,则直言重刻矣。又以南监所存南宋本集解照之,不惟行字数同,幅之高广,字之构造,无不同者,直是翻雕此本。南监本 是南宋监本,《玉海》谓'今所行'者也。向读《玉海》此条,颇有蓄疑,见此刻本,涣然冰释,古本名贵在此。”又曰:“北宋监本《史记集解》,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六七字。避讳至'恒'字、'贞'字,而'贞'字似有刊改之迹。《殷本纪》'炮烙'作'炮格',然'格'字较高下字略瘦,疑亦经刊改。傅言此本行款字体均与士礼居藏景佑本《汉书》同。内府有宋景德刊本《汉书》,此本避真宗讳,不避仁宗讳,题景德为是。配元刻,有索隐本,每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大小同。鱼尾上有'饶学''饶路学''饶泮'字。” [11]《宋本刻工姓氏》题“宋景佑监本”。仁寿本题作景佑本。曹元忠跋仁寿本时题为“北宋本”,谓一是行格与涵芬楼藏北宋景佑本《汉书》同;二是刻工张珪、胡恭、钱真、屠亨、陈忠、屠武、陈吉等亦与景佑本《汉书》同;三是“桓”字均缺笔。又《老子列传》置于卷首,当为政和补刻本(据徽宗命升老子置于列传卷首,诏书有“其旧本并行改正”)故定此本为“北宋景佑监本政和补刊本” 。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亦曰:“此景佑覆刊本,以常熟瞿氏、松江韩氏藏北宋景佑本前、后《汉书》,乃翻刊淳化干兴监本例子。盖出淳化本也。《汉书》版心下记刊工姓名,有张珪、胡恭、钱真、屠亨、陈忠、陈吉诸人,与此本同,知此本与瞿藏《汉书》为同时所刊。然《老子传》居列传之首,则政和间又有补刊矣。此本南渡后有覆刊本,历宋元明三朝尚存于明南雍,《南雍志》所称中字《史记》,即指覆刊本言之。至真北宋本,则除江安傅氏藏一之残帙外,世无第二帙也。” [12] 尾琦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书志》通过对刻工的稽核,认为刻工有6人见于南宋初,因题北宋末南宋初刊南宋前期修。但原版中间有剜去一段笔墨进行补版者,刻工即为补版时候工。《〈史记〉版本研究》以为“尾琦康所说的见于南宋前期文籍中的刻工姓名,正是在此类型中。且此六名刻工,仅是原版刻工的十分之一。因此,不能以此为据,而定此本于北宋末南宋初刊刻。” [13] 张玉春通过各本比对及征引史料、避讳、刻工等方面,综合考证,认为此本“景佑年间对淳化版校正后的重印本”,即不是重刊淳化本,而是对淳化本修版后的重印本。关于补版问题,劳干曾依据版页新旧及刻工、避讳对原版、补版作了区分,认为“旧版较富于同等性,而新版则不尽然,亦可知旧版为一次大规模鎸刻而成,新版则有随时补版之痕迹也。” [14]《〈史记〉版本研究》又曰:“至于补刻,如劳干所说:'新版有随时补版之痕迹',即非一时所补,补版讳钦宗名'桓'字,英宗嫌名'树'字、濮王名'让'字、高宗嫌名'购'字亦时有缺笔,独孝宗名'昚'字别体'慎'字皆不缺笔,光宗以下各朝帝名亦无一缺笔。又此本补版刻工多与绍兴二年越州刻《通鉴》相合者,如史彦、王珍、徐升、徐高、毛谏、宋俅、黄晖、陈彦、牛实诸名。而此诸名亦有见于绍兴四年刊《吴郡图经续记》者,故此本之补版应不晚于南宋高宗期间。”“此本为淳化本的补刻本,保留了淳化本的原始形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史记》刻本之一。” [15]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题“北宋刊递修本”,傅斯年、劳干均题“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 [16] 。综合以上诸见,此本当着为北宋刊南宋初修补本。个中参与刊刻《思溪藏》的这部分刻工皆为南宋初补刻刻工。
(六)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
宋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宋元明初递修本,40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8654)。
原版刻工陈彦、杨垓、俞尚、李秀、叶才、吴伸、杨明、李成等8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此本曾为汲古阁毛氏、士礼居黄氏旧藏。古人曾定此本为蜀刻本,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着录曰:“蜀今年夜字《史记》。有缺,有签头三条云:蜀今年夜字《史记》。宝光陆离,真奇物也。此未尝定价,惟先生长西席酌量之。”《百宋一廛赋注》和《爱日精庐藏书志》着录同一行款者均题“蜀大字本”。钱大昕《竹汀师长西席日记钞》曰:“晤黄荛圃,不雅观宋蜀本《史记》,每半叶九行,行十六字或十七字,有《集解》无《索隐》,卷末有'无为军学教授潘旦校正,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开雕'字,官衔分旁边,盖南渡初官本也。” [17] 周叔韬《宋刻工姓名录》着录,并题“蜀本?”,可知颇有疑惑。
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录》着录此本,据衔名宦地,对古人所云“蜀大字本”提出质疑:“曰无为军、曰淮南路,均不在蜀境之内。今眉山七史宋刊卷叶犹有存者,其每行字数为十八,与此之十六字亦有不同。余非敢谓前人为误,特未得其佐证,不能无所疑惑耳。” [18] 故题为南宋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着录为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宋元明初递修本。据刻工皆为南宋初中叶杭州地区及衔名等,故定为宋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当是。
(七)汉书一百卷,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元倪瓒跋,明周良金校,清黄丕烈、顾广圻跋。
北宋刻递修本, 40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9592)。
刻工有陈吉、宋庠、徐真、赵昌、陈浩、陈彦、徐高、王震、陈全、宋荣、洪吉、许亮、施明、张聚、牛贤、董明、张宣、徐雅、沉成、宋俅、张安、汤立、印志等23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中国版刻图录》着录为“北宋刻递修本”“疑杭州或福州”,曰:“字体宽博,清代学者钱大昕、王念孙所谓北宋景佑监本《汉书》,即指此书。但原书是否景佑间刻,却是问题。此书嘉道间黄丕烈家,《百宋一廛赋》着录。黄氏别藏一本,内多补版。补版刻工程保、王文、孙生等人,绍兴十九年又刻赌咒开元寺毗卢大藏。程保等既是南宋初年人,则此书原版刻于北宋后期,即据北宋监本覆刻,而非景佑监本,当是事实。此书《五行志》后有对勘官福州昌乐县主管劝农公事刘希尧衔名一行,更证以明正统八年福州有此书翻刻本,因疑此本当是福州官版。又案此书刻工牛实、徐高档,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区名匠,徐雅、汤立、洪吉、董明等,绍兴初又刻思溪藏,于此见闽浙两地刻工,可配合尽力。此书究为何时何地刻版,尚待后证。百衲本二十 史,即据此帙影印。” [19]《中华再造善本》收入,陈红彦所撰《提要》曰:“的确如此,第一,本书的刻工牛实、董明、徐高档,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区名匠,既生活在南宋初年,故此书不可能刻于百余年前的景佑年间。第二,本书避讳字仅至钦宗名讳桓字,而此后的高宗赵构的构字未见避讳,亦可证此书刻于北宋末年比较恰当。故此书实为据北宋监本覆刻的版本,刻于北宋末年,或已进入南宋初年,而不是景佑刊本。” [20]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通过大量刻工比较剖析,云:“可证此四史之刊刻韶光,不在景佑或咸平,而在其后百余年,两宋之交。” [21] 从版刻韶光上看,此书乃覆刊于北宋末南宋初,并非景佑原刻;而于刊地上由于刻工两地皆有,究竟为杭州或福州,尚需进一步研究。但不管若何,此书由两地刻工“配合尽力”而成,则是不争事实。至南宋初,刻工流动亦是常态,这从《思溪藏》中亦有福建刻工可知。
(八)汉书一百卷,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
宋绍兴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存七十七卷,57册,今藏上海图书馆(863256-312)。
刻工有王荣、王成、王政、金华、洪先、徐颜、沉升、董明、李仲、刘仲、王珎、李询、高异、徐高、沉一、徐茂等17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此本为残本,尚缺二十三卷。全书刻工同于《思溪藏》者,可能还要多一些。
(九)后汉书九十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
北宋刻递修本,存一百一十五卷,38册。中国国家图书馆(6729)。
刻工有王仲、王真、王荣、徐真、张安、许亮、印祥、洪吉、赖安、徐雅、宋俅、徐高、徐杲、杨明、徐茂、陈彦、牛实、孙立、宋庠、董明、王珎、陈明等22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十)后汉书九十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
宋绍兴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明递修本,存六十卷,17册。静嘉堂文库(一函六七架,《图录》着录号22)。
刻工有林志远、王荣、陈彦、陈兴、陈至、杨垓、李秀、刘仲、王永从等9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个中刻工有王永从,是否即《思溪藏》之刻书发起人,待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7345)中又有王仲、杨明2人,亦参与刊雕《思溪藏》,故参与过《思溪藏》的刻工至少十人。
(十一)唐书二百二十五卷,目录二卷,宋欧阳修、宋祁等撰。
南宋初刻本,存一百九十七卷,90册。静嘉堂文库(二函一九架,《图录》着录号35)。
刻工有卫祥、王益、王昌、王真、王震、王成、王祖、王端、华元、虞集、吴谐、周富、李孜、李敏、李谋、李攸、钱旸、严先、董明、董旸等20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皕宋楼藏书志》卷十九及《宋元本行格表》《静嘉堂汉籍目录》《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史部等均着录为北宋嘉佑间刊本,《仪顾堂题跋》卷二曰:“仁宗以上讳'匡'……等字皆缺笔甚谨,不及英宗以下,盖嘉佑进书时刊本也。” [22] 《静嘉堂秘籍志》卷四着录为“北宋杭州刊本”,并据避讳,定为“宋仁宗时刊本也”。《静嘉堂宋本书影》题宋嘉佑刊本。《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着录曰:“此即世所称嘉佑本也。北京图书馆藏有残本,与此本正同,均有补版。此宋印本补版差少耳。” [23]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题北宋嘉佑年间刊南宋配补本。以上着录当非。《正史宋元版研究》题南宋初期刊本,补配六卷为元天历二年覆宋本,当是。《静嘉堂图录》着录为宋绍兴刊南宋前期修,并题配本为南宋中期刊建安魏仲立刊本。检其刻工大都为南宋初期,如王介、王成、江通、吴邵等曾参与刊印绍兴间两浙东路刻本《外台秘要方》,章中、章立、章彦、董易等曾参与绍兴间刻本《景德传灯录》。
(十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宋司马光撰。
宋绍兴三年(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116册。中国国家图书馆(12358)。
刻工有徐升、王政、董明、牛实、朱富、朱集、徐广、高起、王明、陈达、陈彦、黄斍、洪先、宋俅等14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资治通鉴》成书后,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下杭州镂板,此为首次刊刻。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复将此与《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三书合之再刻行世。此本所列衔名均为嵊县、余姚两县进士、学官及簿、尉等,而国图藏傅增湘旧藏本(2461)有此本脱佚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衔名及“绍兴二年七月月朔日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刊板。绍兴三年十仲春二旬日毕工,印造进入”牒记。据此可知,此本当即宋绍兴三年(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其刊地为绍兴,曰:“慎字间有剜去末划痕迹,知是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字体方整憨实,刻工皆南宋初叶杭州地区习见之良工,与同时所刻他书多同。卷末原有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订正官衔名,此本脱。宋时建本、鄂本、蜀本都直接间接从此本出。此书元丰监本久佚,此为硕果仅存之第一本。” [24] 绍兴与湖州同在浙江,间隔不远,故此三书中同名刻工甚多,而参与《思溪藏》刻工亦多。
(十三)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宋司马光撰。清莫友芝题记。
宋刻宋元递修本,12册。今藏台北汉学研究中央(01731)。
原版刻工张升、章珍、黄觉、董明、宋俅、牛实、高起、朱集等8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菦圃善本书目》卷一、《台湾公藏宋元本联合目录》、《“国立中心图书馆”宋本图录》和《“国立中心图书馆”善本书目(1986)》均题宋刊本,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着录为南宋初刊宋元递修本。《修订本馆善本书目讲授—史、子部》曰:“本帙有宋元修补版,原刻版中又有部分之修补。版心白口,单鱼尾,上象鼻处,原刻、宋修皆不记大小字数,元修则记大小字数。就避讳字言之,原刻缺笔至宋高宗之构字,孝宗之慎字则不缺;补刻之慎字,或缺或不缺。光宗以下之讳字,惇、敦等字原刻修版俱不避。就刻工而言,则全为绍兴至孝宗朝杭州圈内之刻工。综合上述,本帙修正为'南宋初刊宋元递修本'。” [25] 据刻工、避讳、行款、字体等,此本实与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同刻。
(十四)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宋司马光撰。
宋绍兴三年(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宋元递修本,14册。中国国家图书馆(866)。
刻工有王明、高起、李仲、牛实等4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着录为“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又曰:“薄皮纸印,颇豁亮清明。……此与余藏百衲本《通鉴》中第一种绍兴浙东茶盐司本同。” [26] 傅氏所指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三年(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12358),此两书与《目录》为同时同一机构(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所刻,故刻工多同。此书虽无刊记明证,但从其书之字体风格、刻工均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等来判断,同为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所刻无疑。赵万里、李致忠均持傅氏之说。
(十五)管子二十四卷,春秋管仲撰,旧题唐房玄龄注。清黄丕烈、戴望跋。
宋刻本,12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9601)。
刻工有牛实、沉端、严志等3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着录曰:“皮纸精印,完全如新。首列大宋甲申杨忱序。卷末有张嵲《读管子》一篇,有绍兴己未从人借得,改正讹谬藏于家之语,盖南宋初刊本。” [27] 《中国版刻图录》着录曰:“宋讳桓、沟等字不缺笔,笔墨多经后人描失落。刻工杨谨、金升、李恂、张通、乙成、李懋、昌旼、牛实、沉端、严志等人,皆绍兴间杭州地区良工。审其字体刀法,当是南宋初叶浙刻本。”[28]
(十六)外台秘要方四十卷,唐王焘撰,宋林亿等校。
宋绍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42册。静嘉堂文库(《图录》着录号64)
刻工有王成、徐颜、徐杲、徐高、徐升、赵宗、陈浩、董明、李成等9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此本目录、卷一、三至五、七、十、十四、二十三等末有“右从事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赵子孟订正”、卷二、六、八、九、十一至十三、十五至十九、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三至三十八等末有“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订正”、卷九等末有“朝奉郎提举药局兼御医令医学博士臣裴宗元校正”、卷二十二等末有“从事郎充两浙东路茶盐司干办公事赵孟订正”等校正衔名;刻工徐政、徐高、丁珪、余全、阮于、赵宗、李忠等均为南宋初杭州地区刻工,尝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旧唐书》等多种两浙东路茶盐司主持刊刻的书本。又,是本“慎”字不避,知其确刻于高宗朝绍兴间。此本今存多部,个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9373),《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刊地为绍兴,曰:“卷后有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赵子孟订正、张寔订正各一行。刻工徐政、徐高、阮于、章楷、徐升,绍兴九年又刻《毛诗正义》,《毛诗正义》为绍兴府刊,二书正同时同地刻本。”[29]
(十七)东坡集四十卷,宋苏轼撰。
宋刻本,存二十三卷,12册。日本公函书馆藏(重2-3)。
刻工有王政、朱富、李询、周宣、陈兴、徐高、黄常、李元、徐忠、章珍等10人,参与刊刻《思溪藏》。
案:此本曾被古人误作北宋椠本,如《宋人刻工姓氏》题“干道本”。宋讳缺笔至“慎”字,“敦”“廓”不避,当刊于南宋孝宗韶光。《宋人别集叙录》卷九着录作“孝宗时刊每行二十字本”,当是。1929年,傅增湘曾目验一过,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断为杭本,曰:“此本行款版式与余所见宋刊数本皆不同,审其结体方整,雅近率更,自是南渡往后浙杭风姿。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述东坡集刊板有杭本、蜀本、吉本之别,此断为杭本无疑。” [30 ] 检其刻工,如李宪、李师顺、洪坦、宋圭、宋昌、赵通等均曾参与刊刻南宋浙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亦缺笔至“慎”字。如蒋晖、周彦、李宪、李师顺、高彦、宋圭、宋昌、陈昌等又见于宋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刻本《史记集解》。此为淳熙三年张杅守广德时,据蜀小字本重刊于桐川郡斋,刻工皆为浙江地区良匠。桐川,即今安徽广德县。广德东临苏杭,而距湖州最近,刻工往来方便,这批刻工紧张生动于南宋初浙江地区,为了刻诗人计,往来与广德、杭州、湖州等地,亦属正常。
(十八)文粹一百卷,宋姚铉辑。
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本,42册。中国国家图书馆(10726)。
刻工有陈明、牛实、何全、王成、董明、徐真等6人,参与刊雕《思溪藏》。
案:此本卷首有临安府开雕题记及衔名,云:“临安府今重行开雕唐文粹壹部,计贰拾策,已委官校正讫。绍兴九年正月日。”宋讳缺笔至“构”字,与刊年相合。
类似《思溪藏》中成批刻工刊刻同一书的例子尚有很多,个中有的是残本,而已经亡佚的则无法统计。若就当时刻书实际环境而言,肯定还有大量《思溪藏》刻工同刻他书的征象,本文仅从经史子集中各检数例而已。从单个刻工来看(当然亦和其他刻工同时涌现于同一书中),涌现10余次的很多,如陈达、陈高、陈立、陈明、陈彦、陈浩、董明、高起、洪先、李成、蒋成、金华、李元、李茂、李洵、李仲、李秀、牛实、刘仲、王成、王明、王荣、王显、王祖、吴仁、徐高、徐亮、徐茂、徐义、徐宗、徐明等,而牛实、陈彦、董明等则涌现20余次,解释这些刻工在当时非常生动,刻书浩瀚,刊雕效率很高。毫无疑问,他们因此此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刻手。
上列各书有的刊年非常明确,尤其是南宋初绍兴间某年刻者,其刻工的刊雕时限可以确定无疑是在北宋末南宋初,由此可以反证《思溪藏》刻工亦在同一期间。而有些不能确定刊年的刻本,因大量刻工相同,则可据《思溪藏》刊年确定该本的大致刊刻韶光。总之,依据刻工相同可以互证、旁证,皆可起到进一步考定刊刻韶光及刊地的浸染。刻工之用,可见一斑。
四、利用刻工鉴定《思溪藏》零本
由于《思溪藏》绝大部分不鎸刊记,因此零本的鉴定非常困难。刻工则为鉴定版本供应了坚实的证据。譬如下列个案:
(一)众经目录五卷,隋仁寿年翻经、隋释彦琮撰。
宋刻本,5册。“席”字号。今藏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
每折六行十七字,高下单边。刻工有丁宁、付先、王政、徐珍、徐华、陈山、杨寔、冯辛、冯成、高起、赖安、赵昌、董旸、严信、天澥等15人,悉同《思溪藏》。
案:《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着录为宋版,未言是否《思溪藏》。此为石井积翠轩文库外流善本,后为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天理图书馆《善本写真集》《稀书目录》均着录,未言其为《思溪藏》。直到阿部隆一《天理图书馆藏宋金元版本考》[31] 始着录为《思溪藏》经版。又,《安吉州思溪法宝藏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卷下《众经目录》五卷之千字文号为“席”,此本正作“席”字号。
(二)出曜经三十卷,姚秦竺佛念译。
宋刻本,存一卷,1册,卷十八乐品第三十一,“殿”字号。今藏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BQ1373.C6C48)。
每折六行十七字,高下单边。刻工有吉彦、王政、宋荣、宋俅、叶印等5人,悉同《思溪藏》。
案:《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目》题宋刻本,谓“按此本每纸右端接缝处鎸有千字文编号、书名、卷次、叶次及刻工,因与前纸左端粘接,被覆盖于内,故不易创造。上海图书馆亦藏有同版卷十五一册,为《广演品》第二十五,卷端鎸'殿'字编号,因纸缝尚固,刻工不详。” [32] 由于刻工未详,故未敢肯定是《思溪藏》。其后《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图录》题“宋靖康元年至绍兴二年两浙路湖州王永庆兄弟一家施刻《思溪藏》本”,盖因揭出刻工始定为《思溪藏》本。
(三)中阿含经六十卷,东晋释伽提婆译。
宋刻本,存一卷,1册,卷二十三,“兴”字号。今藏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
每折六行十七字,高下单边。刻工有何忠、何全、严昌、周育、李仲、朱富、章珍、章祥、公禾、许亮、杨亮等11人,悉同《思溪藏》。
案:《天理图书馆稀书目录》着录为宋版,《天理图书馆藏宋金元版本考》着录为思溪版藏经。艾思仁曾致函作者云:当存疑。然自刻工悉同看,其为《思溪藏》本当不容有疑。又,《安吉州思溪法宝藏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卷下《中阿含经》六十卷之千字文号为“薄早起温情似”,此本正作“兴”字号。
以上及近年来拍卖会上时常涌现的零本,起初不敢确定是否《思溪藏》本。刻事情为直接证据,结合千字文号、字体等其他手段,对剖断其为《思溪藏》本起了关键浸染。
在检索刻工过程中,当然也不用除有重名者,如宋蜀刻大字本《苏文忠公函集》四十卷,刻工张宣在《思溪藏》中亦涌现,显然并非同一人。在南宋时期,从川蜀到浙江路途迢遥,以当时的条件当不会如此远行执业。而浙江良工张宣与其他数十位刻工同时参与刊刻了北宋末浙刻本《史记》《汉书》等,当是同一人无疑。由于同一批刻工涌如今多部书中,一样平常不可能全部重名。基于此,笔者在以上列举个案、检索刻工时,亦遵照关注数人、数十人的成批刻工而不举单个或低于三个刻工的原则。因此确定《思溪藏》刻工也刻雕了其他书本,当是可信的。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思溪藏》中有一刻工为李嘉谋(或加谋),曾刊过宋绍兴十一年(1141)刻本《金园集》三卷一册(宋释遵式撰,释慧不雅观重编),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403.49)。此本无序跋,卷末端题后有刊记曰“圣宋绍兴辛酉孟秋圆日刊板”,其后又有四行题字:“郡人李嘉谋刊字,弟子沉玠助缘,法孙子宣助缘,法孙师普敬(缺末笔)书。”其后又有“请神照法师住东掖山疏”,顶题“杭州灵山传教梵衲遵式(次行顶格)谨裁简染疏寅请本如座主于台州东掖山承天院,永久传唱,晒台大教奉用祝延圣祚,保安州县军民。”疏文顶格,疏文末两行署题“天禧元年正月日疏”“杭州灵山方丈传晒台教不雅观梵衲遵式”。据此,将此本定为绍兴十一年(1141)杭州刻本,并无疑义。此本版心下不鎸刻工姓名,但卷末题记中“李嘉谋刊字”如斯,解释此本为其一人刊字雕版,其活动韶光、地点为南宋初杭州地区。这与《思溪藏》的刊时刊地同等,当即《思溪藏》刻工李嘉谋无疑。《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释氏类着录《金园》《天竺》二书,各三卷。《文渊阁书目》卷十七着录《金园集》一部一册,又《天竺别集》一部一册。今日本《续藏经》收入此书,且《天竺别集》卷下亦题“圣宋绍兴辛酉仲秋圆日刊板”,则此别集与《金园集》当亦为李嘉谋刻之,韶光上一在“孟秋”,一在“仲秋”。《金园集》的行款为十行二十一字,与《思溪藏》之六行十七字迥然不同,可知其为单行本。这些刻工刊雕类此释家类单行本切实其实定还有不少。
综上,《思溪藏》刻工浩瀚,是迄今为止所见宋椠诸本中参与人数最多的单刻本。《思溪藏》刊于湖州,刻工自然以浙籍为主,当然亦有少量南方福建刻工。这批刻工不仅刊刻了《思溪藏》,还刊印过《崇宁藏》《毗卢藏》,同时刊雕了不少非释家类刻本。就刻书种类而言,遍布经史子集,覆盖广泛,个中尤以刊雕大部头的经史原典为多。他们紧张生动于北宋末至南宋初,有的延至南宋中期。利用《思溪藏》刻工,可以鉴定其他刻本的刊雕韶光或地点,当然其他刻本的刻工亦可反证《思溪藏》,这种互证供应了更多的鉴定版本资源,使版刻原始真面更加清晰。
注释:
[①] 见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岩屋寺藏《思溪藏》本卷。
[②] 日本京都南禅寺收藏《第贰回大藏会陈设目录》,大正五年(1916)十一月。
[ ③ ]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卷第557号,《<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台湾成文出版社,1984年,第6796页。
[ ④ ] 李际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思溪资福藏”概述》,程焕文、沉津、王蕾主编《2014年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45页。
[ ⑤ ] [日]尾崎康着,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29-30页。
[ ⑥ ][ 日]野沢佳美:《宋版大藏经刻工——宋版三大藏经刻工一览(稿)》,《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110,1999年9月。
[ ⑦ ]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11页。
[ ⑧ ] 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244-245页。
[ ⑨ ] 丁瑜:《经典释文跋》,《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卷末。
[ ⑩ ] 赵铁寒:《北宋刊五种<史记>版本辨正》,《大陆杂志》23卷,1961年第2、3期。
[11] 此第二篇跋未在原书上,见《海日楼书录》,《历史文献》第16辑;亦见《海日楼群书题跋》,中华书局,2017年,139页。
[12] 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中心研究院历史措辞研究所专刊》10,1932年。
[13]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117页。
[14] 劳干:《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历史措辞研究所集刊》(18册),中华书局,1987年,497页。
[15]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117页。
[16]国立中心研究院历史措辞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历史措辞研究所集刊》(18册),中华书局,1987年,488页、497页。
[17] 《钱大昕全集》第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31页。
[18]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8卷·古籍研究著作·宝礼堂宋本书录》,商务印书馆,2009年,34页。
[19]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8页。
[20]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编著:《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159页。
[21] [日]尾崎康着,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47页。
[22] [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中华书局,2009年,45页。
[23]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186页。
[24]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20页。
[25] 李清志:《国立中心图书馆馆刊》第20卷第1期,1987年6月。
[26]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203页。
[27]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483页。
[28]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11页。
[29]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20页。
[30]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971页。
[31] [日]阿部隆一:《天理图书馆藏宋金元版本考》,《阿部隆一遗稿集》第1卷宋元版篇,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汲古书院,1993年。
[32] 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编:《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38页。
注:本文揭橥于《文津学志》第12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来源:书目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