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辜负、被侵害后无法得到道歉的人该若何连续生活,那些余生被彻底剥夺了快乐的可能性的人生要若何消化,这是文艺作品常表现的主题。既然没有道歉也就没有资格体谅,这是施加于受害人的不可化解的精神暴力,就如电影《密阳》里那个杀人犯先行的自我宽恕所导致受害者母亲的精神崩溃,这种覆灭性的疼痛来自于尖锐的抵牾对立和显而易见的对善的吞噬和取消,因此格外震荡也相对随意马虎捕捉到恶的肆无忌惮。
相对不雅观之,常小琥更多去书写那些有负于人而无法给出道歉或没有能力补过的人生,与其说他们怎么做都是错的,不如说就没有留给他们做对的选项,作品因此预留了难以全然责备的道德余地和伦理空间。《大狗》里权力与人情的纠葛,龃龉出一个关于辜负的故事。大狗辜负的是秃子一家对他的信赖,其值得书写的意义就在于信赖二字的重量,在一定意义上信赖是比倾慕、讴歌更深刻、更厚重的关系,是人主动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最可靠依托乃至请托,“是一种名贵的礼遇”。以是,大狗深知他亲手断送了一种更为天然深厚、比秩序更具有前缘性与合理性的情绪代价,以是他只有用回避来缓冲辜负带来的愧疚。至于行文上些许语焉不详导致无法很好地理解大狗行为动机的断裂(为何直接欲意取其性命),是某种构思上的疏漏还是故意隐蔽,那或许是另一个层面关乎于“能写”与“不能写”的问题。
《穿心莲》和《唱吧,吉米》是小说集中用笔、用情较为平均的两篇,也都是有关家庭创伤与亲子关系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都“承受着海底一样的压力”,比常见的一地鸡毛更重更彭湃,也比所谓正常家庭里的日常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两相对照,不免斟酌,到底是两个子女(焦海莲、吉米)更不幸,还是两位父亲(焦武、陈傲)更可怜,但无论是力不从心的守护还是无法面对现实的抗拒,都含纳着一种显见的辜负,即父对子的亏欠。于此,作者再次转让出了不容置疑的对与错、善与恶二元对立审判机制的失落效地带,在诸多的侵害和失落望中写出一种人物试图和解与理解的努力。除此,两个作品写出了真正具有“朋克精神”的人,焦海莲与吉米,他们承托并转化了父亲的辜负,授予他们和自身坚韧且悲壮的人格和情绪意义,悲哀但不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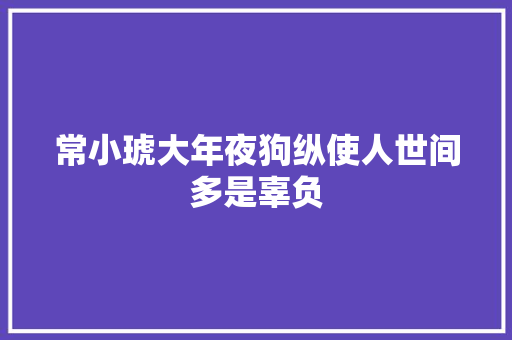
小说集里还有另一种辜负,和另一类被辜负的人,用作者的话说便是那些“无所适从的人,或者说是列车转弯时甩出车窗的人”,即那些堂·吉诃德式的执着又不合时宜的失落落的人,而辜负他们的是时期,和新旧交替的夹缝里无法安顿的命运。《变脸》《岁寒三友》,对肃静的持守、对技艺的执着和忠实以及岁月里漫长的哑忍是人物存在于作品的姿态,而漂浮在如今看来已然定型的历史不愿定中,他们对付再次获取合法的生存空间的试探与渴望和不断被摧毁被践踏的委曲,让作品充满了悲剧意味。千帆过尽,比较于时期,个体的生存状态更值得被书写,它是文学功能的一种应然,亦是作家承担的某种道义。经由与书写工具产生生命链接的办法,呈现另一种真实和历史景不雅观,“连同自己的故事一起被留在那里”。这也是为什么常小琥总是在写“从前”,为什么总是那么念旧。
和小说中许多不合时宜的人物一样,常小琥的写作本身也有那么点“不合时宜”。他乐意处理那些充分当代化了的作家已经不太相信的,或在当代生活确已逐步退场的各类道德化主题。在写作态度上,他彷佛排斥一种恃强凌弱的当代性和工具理性的坐观成败,无法全然地将书写工具工具化,将书写仅仅交给书写。因此,他的作品永久指涉超越自然征象和动物本能的情绪代价,即“道义”。这种将“先天缺失落的不断空想化、合理化”有些许浪漫化嫌疑,但是当我们看过了太多技艺博识的当代主义作品,不得不说,生活的诚挚和讲述的谎话变得越来越难分难辨,对付本属于人类群体的古老情绪越来越不被理解。或许,古典的情怀只能用古典的办法去呈现,在这一意义上,常小琥的笔墨内容和表现形式如榫卯般严丝合缝。
电影《密阳》剧照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各类辜负和深深的遗憾无力改变,那么记录算不算是一种填补和安慰,就犹如电影《密阳》里的母亲,在侵害即成事实的情形下等的不过是声道歉。如此说来,《大狗》的作者给予了人物一份主体性,给与了读者一份悲悯。读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否感慨一句:纵使人间间多是辜负。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摄图网
id : iwenxuebao
微信公号
新浪微博
@文艺速效丸
小红书
@41楼编辑部
小宇宙播客
2024文学报开启订阅
邮发代号3-22
周刊 / 整年定价:6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