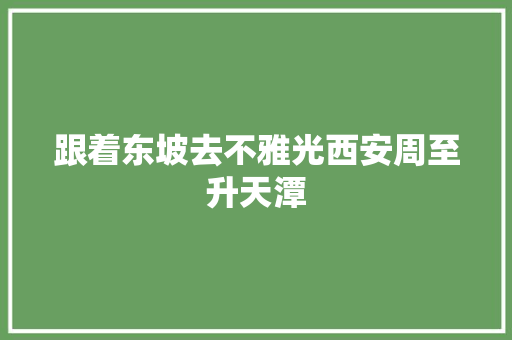“白塔”并不白,实为黄褐色,是一座形状类似西安小雁塔的砖筑密檐式佛塔,塔分七层(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宝塔”之意),再加上新建的基座,三、四十米高,流畅大方,巍然矗立。据传这是我国仅存的隋代方砖塔,镇守秦岭近1500年,历经王朝兴衰、山河巨变,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正由于宝贵,两年后建筑黑河水利工程,才得以整体迁移保存,连续见证人间风雨,世事沧桑。
法王塔旁建有仙游寺大殿, 仙游寺始建于公元598年,原名“仙游宫”,系隋文帝行宫,留有历代许多文人墨客的轶闻遗迹,特殊是唐代“诗史”白居易在这里写下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长恨歌》,苏东坡则至少二次漫游仙游潭区域。
(从延生不雅观)下山而西行十数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游潭。潭上有寺三,倚峻峰,面清溪,树林深翠,怪石不可胜数。潭水以绳缒石数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砾投之,翔扬徐下,食顷乃不见,其清澈如此。遂宿于复兴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飞泉甚甘,嫡以泉二瓶归至郿,又嫡乃至府。
留题仙游潭复兴寺,寺东有玉女洞,洞南有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
上述两段话是东坡于公元1062年仲春首次来嬉戏时的自注,在其长诗《壬寅仲春,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中,看到仙游潭、仙游寺、玉女泉等胜景山水风光,情不自禁回顾起当年与弟弟苏辙同游长江虾蟆碚的情景:
入谷警蒙密,登坡费挽搂。乱峰搀似槊,一水淡如油。
中使何年到,金龙自古投。千重横翠石,百丈见游鯈。
最爱泉鸣涧,初尝雪入喉。满瓶虽可致,洗耳叹无由。
忽忆寻蟆培,方冬脱鹿裘。山川良甚似,水石亦堪俦。
惟有泉傍饮,无人自献酬。
当晚,东坡宿于黑水北岸的复兴寺(北寺),题诗:
清潭百尺皎无泥,山木阴阴谷鸟啼。蜀客曾游明月峡,秦人今在武陵溪。
独攀书室窥岩窦,还访仙姝款石室。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东坡认为仙游潭之清,黑水峪之静,像蜀中明月峡一样亲切,又好比桃花源人间瑶池,还有马融读书石室的古迹和萧史弄玉结伴飞升玉女洞的俏丽传说,引人入胜,可惜因黑水阻隔,南岸的美景只有独木桥相连太危险,心有余而力不敷不可到达,徒留遗憾。
两年后(公元1064年)正月,东坡陪朋侪章惇重游仙游寺,著有《自清平镇游楼不雅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来回四日,得十一诗,寄子由同作》,诗作大半与仙游潭干系,并在自注中再次提到仙游潭的险要:
潭上有二寺。一在潭北,循黑水而上,为东路,至南寺。渡黑水西里余,从马北上,为西路,至北寺。东路险,不可骑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测,上以一木为桥,不敢过。故南寺有塔,望之可爱而终不能到。
仙游潭分南北两寺,“光摇岩上寺,深到影中天”,佛寺与天光倒映潭底,波光粼粼又反射寺壁,光影摇荡,如梦似幻。南寺阵势险要,风景奇丽,“东去愁攀石,西来怯渡桥。碧潭如见试,白塔苦相招”,北寺人迹罕至,历史久远,“唐初传有此,乱后不留碑。畏虎关门早,无村落得米迟”。两寺之间隔有溪涧,仅独木桥相连。
东坡嬉戏中多次提到的这根独木桥,今人因建水库已无法想象其险要,竟然令年轻的东坡望而生畏裹足不前,但同游的章惇却毫无惧色如履平地。据东坡《书游仙游潭》碑记一文:
嘉祐九年正月十三日,轼与前商洛令章惇子厚同游仙游潭。始轼再至潭上,畏其险,不渡,而心甚恨之。”
《宋史•章惇传》记载:
……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游。”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异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
可见东坡章惇两人年轻时交好,亦见章惇之生性大胆凶恶,可惜二大奇才终极因政见不合,分道扬镳。
对现已淹没水底的马融石室和玉女洞,东坡也曾留诗纪念,听说东坡当年给仙游寺还写过一幅楹联:客远尘凡丛中,到此俗缘尽了;堂开白云窝里,从兹觉岸齐登 。
东坡这些流传千年的诗句,和马融、白居易、岑参等名人诗文,对周至这片山水来说便是最好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