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别业》
[唐]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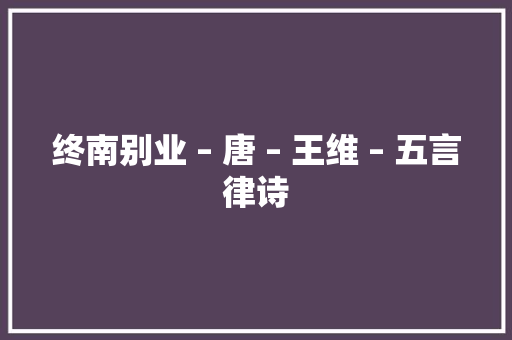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有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译文
中年往后存有较浓的好道之心,直到晚年才安家于终南山边陲。
兴趣浓时常常独来独往去嬉戏,有快乐的事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间或走到水的尽头去寻求源流,间或坐看上升的云雾千变万化。
有时在林间遇见个把村落庄父老,偶与他谈笑谈天每每忘了还家。
拼音
注释
中岁:中年。好(hào):喜好。道:这里指佛教。家:安家。南山:即终南山。陲(chuí):边缘,阁下,边疆。南山陲:指辋川别墅所在地,意思是终南山脚下。胜事:美好的事。值:碰着。叟(sǒu):老翁。无还期:没有回还的准确韶光。题记
此诗大约写于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之后,是王维晚年期间的作品。王维晚年官至尚书右丞,由于政局变革反复,他早已看到仕途的艰险,便想超脱这个烦扰的尘世。他吃斋奉佛,清闲清闲,大约四十岁后,就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
赏析
王维这首《终南别业》历来吟诵甚多,王维人称诗佛,这首是公认的禅诗,而诗中又处处表现禅理,历来解析这首诗歌的每每谈王维的淡泊宁静怡然自乐的情调,而实际不达至理。刘辰翁评,“无言之境,不可说之味,不知者以为淡易”,可谓深契王维之意。
王维自称摩诘,维摩诘居士是印度大乘佛学的代表人物,东方金粟如来转世,而这首诗中作者意欲表达的正是这种领悟大乘境界时的怡然自乐。
首联两句写自己信奉佛道由来已久,晚年时隐居蓝田辋川修佛学道。这两句也正是对诗歌背景的描述。
颔联两句写自己学道兴趣味浓,每每独来独往,而这种领悟禅宗至理的心境只可自己知道,不可与人言说。释迦牟尼说自己说法49年未尝说过一字,六祖慧能说禅宗至理非可言说,为传佛法,吾今强说。可知佛家所讲的自性非空非有,非善非恶,非实非虚,非烦恼非菩提,王维领悟这种境界岂是自己悭吝不肯与人言说,实在无法可说。所往后来人称东方维摩的庞蕴居士问女儿,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作解。灵照也只是回答说,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至理脱与名相措辞观点,佛每每斥说,凡人偏有,小乘偏空正是如此。
颈联两句可小解,也可大解,可知佛性不分大小,只是运用不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指水源之处,这地方再往上就没有水了,讲作者领悟禅宗向上至理的情境,清净寂然,不着不染,任从世事纷繁,英雄西烟而不著不动。正像有人问赵州从諗禅师,两龙戏珠,哪一只会赢,赵州答说,老僧只管看。其理一趣。
尾联则说作者不求高不求低,随遇而安,并能处处作乐的心态。佛家至理领悟的人不少,但转过来随处利用而不有碍的不多,所谓"荆棘丛中下脚易,月明帘下转身难"。以是佛家有"保"和"任"之分。王维在诗中表达的正是这种“任”的心态。
赏析二
全诗的着眼点在于作者抒发对得意其乐的闲适情趣的神往。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中岁”即中年。“道”这里指佛理。“晚”是晚年。“家”即安家。“陲”即边缘,阁下。“南山”即终南山。“南山陲”指辋川别墅所在地。据干系资料记载,辋川别墅原为宋之问的别墅,王维得到这个地方后,完备被这里奇丽、寂静的田园山水所陶醉。这两句是的意思是说,(自己)中年往后厌尘俗鼓噪,信奉佛教,晚年定居安家在南山边陲。诗歌开始就阐述了自己中年往后即厌尘俗而信奉佛教的思想。“终南山”在古代诗歌中,每每表现隐逸的地方。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即为终南山,暗示了陶渊明过着隐逸安适的生活。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胜事”即美好的事。“空”即白白地,或自然而然地。“自知”便是自己得到,自己得到,或者自己感想熏染到。这一联的意思是说,兴致来了,就独自一人自由清闲地前往欣赏终南山俏丽的景致,在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中得到了无尽的乐趣。这一联承上而来,墨客在此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闲情逸致了。上一句中的“独”字很有分量,不但写出墨客勃勃兴致时不受任何干扰,自由清闲的生活,而且也表现出了墨客的一种清闲的生理状态。下一句的“自知”又写出墨客在欣赏美景时所得到的自由清闲,得意其乐的情趣。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即言“胜事”。在山间信步闲走,不知不觉中,已到了溪水尽头,彷佛再无路可走,但墨客却感到面前一片开阔,于是,索性坐下,看天上的风起云涌。统统是那样的自然,山间流水、白云,无不引发作者无尽的兴致,足见其清闲清闲。清人沈德潜赞曰:“行所无事,一片化机。”“行到水穷处”,让读者体味到了“应尽便须尽”的开阔;“坐看云起时”,在体味最清闲、最清闲境界的同时,又能领略到妙境无穷的活泼!
云,有形无迹,飘忽不定,变革无穷,绵绵不绝,因而给人以无心、清闲和闲散的印象,陶潜有诗云“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而在佛家眼里,云又象征着“无常心”“无住心”。
因此,“坐看云起时”,还蕴藏着一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机。简而言之,便是“空”,如果人能够去掉执着,像云般无心,就可以摆脱烦恼,得到解脱,得到清闲,墨客在一坐、一看之际已经顿悟。再看这流水、白云,已是无所分别,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从构造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句,对偶工稳,一向而下,从艺术手腕上看,此二句俨然是一幅山水画,是“诗中有画”也。
“有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突出了“有时”二字。实在不止遇见这林叟是出于有时,本来出游便是乘兴而去,带有有时性;“行到水穷处”自然又是有时。“有时”二字实在是贯穿高下,成为这次出游的一个特色。而且正因处处有时,以是处处都是“无心的遇合”,更显出心中的清闲,如行云自由遨翔,如流水自由流淌,形迹毫无拘束。它写出了墨客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对付我们理解王维的思想是有认识意义的。
这首诗没有描述详细的山川景物,而重在表现墨客隐居山间时清闲得意的心境。诗的前六句自然闲静,墨客的形象如同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不问世事,视山间为乐土。不刻意探幽寻胜,而能随时随处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好。结尾两句,引入人的活动,带来生活气息,墨客的形象也更为可亲。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紧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人物性情光鲜。这首诗把退隐后得意其乐的闲适情趣,写得有条有理,惟妙惟肖。兴致来了就独自傲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清闲得意由此可见。
其次,看重细节描写。诗歌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大背景中,墨客又描写了与“叟”偶遇而笑谈的细节。个中这个“谈笑”,不但表现课墨客自由惬意之态,也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审美想空间。
再次,看重时空交错。在诗歌中,特殊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联,上句中的“处”字,下句中的“时”字,不但将行到水源的韶光过程给空间化,而且也把人看云起时的空间关系给韶光化,从而使诗歌的境界更加开阔高远。
末了,措辞简洁平实。这首诗歌的措辞简洁平实,平白如话,却意蕴深刻。同时,在这平实简洁的措辞中,不但富有情趣,而且更有理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