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天社倒勾着头,拨拉着一块小石子,圪蹴在记工室的高台阶上,瞪瓷眼,看蚂蚁排队。
巷道里空静无声,阳光残酷,晓风清凉,槐格九从槐枝叶杈里垂下来,拉丝吊线。九九家的大红公鸡气宇轩昂地打惠天社的面前走过,拦住他家的芦花小母鸡大献殷勤,忽而骄傲地一声长鸣,张起绚丽的翅膀,把芦花小母鸡揽在身子底下……
“砰!”惠天社手中的小石子带着愤怒,准确地打在大红公鸡的背上,大红公鸡怪叫一声,连飞带跳地跑走了;而芦花小母鸡呢,惊骇不安地望着惠天社,不明白这两厢宁愿的事与他何干?
嗨!甭说芦花小母鸡,便是惠天社他爹也猜不着惠天社的苦处呢!小伙子今年刚满十八,却长了个戳天的个子,浓眉大眼的,而且是屯子社里的老资格的社员了呢,送公粮,瞎眼窝喜成队长却不派他这个漂俊秀亮,穿着红背心的俊小伙去,硬让歪歪颡三旺顶了他的空儿,跟在玉巧儿尻子背面,挟着粮食口袋装公粮去了!“我啥不如他?”惠天社满腹冤屈地怨恨着:“啥好好事都轮不上咱,真是个瞎眼窝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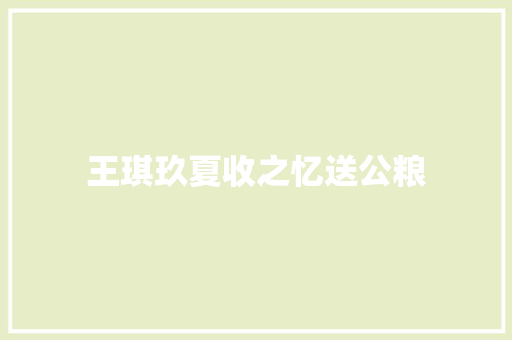
送公粮,能是怎么个好事么,值得我们的俊小伙这么伤心?
哈,这你就不明白了!
自从小满过后到如今,村落里的小伙子姑娘们割麦呀,碾场呀,丢了镰把拉车把,丢了扫帚拿杈把,黑地白日都在场里熬着哩,啥地方都去不了,啥衣服穿着都没样样,谁都愿望能到十五里路外的流曲粮站去送公粮!送公粮跟走亲戚一样,看风景,谈笑话,虽说也不轻省,但又挣工分又能逛,而且,还有打扮得花不楞登的姑娘娃厮随着,你看洋不洋?难怪惠天社生闷气哩,跟村落里的小伙子们比,娃又不差啥么!
但是,不管惠天社怎么不高兴,麦场上送公粮的姑娘小伙已经开始把一袋一袋的粮食口袋往架子车上装啦!装粮车,仿佛只是小伙子们的事,姑娘们戴着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红字的草帽,穿着粉的,绿的,或是月白的燕子领短袖和塑料凉鞋,站在场边的柳荫里,看着小伙子们装车,嘻嘻哈哈的,像一群喜鹊。小伙子们呢,彷佛玩儿似的,两个人一组,捉住麦口袋两头,嗨哟一声,百十斤重的口袋就忽地飞上了架子车顶。还有更精彩的呢!看,五大三粗的捉住,两手搭在大腿上,扎着马步,用牙咬住横在地上的麦口袋角,逐步地把麦口袋拽起来,又猛地一松口,脖子向前一伸,顺势接住斜倒下来的麦口袋,腰陡地一弓,腿猛地一贯,忽地一下,就把百十斤重的麦口袋扛起来了!脸不红,气不喘,腿不颤,小伙子得意地往姑娘群里瞅,期望赢得个满堂彩。不想姑娘们全都没瞥见……嗬,光堂堂的大路上,民选戴着墨镜,骑着新格铮铮的飞鸽车子,驮着竹笼红包袱和白胖白胖的麦喷鼻香,给丈母娘“转忙罢”去呀!麦喷鼻香穿着荷绿色的花边领短袖。脸儿笑得像朵盛开的红莲。
“噢--麦喷鼻香!大馍油角角掉了!”
“民选哟,车子带放炮啦!”
民选和麦喷鼻香伪装没听见,追风逐电般一闪而过,留下一串脆亮的响铃。
姑娘们嘻嘻哈哈,小伙子们痛惜若失落,狗日的民选,挑了这么俊秀个媳妇!张狂呢!看不摔个狗吃屎!——还没咒怨完呢!喜成队长吊着黑风脸一起骂过来啦:“日晃了一早上,还不起身!等人家粮站关门呀?”
小伙子们这才日吃紧忙赶紧钻进车辕里,姑娘们哄然四散,各寻各的伴当,拽起绳带,走!嘿,这下可好看咧,瞧!一男一女一辆车,一溜排十几辆装得满满的公粮车队,辗着浓浓的树荫,拽着清凉的晓风,咯吱咯吱地出了村落,向西,向南,再向西,起伏在半人高的绿翠如茵的早玉米田间,顺着开满牵牛花的水渠沿向流曲粮站方向蜿蜒而去……不知是谁,竟有那么高的兴致,捏腔拿调地唱起了眉户《梁秋燕》里的段子:
阳春儿天,秋燕去呀么去田间;
慰劳军属把呀么把菜剜,安安安嗯安。
样样事我要走在前边……
唉,小伙子哟,高兴啥哩嘛,离流曲粮站还有十几里路哩!不过,这对牛娃子一样平常健壮的小伙子们来说,根本就算不了啥,更何况身边还有个花枝飘荡的姑娘娃呢!女儿家嘛,天生便是穿花花衣裳,捏针拿线的,这着力量的话,原来便是男人家的事嘛!谁肯舍不得力气,落个去世老汉病娃的名声呢?看,小伙儿案板的脊梁弯得像张弓,双手用劲,两脚生风,车轮如飞;姑娘们呢,被车催着跑,省劲,省力,可省不了脚步;笑着,乐着,却不住的埋怨:“慢些,早哩!前面又没有谁等你哩!”
前边是没有人等,可前边,就在盖村落那儿,有卖喷鼻香瓜的哩!刚开园的白兔娃喷鼻香瓜,嫩、脆、沙、甜!还有刚出锅的泡油糕哩!焦油甜软的壳儿,满满一泡糖水儿,咬一口,满嘴油甜,爽!没有钱?——拿麦换!敢么?——怎的不敢?每辆粮车上都装有耗消多头哩,三斤二斤的,一准少不了大数,更何况这是村落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有例案呢!年年送公粮,都是这样嘛,又不是每天吃,要不然谁还争着送公粮呢?要不然惠天社就不会怨气得连鸡踏蛋都看着不顺眼!
好!——换!——吃!先吃泡油糕,再吃甜喷鼻香瓜,谁说生冷油腻不敢一块吃?看,小伙姑娘吃得多喷鼻香,多滋润津润!再看黑娃,吃完了油糕,还舔油指头哩,——贫气,不怕人笑话!怕啥呢?黑娃才十六,离娶媳妇还远着哩!好了好了,吃完了就走,赶紧!趁凉!日头都快到头顶了。再迟慢就交不进去了!于是,你听:脚步蹭蹭,车轮隆隆,姑娘小伙又唱合百搭地上路了!
果真,紧赶慢赶,还是迟了许多,——排队交粮的架子车都排到粮站门外边的大渠沿上啦!怎么办呢?等嘛,还能有啥法?小伙姑娘们把粮车一辆一辆挨着排成队,然后坐在大渠沿上的桐荫里,歇凉!小伙子们干脆往喷鼻香茅草上一躺,头底下垫块半截砖,草帽往脸上一扣,歇开晌啦!不歇的呢?背靠大树,鞋往尻子底下一垫,大腿跷在二腿上,吸烟!你看惬意不惬意!姑娘们呢?或是拿草帽扇凉,或是纳着鞋垫儿,或是拿小镜儿照着耍,同时,还照看着不断地往前挪粮车。让小伙子们歇一会吧!过一阵,往粮库顶上扛粮袋子,靠这些愣娃哩!
这阵儿,天却像着了火似的,满地都是红得发白的火星儿,一波一波的热浪,白花花地浮漾着,风儿不吹,树叶儿都
可是,弥漫着燥热的尘土和汗腥味儿的粮站里,这阵儿却乱马踏营似的人喊马叫,搬粮食口袋的,过地磅的,上仓板的,争地盘的,跟过来跟过去撵验粮员的,在烈日下,在浮尘中,在汗雨里,喊着叫着。验粮员是仁张村落的麻子怪老惠,老惠戴着青竹细草帽,架着墨镜,穿着日本尿素袋子缝的短衫短裤,拿着验粮的铁梭杆,盛气凌人地往粮食口袋里戳下去,又满脸严明地拽出来,倒几颗在手心里,又吃花生仁似的往嘴里一扔,咯崩一咬,眉头目一皱,——坏啦!可把晒粮的事弄下啦!凑在他跟前的送粮人暗暗叫苦。果真,麻子怪老惠把黑脸一板:“晒去!”送粮的赶紧递上一根纸烟:“老惠,哎老惠,我是你娃他舅村落里的,哎,要不再验验,——不湿么!”麻子怪老惠像没听见似的,不应不笑,把烟往耳朵背后一夹,却依然还是那两个字:“晒去!”说罢,尻子一拧,又验另一家去啦!若是麻子怪老惠的眉头目一展呢?送粮的人们便长出一口气,兴趣勃勃地把粮食口袋往地磅上搬。啊,麻子怪老惠的眉高眼低如此这般田主要,怪不得送粮的给这个脸上有几点麻子的老汉起个老怪的外号呢!
再看那些从去世板地一点面子都不讲的麻子怪老惠部下过了关的送粮人吧!欢得就像脱了缰的马,只管灰土汗水和不断搬动粮食口袋的紧张劳动,把小伙子们弄得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但大家精神亢奋,感情飞腾。广播里不断播送着全县交公粮社队的名次和《龙江颂》里江水英的唱段,莫名的光荣感和紧张的劳动气氛使得小伙子们如久闻号角的战马,跃跃欲试。看!北耕村落的小伙多能!一律穿着圆领蓝条海军笠衫,头上连草帽也不戴,把一袋袋粮食抬起来,码在地磅上;待报数过后,又一袋袋卸下来,靠成一排。而专往高高的粮仓里扛的小伙子呢,大家肩脖上绑着白坎肩,腰一弯,手一板,腿一贯,就把一袋粮食扛起来了!而且,一溜小跑,蹭蹭蹭几下就窜上了高高的搭在粮仓上的斜板,肩一斜,手一举,哗的一声,满口袋金黄的麦颗就像归海的鱼儿,刷地灌进仓里去啦!满粮站的人,哪个不服气呢?——人家是全县有名的青年突击队么,甭说小伙子,便是人家村落里的姑娘娃,一个个都凶火获胜过穆桂英哩!北耕村落小伙的入粮演出,把刚进粮站的沐惠村落的姑娘们的眼都看直啦!
“骚情啥哩!”哈!还有人不服气呢?谁?噢~~沐惠村落的捉住么!捉住有这本钱,姑娘们都看着捉住,——捉住壮实得像座塔,豹眉环眼,脊背赛案板,手像蒲扇。不知为啥,捉住便是看着北耕村落的小伙们不顺眼,尤其是看着他们一个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张狂劲,还有那贼眉鼠眼地光朝姑娘窝里瞅的熊样儿,心里就来气。三两步走过去,拍拍北耕村落小伙的肩膀,一声不吭,把两袋百十斤重的粮食口袋紧口向下并排儿倒竖着,扎起马步,又稳稳地蹲下身,两手轻轻一板,两只粮食口袋顺顺地倒斜在两只肩膀上。捉住拧拧头,两手抓紧粮食口袋,美美地憋一口气,腮帮子一鼓,忽儿“呀”地大叫一声,腰一挺,忽地一下站了起来!仅这一下,粮站上四村落八寨的送粮人都木鸡之呆了,——天爷!二百多斤重哩,这娃莫不是李天王下凡?嗨!绝活还在后边哩!你看捉住,走在高得怕人的窄窄的斜架板上,忽悠忽悠地,像扭秧歌呢,他竟然不怕!而且,还站在宽不过二尺的粮仓边上换脚哩,——胆大!张狂!仿佛是张狂够了,捉住这才在大伙担心、敬佩、倾慕、妒忌的目光里,松开抓在粮食口袋紧口上的手,让麦颗瀑布般地流进仓里。沐惠村落的小伙子们立马掌声大作,唿哨乱响;沐惠村落的姑娘们呢,虽然愉快激动得脸像一朵花,但却没有一个人乱抛媚眼,一是怕捉住看不见,二是本来就没那个心——捉住只管穷得只有一个老妈,但却是富农成份,跟了他,每天挨批斗,扫巷道呀?可是,姑娘的心,海里的针,谁又能猜得透,说得准呢!
只管捉住赢了个满堂彩,但沐惠村落的公粮还是交得最迟。唉,直到日头爷已经偏西了,这才好不容易排到跟前,粮食验过了,麻子怪老惠的眉头不皱也不展。嫌咋?——土大,过铁纱网去!唉,过就过吧,不过有啥法?那个去世人脸麻子怪老惠,是个吃钢咬铁的家伙,再纠缠也没用!嘿,等到把一袋袋麦颗重新用铁纱网筛过,装起,过磅,入库……逐一忙活完毕,沐惠村落的姑娘小伙子们前襟后襟的汗,都不知道湿过干过几次了,一个个乏得就像雨地里的地皮爷——软得走不动啦!幸亏刚才歇晌起来的时候,黑娃还用麦换了一篮子黄杏,美美地吃了一饱,要不,这会儿早就饿得爬下啦!
但是,姑娘小伙们眉宇间却漾溢着浓浓的喜悦,啊,公粮交了,心轻省了嘛!他们圪蹴在粮站门外的水渠沿上,洗脸擦汗,撩水嬉闹,像刚刚打了胜仗的游击队员,怠倦而又愉快地议论着交粮的插曲。一下子,歇息够了,洗刷净了,小伙姑娘们缓过神来,又神采飞扬地拉着架子车往回赶。回来的路是漫长的下坡,小伙子们把两辆架子车辕一前一后反向交叉,又用拽绳贯串衔接起来,一溜一串地在公路上开“火车”,呼呼呼往下窜,姑娘们坐在车厢里,吓得吱哇乱叫……
这会儿,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山尖,落晖在婆娑起舞的早玉米叶上闪闪跃动,灿亮如金。滑爽的晚风轻挽着公路两边粗直的箭杆杨,忽啦啦的树叶翻转如飞,而遥遥地,在炊烟袅袅,绿树掩映的村落落那边,《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在大广播里年夜方激越抒发着壮志豪情: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作者简介:王琪玖,作家,现当代文学教授,秦文化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