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芬
周恭寿
胡雪松
刘薰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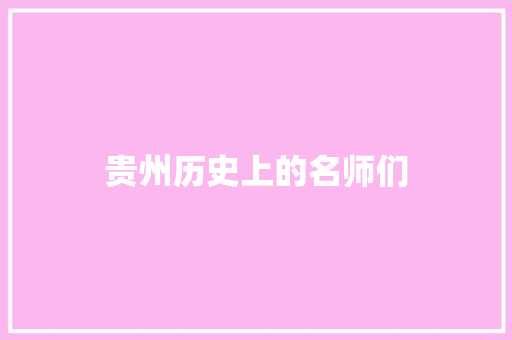
任可澄
濮振远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 惬意
在又一个西席节来临之际,翻开贵州教诲的干系史料,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上世纪初到六七十年代的贵州名师——这个韶光段的出发点是贵州大学、贵阳一中等学校创建期间的名师,终点是他们至今仍旧健在的学生对他们的回顾。
办学篇
1.旧时的贵阳一中
2.国立贵阳师院附中教室
3.国立贵州大学远眺
4.国立贵阳医学院。
大名鼎鼎的贵阳人李端棻,号称中国近代教诲之父。1889年,当他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时,少年梁启超以“熔经铸史”的文笔,被他慧眼识珠。李端棻不仅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首倡者,也是贵阳一中和贵阳市师范学校创始人。1905年,李端棻会同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呈请贵州巡抚林绍年批准,将原设正本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往次南门外丁公祠、昭忠祠、雪涯洞,改名贵阳中学堂——贵阳一中的历史,即以此为发轫。
1905年,任可澄受聘为贵州学务处参议,开始创办新学。除了贵阳一中,他在贵阳参与创办的学校还包括:1905年,和唐尔镛、徐天叙一起,开办师范讲习所,为贵阳近代小学供应了师资;1907年,与唐尔镛、华之鸿创办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1910年,又与华之鸿等创办宪群法政学堂,专门培养法政人才。
作为贵州近代教诲的开拓者,从李端棻到任可澄,都具有强烈的家国意识和远大抱负,以“教诲救国”为思想支撑,将兴办学堂、发展教诲作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政治空想的主要路子,并为新学入黔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周恭寿担当贵州第一任教诲厅厅长。这位1905年曾赴日本留学和稽核教诲两年的教诲家,返国后在贵阳创办官立高档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9所。关于他对贵州教诲的浩瀚贡献中,一件看似“非主流”的作为,却和当下教诲对体育的重视遥相呼应——1911年,担当官立高档和初等小学堂堂长的他,主持在贵阳南郊新军操场(今省军区内)举行千逻辑学生参加的运动会,不雅观众达4万人,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次运动会。
1929年创办贵阳县立中学的王佩芬,曾经在贵阳多所学校任教或担当校长。他不仅用丰富学识使人受益,更用他的人格魅力折服了所有师生。新中国成立后,他连续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执教20多年,听说总是穿着朴素,时常一袭蓝布长衫。性情爽朗,讲课生动诙谐,夷易可亲,深为学生敬仰。由于他的渊博学识,他的学生们给他起了两个外号:“多宝道人”和“活字典”。
王佩芬治学严谨而有研讨精神。在他的书房中,总是贴满一些小纸条,他把要记的东西写上,随时朗读背诵。50多岁时,他开始学习古典诗词创作,后来果真写成一些受人称道的好作品。60多岁时,他开始学习俄文,终于能做到阅读俄文书本以及做大略的笔译。70多岁时,他又开始进行笔墨改革研究,垂暮之年还写出《贵州省若何试行汉语音文的研究》一书。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比较以上几位办学者,更多贵阳人有可能更熟习王伯群这个名字。建筑于一个世纪前的王伯群故居,作为贵阳历史上第一栋仿西式建筑,至今仍伫立在贵阳市中央,是城市一处别样景不雅观。抗日战役爆发后,这位贵州兴义籍著名教诲家所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内迁贵州,1938年初,王伯群辗转越南海防、昆明,元宵节晚抵达贵阳。在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探求西南联大》一书中,这样记录当时的场景:“阔别二十余年,故旧来访相继而来。某天,王伯群对夫人保志宁感慨:‘二十余年未归的贵阳,城郭依旧,公民……多不认识了。与我同年迈友,较我狼狈、衰朽者,多不复为国家社会努力,像我还时时想进步,年夜志未已,想必是多与年青的人靠近,似较胜一筹,但我精力大减,不能耐苦,亦是遗憾。看外国人六七十岁,尚精神弥满,奇迹壮盛,我自己又以为很惭愧,以是往后要特殊把稳身体之教化,精神之健旺为至要’。”——多与年青的人靠近,保持身心年轻态,大概是很多为人师者的共同体会。王伯群创办了大夏大学贵阳附中,任校长期间,文娱活动十分生动,组建的军乐队多次在全市演出,开了音乐演奏会之先河,颇有名气。然而提醒自己要养生的他,在1944年日军反攻袭击独山后,为大夏大学的去向问题殚精竭虑奔波劳苦,于当年12月12日病逝时,也不过59岁。1947年,大夏中学更名为伯群中学。
1950年初,省立贵阳高等中学和贵阳中学、中山中学、贵阳师院附中、伯群中学合并而成贵阳一中。胡雪松是省立贵阳中学并入贵阳一中前的末了一任校长。在贵阳一中百年校史一书中,可以瞥见当年的学生这样描述这位“高冷范儿”的校长:“高高的身躯,一副威严的样子。老花镜后是一双大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唇上有短桩八字胡。他的脸上很少浮现笑颜,便是笑,也只是嘴角今后一拉,显出一点白牙而已。”
胡雪松校长管理学校的严格是出了名的。每天凌晨,有个场景都会在校园里反复上演:胡校长站在校长室门口,看着来上学的学生鱼贯而入。如果有学生迟到,必定受到训话。他哀求学生着装整洁,男生不准留发。自己更因此身作则,每天到得很早,穿着整洁的黄卡叽中山装,领扣扣得很好。
对学生的学习管理,胡雪松校长也自有一套办法。学生的作文一定要羊毫楷书,并当场完成,各科平常的小考小测也较多。考试时有严格的考试规章,每次半期和期末考试,都要稠浊编班,试题密封,由西席轮流监考。对作弊的学生除该科考试作零分外,还要记大过一次。同时将精良试卷贴堂,公布总评分数。这样的赏罚制度和榜样浸染的发挥,对学生起了很大的勉励浸染。
看似严厉的胡雪松,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却是发自内心、落到实处的。贵阳中学初三十六期高二十三期学生旷国坚心里珍存着这样一段回顾:“1944年放学期,由于家庭已临绝境,我辍学了。经同学先容,到清镇小学教书。我想,从此不要说读书,便是生活还得自己去找。我还生着病,发着烧。正在这灾患丛生之时,我收到初中同学傅正贤的来信,并附有胡校长的便条:‘国坚,火速返校,用费我为汝卖力。校长雪松。’我心中的感激难以形容。
黔南事变后,学校虽然困难重重,但胡校长还是让我免费读书。我毕业了,不知若何去找事情,正在难堪之时,校长问我:‘你要考大学不考?’我说:‘考什么大学,连饭都吃不起。’他说:‘那么你在学校事情,来日诰日考生来报名,你收报名费。’我高兴极了,想不到还在贵阳我的家乡找到事情,真是雪中送炭啊。我在贵中事情了一年,终于存上了一万元法币,1946年考上师院。能大学毕业,怎能忘却胡校长呢?”
抗战期间,贵阳中学迁到乌当,瞥见学生们家境大多都不太好,胡雪松曾打算由学校来办理吃的问题。有一次他说:“我们把对门坡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往后同学们上学,只带铺盖卷就够了,不要交炊事费了。”但由于日本人打到独山,学校疏散,往后又迁回城里,他的欲望也就未能实现。
抗日战役初期,正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的刘薰宇,接到了时任贵州省教诲厅厅长张志韩的一封信,信中说:“贵州教诲待整顿,需人孔亟,盼回来为故里尽力。”思乡之情以及强烈的社会任务感,让刘薰宇毅然辞去教授职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贵阳,担当贵州省立贵阳高等中学校长。
1950年初,包括省立贵阳高等中学在内的几所中学合并成贵阳一中,刘薰宇担当第一任校长。他是“五四”运动前考入北平高档师范学校数理系的,并与十几个同学组织成立了“工学会”。“五四”运动中,“工学会”主动承担了学校学生会的印刷传单的任务。“火烧赵家楼”时,冲锋在前的学生中间,就熟年轻的刘薰宇。
20世纪30年代,远赴巴黎攻读数学的刘薰宇返国,在教材培植方面硕果累累。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数学》《开明英语》(与林语堂互助)等,是当时风行全国的中学教材;另有《解析几何》一书,是当时我国高中学生主要的辅导读物;与夏丐尊合著的《文章作法》,也是当时广为盛行的中学生课外赞助书。他还是我国“意见意义数学”的创始者,所著《马师长西席谈数学》《数学意见意义》《数学园地》等书,在海内享有盛名。
——校长的气质每每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学校的气质。大半个世纪前的贵阳一中在重视科学和提倡民主上的光鲜特色,与校长刘薰宇的治学为人风格一脉相承。
刘薰宇回到家乡时正是抗日战役初期。在这一期间,全国各地沦陷区,大批文化教诲机构迁到贵阳,很多著名文化人也蜂拥而来。不久,贵阳地区遭到日本飞机频繁滋扰和空袭,省立高中迁至修文县,当时的高中校舍便是一座年久失落修的破庙。修文的冬天比贵阳寒冷,加上教室和宿舍四面透风,寒冬就更加难捱。刘薰宇深恐学生们受冻,于是许可大家带烘笼进教室。在上课和自习时,学生们每人桌下都放有一个烘笼,教室里充满了春天般的温暖。
当时的贵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学校教诲在朝不保夕的生存困境之下,更是风雨飘摇。一些学校终结了,一些学校则濒于崩溃边缘,然而刘薰宇领导的省立高中却在浊世中创造了欣欣向荣的奇迹。学校在物质上同样相称匮乏,校舍简陋,经费奇缺,师生生活窘迫,但却拥有丰足的精神财富——在刘薰宇的力邀之下,一批贵州教诲界、文化界的有名人士汇聚学校任教。刘方岳、李俶元、赵伯愚、蹇先艾、杨文山……他们在极其艰巨的条件下,任劳任怨,潜心传授教化,用深厚的素养和高尚的人格,为省立高中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战乱之中文化教诲的“桃花源”。名师搜集强化了名校效应,一韶光,省立高中名声大振,贵州各地慕名而来的求学者相继而来。刘薰宇这位在全国教诲界拥有广泛影响的校长,用他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让当时的学校虽偏居古龙场驿的龙岗山,却仍旧大放异彩。
抗日战役胜利后,省立高中由修文迁回贵阳复课。刘薰宇许可学生“办私菜”,也在当时传为嘉话。那时的学校集体炊事办得差,刘薰宇除了常常加强对伙食职员的教诲外,还许可学生们不吃集体炊事而去办私菜,加强营养。当时的省高门口,有开馆子的,摆水豆腐、酸菜豆汤摊的,热闹得很。时至今日,每一所学校外都有某个区域店铺林立,餐馆连延,这险些已成校园“标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贵州教诲的发展,尤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贵州各个学府的光辉影象,正是被这一位又一位“新学入黔”的先驱和才略与实干兼备的校长所开篇。而早期办学者们的美好品质也在后来者身上代代相传——之后当了贵阳一中30年校长的韩述明,和当年的胡雪松校长一样,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校的人。他刚上任的那些年,位于遵义路的朝阳桥和位于两江口的一中桥都还没有建筑,学生进出学校仍旧须要乘坐两江口的渡船。每天清晨,当学生们乘船向学校逐步靠近,他们便会迎来熟习的一幕——年轻的韩校长站在操场上,等待他们的渡船逐渐靠岸,迎候陆续下船进校的师生。淡淡晨曦里,这是每天这座校园带给他们的温暖的第一课。
(本版宣布感谢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学术支持!
)
本版图片均由濮振远供应
传授教化篇严寅亮
尹笃生
谢孝思
凌秋鹗
李俶元
田君亮
这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三月的一天。在南明河两江口的北岸,那条叫雪崖洞的小巷里,一座灰砖青瓦的宅院内传出了朗朗读书声,让过往的人感到了些许迎面的生气——贵阳中学堂(次年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在这里开课了。
这是一座在贵州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学”,从它开设的课程便可知晓:国文、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美术图画、体操、法制理财、读经讲经、修身品行等10多门。
从这天开始,51名来自贵州各地的年轻的学子在这里恭候着一位位青衣长衫的师长西席。这些“传道授业解惑”者,年事从二十八九岁到三十八九岁,正可谓年富力强,他们中有任可澄、李裕增、孙世杰、姚景崇、景方祯、黄禄贞、孟光炯等等,个中还有一位“外教”——来自日本高崎的33岁外语西席落合兼光,他在来中国前就从事师范教诲。
这些学子是幸运的,由于他们面前的这些师长西席,不仅“术业有专攻”,且不少人在贵州近代教诲史上,还曾是掷地有声的人物——
李裕增,与于德楷、乐嘉藻是我省师范教诲的最早倡导者,贵州公立师范学堂的创始人。
孙世杰,留日归来,有“贵州历史上第一批‘学兼中西’的人才”之誉,讲授修身、算学、音乐,时年29岁。
景方桢,国画西席。是我省“新学”最早的美术西席。他善于画花鸟,尤爱画牡丹,风格清雅。在本日的贵阳一中校史陈设室里,有一幅题为《通省公立中学堂侧视图》的绘画作品,便是景师长西席1908年绘制的。这是一幅鸟瞰图,当年的校园风貌、建筑布局尽收眼底,它成了贵州这所最早的“新学”的极为宝贵的“立此存照”……
回看一个世纪前的贵州教诲史,人们对一长串精良西席的名字已经知晓不多,然而正是他们所造就的桃李,孕育了这片地皮的日渐芬芳。
贵州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的尹笃生,从日本东京高档师范学成归国后,长期从事师范教诲,1912年创办贵州省立师范学校,主持校务长达9年,使贵师成为贵州师资的摇篮。他卒于任上,身后冷落,家徒四壁,留下的幼小子女幸得学生及社会救援。其同事、书法大家严寅亮评价其“心迹光明清似水”。
严寅亮,清末民初贵州著名教诲家、全国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北京颐和园大门匾额上的“颐和园”三字,便是严氏所书。辛亥革命后回原籍贵州,在贵阳执教近20年,专授国文、习字。其治学严谨,为人师表,有时一日在数校上课,往来奔波,毫无怨言,更无名家架子。他对付索书者从不谢绝,且从不收取“润笔”。
萧协臣,年轻时师从维新名人李端棻,戊戌变法失落败后从事新学教诲。善于数理传授教化,为多所学校竞相聘任。其上几何课时,每逢在黑板上画圆,不用圆规而用脑后的辫子——以脑袋为圆心,以辫子为半径——一时成为当时校园趣话。
王和叔,一位勇于创新的教诲家。曾任省立模范小学校长,在学校开设“格致”课,即格物致知之义,内容为今生物、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深受学生欢迎。学校还设有标本陈设室,陈设有人体骨骼及动物、植物、矿物等标本,这也为当时其他小学所没有。他强调实践,上化学课重视实验,还组织学生生产肥皂、粉笔、颜料等,以勤工俭学的形式供应市场,产品的包装上写明“贵州省立模范小学制造”。当时学校绿树成荫,花木繁多。校园内的每一株花木都挂有写着其科属、产地、用场等的木牌,他让校园也成为对学生进行直不雅观传授教化的场所。
凌秋鹗,著名教诲家,口语文传授教化倡导者。他终生从事中学传授教化及教诲管理,数度出任达德学校校长。在他倡导下,学校采取口语文教材,学生用口语文写作,西席用口语文批改。他反对女子裹足,开办女校招收女生。
钱瑗,1908年从中国第一所新型高档学校——京师大学堂毕业。几十年从事史地传授教化,并主讲过论理学、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他讲课形象生动,普通易懂,如地理课上他讲“意大利像一只皮靴,踢着的球便是西西里岛”,这一有趣的比喻往后常常被人们提起。
谢孝思,省立贵阳高等中学美术教员。著名国画艺术家、美术教诲家、文物家。曾创办文艺讲习班和美术刺绣班,并帮忙贵阳师范学校成立艺术师范科,为家乡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也为苏州园林修复和文物保护作出过重大贡献……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学入黔,载入贵州教诲史的名字还有蹇先艾、李俶元、刘方岳、肖之亮等等,不胜列举。在此罗列的也只是一些史料记载中“有故事的人”。比如田君亮,贵州最早的教授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副省长、贵州大学校长、省教诲厅厅长、省文史馆馆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有个关于他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革命活动,保护进步学生的故事广为流传:一次,他在贵阳文通书局遇见时任省教诲厅厅长的陈公亮,即质问当局为什么要弹压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陈公亮却多方狡辩,诬学生之举是“图谋不轨”,田君亮大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学生)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是国家民族之大幸!
”说罢举起手中的长烟杆要揍陈公亮……这便是盛传一时的“二亮闹文通”。还有一次,贵阳青年学生宣扬抗日,一伙特务闯进贵阳中学大门要抓“共党”,溘然两根长长的叶子烟杆挡在了面前,举头一看,面前是两位长衫师长西席——大名鼎鼎的李俶元和田君亮,面对两位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特务们只好悻悻而退……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