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本身就有一定的理解难度
诗是韵文,是高真个、凝练的、有节奏感的情绪抒发笔墨。换言之,诗是有更高条件约束的文章,纵然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诗歌也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于被理解,乃至须要“翻译”(赏析)的文体。正由于表达的弯曲,意境的悠远,诗歌才能成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虽然遗世独立,却睥群雄。
很多人读不懂诗,但是却无法也不敢轻视诗歌——这是文化地位爱崇的表示,以是不论从古到今多少荒诞的事情涌如今诗坛,也不会影响到诗歌在人类心目中的地位。
作为文章,表达是第一目的。弯曲回环的修辞手腕是为了让读者在达到理解作者思考之时或恍然大悟,或如痴如醉。也便是说,诗歌是用精髓精辟的措辞将情绪衬托玩到极致,构思和意境极其主要。如果只看重修辞,而没有内容和意境,就会成为形而上的空洞文辞,历史上的齐梁体、晚唐体都是样本。
以是,诗歌的精确走向都是在修辞和内容之间达到高度的平衡。既要写得美,又不能让读者被绕晕——而后一点尤其主要。为什么我们喜好盛唐诗歌?由于他们那个时期既继续了宫体诗的美,又合了盛唐昂扬向上的意象,学习汉魏风尚,以内容为肱骨。同时,白居易为代表的墨客们认识到唯有传播出来才是好文学,写诗要让不识字的人都能听懂,盛唐、中唐在形式和内容,高境界和广流传之中的度是把握得极好的,才创造了诗歌史上的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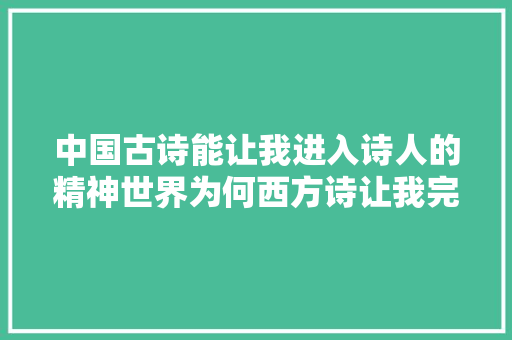
我们母语的诗歌,一定是让我们听懂,并走入墨客的精神天下的——这是诗歌、是文学最基本的功用。从实质而言,天下上所有的文章都是议论文,只是修辞手腕不同罢了。议论文便是摆论据,论证不雅观点,说服读者。小说是这样、散文是这样、诗歌也是这样,它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手段,说服读者,产生同理心。让读者产生通感,从而被打动,是所有笔墨的最初始的浸染,乃至我们日常措辞互换的目的也是如此——探求沟通,得到认同。
只不过手段不同,理解的难度不同,修辞的手腕不同而已。
有了本民族措辞文化从小打底的根本,再难的学术著作,再神秘弯曲的小说,再绮丽神秘的诗歌,只要我们负责学习,不断积累,去理解背后的知识,没有读不通的——由于构成这些作品的字我们从小就认识。
翻译霸占决定性成分
西方诗对付西方人也是一样的。
以是,问题在哪儿?在于人,在于人生活的团体,在于人生活团体所在的地域。总的提及来,在于文化差别。
西方诗是在西方措辞之上简练、提成、表达西方人想法的韵文(这一点是相同的),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西方诗,觉得没有节奏感、又没有押韵?
那是翻译太烂的缘故。
有朋友说泰戈尔的小诗就不押韵,没节奏,可是地位崇高。
《飞鸟集》里的诗,实际上都是泰戈尔平时随性而写的几句话,犹如你在朋友圈写那么几句一样。只不过泰戈尔用墨客的眼力和敏感,来不雅观察和欣赏自然,写出幽美的句子,常常透出哲思。 这些“小诗”,有点像西方人写的“断章”,并不符合西方诗的格律,而靠内容本身的幽美和哲思取胜。
也便是说,从严格的,刻板的,守旧的不雅观点来看,《飞鸟集》就不是诗。
但是泰戈尔的作品,充满意见意义,引人寻思。这种寻思,是在强制读者去思考,而读者沉浸在他幽美的笔墨中,毫无察觉。他虽然形式上冲破了诗的局限,但是在催人思虑的哲思之路上,他走得比传统墨客更远。郑振铎选译了《飞鸟集》,中国人立时被这种小巧、俏丽、妙思的形式所吸引,泰戈尔热延续至今。冰心的《繁星集》便是模拟《飞鸟集》的形式。
中国的当代诗也正来源如此。只不过后来者相对缺少这种哲学灵性。同时在风云激荡的时期,当代诗又接过古典诗歌讽喻、批驳社会的功能,加上热血青年的激情,变得更加光滑油滑、接地气,篇幅也越来越长,中国人浸刺骨子里的诗歌特色“平仄、节奏、押韵”开始逐步回归,掀起了当代诗的发展高潮。
翻译的好坏对我们理解诗歌的帮助,我们就看《飞鸟集》的翻译就知道,郑振铎的翻译带领了中国当代诗的发展方向,而当代“大家”冯唐翻出来,没几天就下架了,由于那切实其实便是一场灾害。
有生于无,反制于无
人是一样的人,精神殊途同归,终极也会走到一起。以是古诗、当代诗、西方诗对天下的多样性反射、对精神天下的多样性抱负,实在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一点从宗教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宗教是对文化异化得最明显、最恐怖的路子,但是我们去探究那些宗教所仰仗的思想创立者的学说,就会创造实在“天下大同”,他们都是在探求天下的本源,人类的死活。
而冲破这种殊途同归的同一性的,便是文化的多样性,好比如相同思想不雅观点衍生出不同的流派来一样,终极不同流派反目成仇,相互厮杀。释迦摩尼提出“苦集灭道”的时候可曾想过他的后学者不能吃肉,不能娶妻?这些都是人为不雅观点的异化,变相的阻碍了人类对终极不雅观点“同归于尽(本意)”的追求。
从老子的不雅观点来说,这是由于“道生一”,生出“德”来,反而阻隔了人类追寻“道”的脚步。措辞笔墨的地域性发展是一定天生的,反过来阻碍了人类精神天下的大同。
以是,我们对西方诗没有觉得,实在和西方人对我们的诗没有觉得是一样的。一个外国人,得有多深厚的中华文化知识才能读懂“庄生晓梦迷蝴蝶”?我们很多人都不能精确理解,乃至没有人能精确理解。那我们又何必奢望去理解西方诗歌背后的文化隐喻呢?
这不仅仅是翻译的“信、达、雅”的问题,而是沟通办法,措辞笔墨本身就有文化沉淀和模糊观点,无法精确的量化。
“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便是要使译文忠于原文,如实地、恰当地利用当代汉语把原文翻译出来。“达”是指内译文要畅通畅达,便是要使译文符合当代汉语的语法及用语习气,字通句顺,没有语病。“雅”便是指译文要幽美自然,便是要使译文生动、形象,完美地表达原文的写作风格。
这三点的根本都是当代汉语翻译。
“信、达、雅”于诗歌的分外难度
诗歌是笔墨之上的提炼,本身就对“达”互为抵牾。比如说我们的“诗家语”,倒装或者缺失落都是为了节奏感的存在,让我们的诗歌形式更“雅”。也便是说诗歌(文言文之上)这种形式和文章、小说翻译不同,你要“达”,就要捐躯一部分“雅”;你要“雅”,那你就得适应“诗家语”的分外表达办法。
而一旦不“雅”了,又谈什么诗歌美感?如何办理好这个问题,没有长期在东西方都生活过,并且对东西方笔墨、措辞、文化都有深刻研究的人是无法胜任这个事情的。
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的翻译者,又如何有能力将“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翻成和西方笔墨中具有韵感节奏感的诗?
这对如今的翻译事情者来说是过分的哀求。
并不是在西方就看不到这个景致,也并不是老外就没有这种感想熏染,而是表达办法会有所不同,如果能够打通这两者之间的表达办法,最大略的便是都翻成口语文,翻成大家都理解的当代笔墨。“常凯申”该当便是这种办法的结果,翻译者并没有想过去进行考据订正,当然他们可能也认为国外通用发音,不用顾及海内读者。
而翻译的目的,和措辞笔墨的目的是一样,是为了互换、沟通、说服。显然这种翻译除了让人以为可笑之外,达不到其他效果。
当然,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到的。
说到诗歌翻译,比来网上最盛行确当是电影《暮光之城》里面一句台词的文言文做派: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
sun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
我爱这世上三样东西,太阳,玉轮和你。清晨的太阳,夜晚的玉轮和永久的你。
如果就这么直译,便是挺齁的一句情话,更像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或者这么说,是不押韵的西方诗。
但是经由我们神奇的网友,带上文言文的外壳,瞬间气质就高大上了起来:
浮世三千,吾爱有三。
日、月与卿。
日为朝,月为暮。
卿为朝朝暮暮。
这是一首古风,而且觉得就出来了。和前面口语翻译比起来,就彷佛泰戈尔的小句子,有着冯唐和郑振铎的差距。
以是,当我们读到这种翻译得非常好,在措辞上完备契合汉字水平,而又没有丢失原意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感想熏染到西方诗的精神天下呢?
当然是可以的,天下本来相通,只是千疮百孔。
而好的翻译便是在这千疮百孔的天下里修路搭桥的人。
(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