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盎:原指腹大口小的盛物洗物的瓦盆,后来泛指盆这一类的容器。
【译文】
牡丹被称作花王,芍药被称为花相,皆是花中的贵族。栽种不雅观赏,不能有丝毫的寒酸之气。用带纹理的石材做栏杆,参差排列,按照次序栽种。花开时节设置宴会,用木料搭起架子,上面铺着碧色的帷幔,以遮蔽日光,夜晚则悬挂灯烛来照明。忌将牡丹和芍药并列同排,忌将这两种花放置在木桶和大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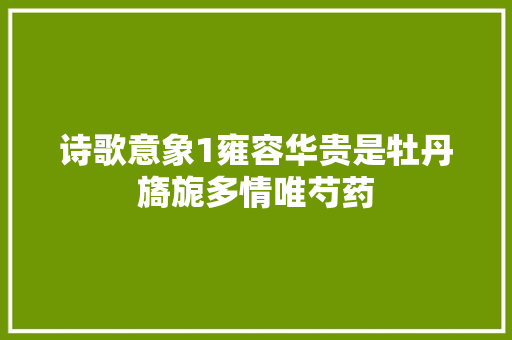
【杂论】
牡丹和芍药既是是我国特有的花卉更是名贵花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她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她们两者虽然都是名花。但实在牡丹为木本,芍药为草本。其余牡丹的花期略早于芍药。以是文震亨认为这两种花不应该并列栽种,大概也是有从这方面的考虑。
作为花中富贵者,栽种玩赏之道,也必须要有富贵的做派,绝不能寒酸。雕栏玉砌以为栽种,帷幔低垂方可不雅观赏。待到深夜,以灯烛映照,朦胧月下在行抚玩,这才是雅士做派,才配得上“花王”“花相”的尊贵气度。
牡丹原产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的山间、丘陵中。最早涌现牡丹的记载在东汉早期墓葬中,是有关于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载。
牡丹作为不雅观赏用场,则始于南北朝。据《太平御览》记载:南朝宋时,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唐朝时,无论宫廷还是佛寺道不雅观,乃至普通人家的宅院,栽种牡丹都已十分普遍。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牡丹栽培中央。
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称:“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他描述当时洛阳人喜好牡丹的风尚:“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包袱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每每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
芍药的历史则更为悠久。据宋代虞汝明的《古琴疏》载:“帝相元年,条谷贡桐、芍药。帝命羿植桐于云和,命武罗伯植芍药于后苑。”帝相是夏代的君王,若以此来算,芍药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
芍药以扬州最负盛名,宋代王不雅观在《扬州芍药谱》中说:“今洛阳之牡丹、维扬之芍药,受天地之气以生,而小大浅深,一随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异色,间出于人间。”芍药的文化意象与牡丹不同,牡丹雍容华贵,芍药则旖旎多情。
《诗经·郑风·溱洧》中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诗句。上巳节时,溱洧河边,青年男女游春相戏,赠芍药以表达绵绵情意。
李清照的《庆清朝·禁幄低张》,则将芍药喻作风姿绰约的佳人:“禁幄低张,彤阑巧护,就中独占残春。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
姜夔在《扬州慢》中,则用芍药的盛开来反衬扬州城经历战火后的破落。他写道:“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二十四桥别号红药桥,原来以红芍药有名,而如今,花开依旧,冷月无声,人事却已面孔全非。
牡丹芍药,同是富贵之花,却被寄寓了不同的文化情怀。
【延伸】
“花园子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院曰花园子,盖无他亭,独占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幙幄,列市廛,管弦个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如此记载。
可见赏牡丹确实要有富贵做派。北宋时,洛阳城中雅士赏牡丹,便是“张幙幄,列市廛,管弦个中”,不但铺着帷幔,还有歌舞管弦,丝竹之乐。
牡丹和芍药,都为艳冠群芳的名花,谁列第一呢?北宋陆佃在《埤雅》中说:“今群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又或以为花王之副也。”可见牡丹第一,芍药第二,古人早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