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柱国,粟特人,年三十九,靖安吏
这句话,显然是一位当代社会的职场人对大都会发出的感叹。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是有史以来上最伟大的帝都。
但就像所有的大都会一样,长安城从出身之日就备受争议。推崇这座城市的人,比如朱子,认为长安城十分完美——布局合理,秩序井然,治安良好,活气勃勃;而讨厌长安城的人则指出长安城的实质是一个东方帝都、是一座超级坞堡,不仅城中商业布局严重失落衡,自北魏以来便实施的城市管理制度——里坊制和宵禁,使这座城市大多数韶光都循规蹈矩,去世气沉沉。基于这个不雅观点的人责怪那些对付隋唐长安城的赞颂是屈曲的,由于——“唐代长安城看似布局严整、管理有序,却是一座除了极少数“上流人士”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广大普通百姓却备受牵制、生存艰辛的’超级看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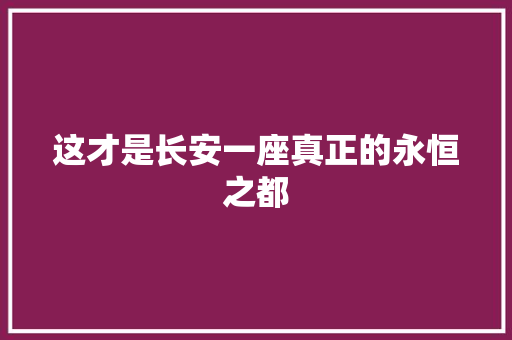
虽然汉唐之后“长安”便是“京师”的代称,比如直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仍旧称书中那个“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国”的京师为长安大都。但是严格地讲,隋唐之际,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以长安为称号的帝都。由于从唐至金,长安城的正式名称基本上一贯是京兆府,而“长安”则一贯是士庶庶民们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隋唐地坛的遗址。
初唐大道旁排水沟的遗址,
唐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建筑的大兴城。在隋文帝篡周之后的第二年,也便是开皇二年(582AD),隋文帝便决定放弃自汉以来的帝都长安城,另建一座新的都城。由于在当时看来汉长安城在规模上已经太狭小了,而且那些古老的宫殿又飘荡着了政治败北者那悲惨的冤魂和惨烈的回顾。按照隋文帝的觉得便是,汉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更主要的是这座城市自汉以来,在经由了数十万人、八个世纪的居住之后,地下水已经被污染。出身于南方的大臣庾季才就指出:
“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而且由于城北的渭水不断南移,这座都城随时都会面临灭顶之灾。于是,隋文帝君臣就决定在汉长安城东南二十里的龙首原之南,另造一座新的都城,由于隋文帝杨坚曾被封为“大兴郡公”,按照“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的原则,新都便被被命名为“大兴城”。在建城之前,隋文帝先派人前去清理龙首原附近的古坟,并建寺追福;之后又拆掉旧长安城的宫殿,将砖瓦石料及大小木料都搬到大兴城的工地上。比如修真坊的南门用的便是北周太庙的门板;而隋唐太庙实在便是对北周太庙的整体迁居——到了开元年间,这座太庙塌了,这时宰相姚崇才见告大家——太庙是隋朝建筑的,而隋朝是拆北周的,北周太庙所用的建筑材料又大多是前秦的······都三百年了,木料早就朽了,不倒不塌才不正常。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因时制宜的方法,十万民夫才能够以不到一年的韶光,即从开皇二年(582AD)六月开始动工,到开皇三年(583AD)三月将宫城基本建成。
隋朝宫城与汉长安的长乐宫、未央宫一样,都是气势恢宏:
大兴宫城东西宽2820m,南北纵深1843m;
比较之下,北京紫禁城东西宽度只有750m,南北长度是960m;
而这座新都城的外廓城则是东西9721m,南北8652m;城墙为夯土筑成,城基宽度10m旁边,高度8m——远远超过元大都以及明清的顺天府。
大兴城,也便是日后的长安城,沿袭自周朝以来的城市方案传统,实施里坊制。最初有一百零六坊,后增至一百一十坊,到了开宝年间因兴建兴庆宫和十六宅,变为一百零八坊。所谓的坊,也就现在全封闭式街区。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长安上元节。
网络游戏中的长安街市。
在唐朝,长安城中的坊按面历年夜小分为三种,个中皇城正南方的四列坊最小;宫城和皇城东西两侧的坊最大。这一百多个坊的大小是:南北,长在500m-838m之间;东西,宽在550m-1125m之间。每座坊的四周都筑有3m旁边厚度的夯土墙。大坊一样平常开四门,内设十字街,小坊则开东西二门,设一横街,坊内的街宽都在15m旁边;坊内除了街还有曲巷,宽度在5m旁边。最小的坊有20多万平方米,有三分之一个紫禁城大,最大的坊76万平方米,比紫禁城大四万平方米。坊内深处还有曲巷,宽6m旁边。有些坊里面住着几家豪门贵戚,也有的坊里住着差不多一万人旁边的平凡百姓,以是人们推测,当时的长安城中大概有百万以上的居民。坊内不仅有侯门主第、百姓人家,也有道不雅观、佛寺、酒肆、堆栈、商铺、作坊、娱乐场所等。
自周朝以来,为了治安起见,大城市基本都实施宵禁制度,也便是每到夜间坊门关闭,城内主干道上禁止人马通畅。这便是颇受现在人所诟病的“超级看守所”。但是考虑到一个坊的面积相称于明清期间一个普通县城的大小,而同期间欧洲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和面积上还不如长安城的一个坊,以是在当时的里坊制给生活带来的不便也就不会有当代人想象的那么严重。而坊的内部还是可以连续的自由往来,以至于有些坊的繁华到了夜晚便无限的繁华热闹。比如说音乐人扎堆的崇仁坊便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而平日里坊中居民的生存买卖也不必去东、西市那种国际化的商业圈,完备可以在本坊或临近各坊买到各种生活物资。
当然,和所有的大都会一样,在长安城能住在什么样的坊,常日要看你的社会地位——王侯公卿、豪门权贵都住在宫城附近。这些人每每住在一样平常人无法想象的豪宅之中,花园中有着像自雨亭这样的高科技设备。撤除这些顶级豪宅之后,庶民阶层能住进什么样的坊,那就要看你的财富或能力。为了严格掌握长安城的房价,朝廷对不同的阶层的人居住什么样的宅院有着规定:良民三人以下一亩宅,三人以上加一亩;贱民五人以下一亩宅,五人加一亩——条件是你们买的起。靠近宫城,能够和大人物做邻居的那些“高档社区”全部被富商或能工巧匠们霸占着,没钱没势没能力的人只能住在冷落荒凉的南城和种菜的农工资伴。
长安一百零八坊。
晚唐西市
晚唐东市
也便是说,长安城确实是个充满了贫富悬殊,物欲横流,只相信实力不相信空想和眼泪的无情天下。在这里,只要足够强大你就可以傲视天下,为所欲为;而如果你贫穷、平凡,那等待你的便是王起明或卡捷琳娜乃至是于连·索雷尔的悲惨命运。大明宫、平康坊那如梦似幻的繁华壮丽,在短暂的陶醉了每一个长安城的新客人(长安城没有主人)之后,就开始无时无刻的提醒着这个天下——长安城既不是乐国乐土,也不是个“超级看守所”,而弱者的绞肉机······
但是,古今中外,那个大都会不是如此呢?
中唐往后,里坊制开始逐渐崩溃,一开始是有人由于在坊的外墙上打洞并且违反宵禁,展开夜市贸易。之后便是逐步的侵略宽阔的街道,搭建违章建筑。为了担保朝廷对长安城的完备节制,唐家天子多次敕令清查“乱象”,我们看看朝廷的方法: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AD)五月,诏令:
“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罚统统不许,并令毁拆。”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AD)仲春,再次下诏:
“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毁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建”。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AD)七月,左街使上奏:
“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略禁街”。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AD)有旁边巡使卜奏说长安坊门:
“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
至太和十六年唐文宗又再次下敕书引用过一条早已过期的律令:
“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此时的里坊制已经是有名无实。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里坊制溃散之后,长安城的时期也随之成为历史。
从安史之乱往后,被后人想象为“军事要塞”的长安城竟然犹如纸糊的一样平常——安史叛军、吐蕃、朱泚、黄巢这些内忧外祸都曾经盘踞长安,天子以“巡狩各处”的名义播越蒙尘更是不绝于史,以至于有“长安六陷,天子九迁”的说法。而关中自身的经济规模也无法支撑百万帝都人口、黄河砥柱天险也每每导致关中地区的漕运不便、政治重心东移更是大势所趋······
至天祐元年(904AD),叛将朱温胁唐昭宗迁洛阳,尽毁长安宫室民居。又以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驻守长安。 当时的长安城城墙毁坏不堪,不利防守,于是韩建利用唐朝皇城的城墙修建新城,封堵了南面正门朱雀门,东北角与宫城交界处的延喜门、西北角的安福门,同时在原皇城内尚书省东半部和左骁卫、左武卫的位置增筑了一座子城,将长安变成了一座大军营。从此千年的岁月中,长安城变成了一个去世气沉沉的地方。
但那个伟大,但绝非空想的长安时期却化作了传说中盛世乐土,勉励着后人,培植着当下,憧憬着未来。
长安,永恒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