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人质疑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了,由于他在诗的末句里提到了“夜半钟声”。但是,哪里有寺庙会在半夜敲钟呢?
只管从唐朝开始,就有许多张继的支持者举证解释:寒山寺在古代,真的有在夜半敲钟的习气。但是,辩论依旧没有停下来。
实在张继的这首诗,问题不只出在“夜半钟声”上。当张继写下第一句诗时,就已经注定要出麻烦了。由于他这首诗光是第一句,就被当代人挑出三个“悬疑”。
一、“月落乌啼霜满天”的三大“悬疑”首先,“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鸟。其次,这句诗究竟写的这天间还是晚上。末了,霜明明在地上,为什么要说“霜满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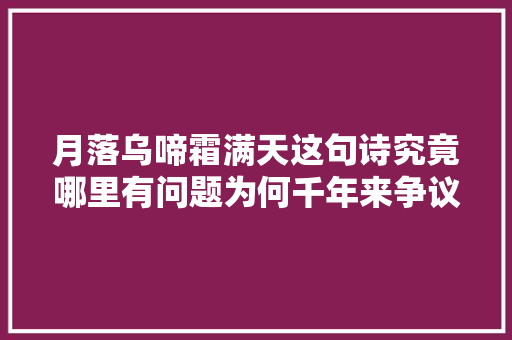
由于这三个问题的前两个是密不可分的,以是我就合在一起讲了。“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一句诗,紧张是在交代事情发生的韶光,以及当时的景象。
公民文学出版社八零版的《新选唐诗三百首》中说,这一句写的是“秋日的夜晚”,玉轮落下去了,乌鸦开始啼叫。
而中华书局的《唐诗三百首详析》,也做了差不多的阐明。韶光是在“半夜”,以是才能和末句的“钟声”相呼应。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同样说是“一个秋日的夜晚”。
但是,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哪有乌鸦会在秋日的夜晚啼叫的?由于乌鸦只会在薄暮或者是清晨的时候啼叫。
于是,有一位叫徐文的学者提出:这里的“乌”实在不是指的乌鸦,而是指的乌臼鸟。并举了南朝乐府民歌《读曲歌》为例子: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这首民歌里面说,要打去世啼鸣的大公鸡,再弹走“乌臼鸟”。由于,唱歌的人不想天亮。他大概是想睡觉,巴不得一年才天亮一回。
由于鸡是清晨打鸣的,以是可以证明“乌臼鸟”也是在清晨啼叫。可见,《枫桥夜泊》中写的事,实在也是发生在一个清晨。
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不过在民间,还是有许多的人和他一样,认为“月落乌啼”发生在一个清晨。
月落一样平常有三个韶光段:一,农历每月月朔至初十,上半夜;二、农历每月十一至二十,下半夜;三,农历每月二十一至末了一天,清晨。
仿佛并没有什么鸟儿会在半夜啼鸣,因此月落的韶光就必定是清晨。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大出版社,这么多的诗词专家,非要说写的是“半夜”呢?
这是由于,张继在诗的末句直接写明了韶光是在“夜半”。如果诗的第一句写的是清晨,那么这首诗的韶光跨度就太大了。刚刚还在讲早上发生的事,结果莫名其妙又写到了半夜,说不过去。
于是有人提出一个不雅观点,说这里的“乌”并不是指动物,而是指“乌啼山”。明月从“乌啼山”的背后落下,天空中繁霜暗凝。其余,不但“乌啼”是指一座山,连第二句中的“愁眠”也是一座山。
可是,这乌啼、愁眠二山,本来便是先有了张继的《枫桥夜泊》后面才得得名。以是关于这个“乌”字的辩论,以及诗的第一句到底写了清晨还是半夜,辩论还没有结束。
至于“霜满天”,也有人认为是缺点的。由于霜是在寒冷的景象中,由地气上升,在地面和草叶上凝集而成。它是不可能生到天上去的,以是张继是在胡说八道。
也有人阐明说,墨客当时正在渔船中睡觉,溘然被乌鸦叫声惊起,然后探出头来向外看。首先看到的是凝霜的树枝在水面上的倒影,以是他说“霜满天”不为错。
不过也有人说,当时都“月落”了,他还能够看清楚倒影吗?可能是由于空气太寒冷了,引发了他的想象罢了。
二、要“唯美”不要逻辑张继这首诗从唐代开始,就一贯走红。近代各种诗集抄本,蒙童读物里面都有它的身影,起影响力可以算是非常大。
近代学者俞陛云认为:唐代七绝佳作如林,就只有《枫桥夜泊》这一首传到了日本,并且还是“凡妇孺皆习诵之”。中外共赏,可见其魅力之强。
为什么这首诗能有如此高的报酬呢?由于这首诗的意境非常幽美,以是只管诗里面有很多的未解之谜,大家还是对它十分追捧。
张继这位墨客,现在留下来的干系资料比较少,只知道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进士及第。可见,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而且他曾经当过盐铁判官。
《复兴间气集》说他是:“其于为文,不事雕琢。诗体清迥,有道者风。”意思便是说他写的诗,不刻意讲究修辞。风格清新,分歧凡响,有一些道家的风范。
以是张继创作这首诗的韶光很可能极短,只是兴之所致,随意发挥的结果。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他进士及第之后,还没来得及等朝廷封官,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张继只得从京城孤身出逃,途经苏州,在秋日的夜晚泊于“封桥”。后来,这座桥也由于他的诗改名为“枫桥”了。
半夜里,乌鸦被什么东西惊飞,因此才有了“月落乌啼”的名句。至于“霜满天”,有可能不是他眼里见到的真实景象,而是他对那个寒夜,以及当时的环境起的“生理感想熏染”。
张继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内心是充满了忧惧与哀愁的。《唐才子传》中说他是一位博学多才,为官有道的能人,在政治方面享有良好的荣誉。
但是当时的国家动荡,他个人的出息也变得十分渺茫。在亡命的状态下,他根本没有心情去打磨诗作,只能随感而发,而且不雕琢本来便是他的风格。
不过,正好也是由于他的这种风格,才造就了这首诗的“开放性”,让读者有了“无限阐明的可能”。
结语诗歌对付写作者而言,实在是通过笔墨传达自身感想熏染的一个载体。而诗歌对付读者而言,是通过笔墨引发想象的一个媒介。
读诗实在就犹如我们读小说一样,“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诗歌的读者,本身便是诗的“二次创作人”。
有人批评张继这首《枫桥夜泊》,为了“唯美”,没有把诗“写通”。实在,我以为完备没有这个必要。由于诗歌是一种抽象艺术作品,完备合乎逻辑的东西,对付艺术而言是去世板的。
以是,不管“乌啼”是什么,也不管第一句写的是夜晚,还是清晨,或者这天间,更不要去管寒山寺半夜到底敲不敲钟。
通过阅读这一首诗,让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完全的“故事”。只要你真正能够感想熏染到它的那种美,也就即是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