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两袭盛世帷幕下的两朵绮丽烟花,虽都能各自燃起一片夜空,但常日它们都被放在一起进行评论辩论。如果想要找出一条诗与词之间的分边界,是尤为不易的,它们仿若红莲白藕,自擅胜景,有人喜好似火的莲花,有人喜好清致的白藕,然而却很少有人两者都爱,这是为什么呢?
在此大略举一个小例子。王安石曾有一首词叫《桂枝喷鼻香·金陵怀古》,是入选过语文教材的经典之作,相信大家都曾在教室上对之苍茫踯躅,摇头晃脑地背诵过。然而我们读到末了两句\公众六朝往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大众时,却不禁创造:为何这个场景如此熟习?
那是由于商女唱后庭这个典故实在太出名,大家都知道它出自杜牧的《泊秦淮》,以是当初小解读到此句时也是很纳闷。
因此,只要你深入到诗词国度中去,就会创造红莲白藕这个形容是非常恰当的:唐诗如红莲,宋词如白藕,先着花后结果,先有红莲后有白藕,红莲妖冶过后,白藕就从红莲中汲取营养,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内容,即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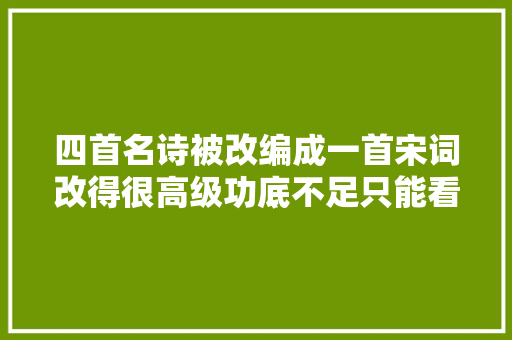
当然文人之间的汲取,可以用\"大众致敬\公众、\公众借鉴\"大众或\公众引用\"大众等专业名词进行阐明,有时候这种致敬还能催生出不错的作品,比如小解下面要先容的这首姜夔的《扬州慢》,便是汲取古人聪慧的精良代表,这首词也曾入选过语文教材。
《扬州慢》宋·姜夔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东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薄暮,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这首是姜夔词清雅空灵特色最显著的一首,乍读之下仿佛意象美好、句句新鲜,但实际上它却隐含了\公众杜郎\"大众即杜牧的四首名诗,分别为:《赠别》、《遣怀》、《题扬州禅智寺》和《寄扬州韩绰判官》,由于篇幅较大,在此就不一一贴出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搜索理解。
姜夔或勾引、或顺承、或化用、或逆转,将杜牧的名篇名句完美嫁接到自己的词中,险些每一句都能索见杜牧之的影子,但每一句又都有姜夔的身姿!
虽然此词改编得非常高等,让人无法认定为\公众抄录\公众,但有一些意象太经典,读者还是能窥伺一二。
比如\公众纵豆蔻词工\公众中的豆蔻,最先将它写进诗词里的人便是杜牧,这个意象太明显,以是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来自《赠别》中的\公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仲春初\公众一句;再比如\"大众二十四桥仍在\"大众则出自于《寄扬州韩绰判官》的\公众二十四桥明月夜,美男何处教吹箫\"大众一句。
这两处是比较随意马虎被创造的,一样平常功底的人或许也就只能创造这两个地方。剩下两处,一个比较随意马虎,一个比较困难,不知各位看官能够创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