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墨客不爱沉浸在古人的陈词谰言中,由于不破不立,无法摆脱沿袭的线路,究竟是写不出好诗。像如今许多墨客,他们作的诗词不可谓不美,但无法令人产生读到唐诗宋词中名篇时的惊艳之感。
究其缘故原由,还是未能摆脱古人的意境,未能写出令人线人一新的句子。写来写去,不过是类似的措辞在相互改换、套用,“小楼”换成“庭院、“东风”换成“微雨”,读来味同嚼蜡。诗本来便是一种非常精髓精辟的文体,若是太多陈词谰言,实在无趣。
由此,许多墨客会以一种“反常合道”的描写,塑造新奇的意境。而“反常合道”便是墨客最常用的,但也是难用得好的。所谓“反常合道”,即跳出了惯有的思维,初读只觉无理,再读却觉理在个中,是为“无理而妙”。
一、字词的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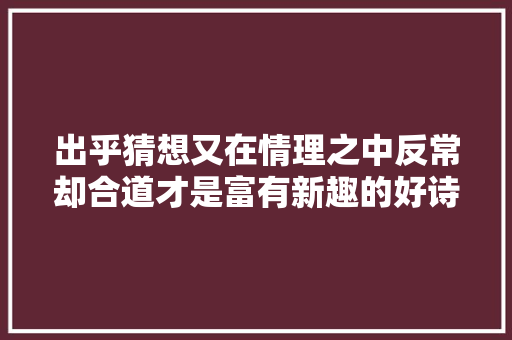
诗词的特质在于精髓精辟,故而墨客常有炼字之说,故而活用字词造就新颖的意境,是墨客常用的写作技法。
比如宋伯仁的《秋晚》有句“红叶已霜天欲雁”。如果按照当代汉语来逐字阐明,多数会落得“狗屁不通”的评价,但有一定古诗词根本的,却能感想熏染到句中蕴含着一种秋意。
句中“霜”本是名词,这里是用作动词“降霜”。当然,如此活用也是常见的。这句诗妙就妙在“天欲雁”三字。我们常会说“天欲雨”、“欲雪”,这从天象的变革可以看出。
然而怎么样的氛围环境,是飞雁掠过的天?是满山红叶?是落木萧萧?三个字,蕴藏着让读者想象的无限空间,新颖而故意境。
再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字,是常常拿来作范例的活用名句。想来红杏如何闹,但正如王国维所说,这一“闹”字,意境全出。
二、奇瑰的想象
写诗要有渊博的知识,要有对生活的洞察,更要有丰富想象力。当然,想象不是毫无根据地大开脑洞,而是要“似出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比如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将雪比作柳絮。韩愈“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则更为新奇,他将雪拟人化,想象雪是由于嫌春天来得太晚,故而自己穿过庭院的树枝,散作飞花。
李白《望庐山瀑布》“疑是银河落九天”同样是极为奇瑰的想象。“银河”虽然称河,但并无水,如何落成瀑布。可那渺远从云端倾泻的巨大水量,若非“天上之水”,何来如此声势?
三、常用字的“另类”搭配
诗词本便是用常见的汉字,组合成一首首俏丽的篇章,就像神奇的匠人,用砖瓦布局俏丽的建筑。而有些看似不干系的常用字,搭配在一起每每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杜甫有一名联“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后世学者对这两句诗夸奖不已,尤其是下半句,向来被认为是神来之笔。“江声”、“白沙”本是常见意象,然而中间添一“走”字,格调极为非凡。“声”本来用“传”,用“响”,“走”字似无理,但读来似觉江声在耳。
像这样“反常合道”的创作技巧还有很多,难以逐一归纳,但反常随意马虎,难在反常还要合理。《围炉诗话》云:“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出人意外,入人意中,才是富有奇趣的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