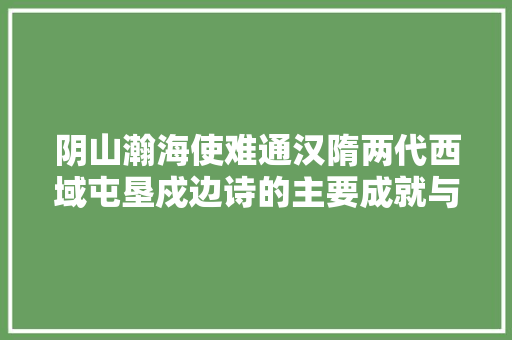艺术会表现人们的生活图景,也会表现一些重大事宜。在屯垦的同时,人们创作了一些诗词、民歌,反响了屯垦生活。也有的文人去西域做官、出使访问,创作了描述西域风景的边塞诗。西域有很多民族,一些诗词也反响了不同民族之间和平交往的景象。
汉代的屯垦戍边诗《小麦谣》诗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
西汉期间,中原王朝就在西域屯垦。这时,汉民族初次与西域各民族有如此多的往来,汉朝人的一些诗作反响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往来。部分诗词反响真实历史事宜,还有一些则带有美好的艺术加工。
汉朝的屯垦戍边诗紧张是一些乐府诗,例如《西极天马歌》、《天马》、《陇西行》、《小麦谣》等,还有一首是远嫁乌孙的公主刘细君撰写的反响汉与乌孙和亲的《乌孙公主歌》。反响屯田农人与屯田兵的民歌难以见到。
《西极天马歌》、《天马》与《乌孙公主歌》为皇族所写。前两首均为汉武帝所写。《西极天马歌》又称《蒲梢天马歌》。在《史记·乐书》中也有关于该诗的记载。司马迁认为,汉朝进攻大宛,得到名马,这匹马叫做“蒲稍”。以是又称为《蒲稍天马歌》。
由于是乐府诗,该诗可搭配乐曲歌唱。古代乐谱今已不存,结合笔墨,应该搭配楚声曲调。《汉书·礼乐志》记载,李延年编了新的曲子,司马相如又把这首诗改成三字一句。《天马》诗共有两首,也是汉武帝所作。
两首诗内容相似,汉武帝认为,得到天马蒙神仙“太一”保佑。天马的外表与普通马不同,流赤色的汗,也即本日的汗血马。天马体态平均,脚步轻盈,乃至能够踏上云彩,见到天空上的龙。
第二首诗汉武帝先鼓吹自己的功绩,接着描述了天马的外表,对其进行歌颂。对天马的外表描述更加神乎其神,马背有双脊,解释此马极其强壮。汉武帝也对天马进行了一些想象,认为天马能像鬼神一样变革。在在诗词末了,汉武帝也把天马与龙写在一起,足见此马神骏。
汉武帝所写的天马诗,都抒发了武帝得到天马后对天马的喜好之情,个中也包含了汉武帝对自己功绩的吹捧。在诗词中,不仅仅是直接描述天马的外表、神态,而且对天马有一些合理的想象。把马比附成龙也是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的征象。
公主刘细君撰写的《乌孙公主歌》可以认为是戍边诗。这首诗表示了远嫁的公主远嫁乌孙,但是措辞不通,内心愁苦。《天马》与《乌孙公主歌》都是由皇族书写的,无法反响公民详细的屯垦生活。
《小麦谣》是汉桓帝期间,凉州诸羌反对汉朝,发动战役,市价麦收时令,男子从军,女子收麦,于是她们唱出了这首民歌,表示了贫穷的民众对汉朝官吏的不满。《陇西行》赞颂了陇西女子主持门户、礼貌待客。
语句幽美,利用比兴的修辞手腕。在后续的描写中,突出陇西特色,例如,客人坐的是毡褥。也描写了陇西女子招待客人饮酒用饭的情景。末了,作者认为这位女子赛过男子。汉代的西域屯垦诗紧张形式为乐府诗,既有贵族文学,又有出自民间,表示民众日常的诗作。
隋代的屯垦戍边诗
《隋书·文学传》记载:“隋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既乎登基,一变其风“。
隋代年代很短,保存下来的屯垦戍边诗不算很多。紧张是隋炀帝杨广、丞相杨素等人撰写的边塞诗。由于隋朝曾与突厥作战,将士们驻扎边塞,或写诗记录战斗生活,或写诗描述边地风光,还有的借边塞景致抒发思乡之情。
隋炀帝本人才艺水平不算低,他撰写的诗词有英气、雄浑的风格,但是也有部分描述风景的词华。隋炀帝、杨素、薛道衡以及虞世基的诗词中都有描述边塞风光的语句。风沙、陇月、烽火台、阴山等意象共组成边塞图景。
还有的诗词表示了将士降服后的喜悦之情。例如隋炀帝的《饮马长城窟示从征群臣》,个中有“单于入朝”、“晨光高照”等意象,这些意象都表示了将士们降服之后的喜悦之情。薛道衡的《从军行》利用了典故。
利用典故都出自史籍,而不是传说。例如“擒冒顿”、“纳呼韩”、“刺楼兰”等。有的诗词中描述较为夸年夜。在隋炀帝的诗词中,有“千乘万骑”、“横漠筑城”的意象。横漠筑城即在大漠上横着修建一条长城。
王胄的诗词中有“羽骑浮云”、“长旌蔽日”的意象,这也是常见的夸年夜修辞。这些诗词都是有名有姓的作者所写的,还有三首诗作者无名氏,分别是《叹疆场》、《回纥曲》与《塞姑》。这三首诗的风格像唐诗。
全篇没有形容词,都是叙事,通过叙事,墨客所抒发的感情得以活灵巧现地表现出来。以是说,有人认为这三首诗是唐代所写。如确为隋诗,足以解释隋末诗词风格逐渐向唐诗转变。
汉隋西域屯垦戍边诗之特色
《后汉书》记载:“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
汉代与隋代的西域屯垦戍边诗有不同的特色,汉乐府诗词继续《诗经》、《楚辞》的部分特点,此后南朝诗词是一脉相承的。都重视铺陈、形容,部分措辞相对华美,想象丰富。也有的乐府诗叙事措辞较为平实。例如,汉代与隋代早期的屯垦戍边诗多用比兴、用典的修辞手腕。
汉代的《陇西行》在开头利用了比兴的手腕,这一手腕《诗经》、《楚辞》均有利用。《诗经》中的比兴多用日常生活中的意象,例如雎鸠鸟、芦苇等。《陇西行》中的比兴,用到了白榆、桂树、青龙、凤凰、凤凰九雏等意象。
表面上看,这些意象是现实与神话生物,实则,这些都是天空星宿名,可见作者想象丰富。张玉谷认为,《陇西行》的比兴,天上星宿成双成对,而人间间的陇西妇女没有丈夫和儿子,天上与人间形成比拟。《陇西行》后续的内容都是叙事,着重刻画陇西妇女待客的情形。《乌孙公主歌》也塑造了鲜活的乌孙公主形象。
《小麦谣》措辞平实,起兴只用“小麦青青大麦枯”,措辞平实,类似《诗经》。汉武帝的一系列“天马诗”既有叙事又有一定的想象成分,例如汉武帝想象乘着天马飞上天空,与真龙相见。
汉魏诗词一脉相承,隋诗上承汉魏,下接唐诗。隋初的诗词仍有南朝炼词用字的风格。在情绪表达上,比起南朝诗歌更为积极。到隋末,诗词风格与唐诗类似。汉隋两代的西域屯垦戍边诗的特点,符合这两个时期诗词的共性。
从汉到隋,诗词的风格是不断变革的,汉代屯垦戍边诗紧张形式是乐府诗,隋朝的屯垦戍边诗的特点介于汉魏与唐朝诗词之间。既有反响民众日常生活之民歌,也有皇族、将领撰写的,反响西域风光、作战的诗词。
结语
汉与隋两代的西域屯垦诗都有一定的艺术造诣。从数量上看,汉乐府中的屯垦诗词存世不算很多,但是类型较为多样。尤其是《陇西行》与《乌孙公主歌》,塑造了维妙维肖的人物形象。
《陇西行》一诗则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描写人物与生活细节。隋朝一代的屯垦戍边诗风格存在转变。文学风气的转变与时期有关,隋朝统一往后,武功突出,诗词的风格在保留南朝风格的同时,逐渐倾向豪迈雄浑。隋末的西域屯垦诗,风格渐类初唐。
参考文献【1】《后汉书》
【2】《文选》
【3】《隋书·文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