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劳。
这首1200多年前的古诗想必无数人都已经耳熟能详,在无数人的孩提时期,父母长辈会在我们不好好用饭或是摧残浪费蹂躏粮食时为我们朗诵这首唐诗,他们想让我们明白碗中饭食来之不易,不应轻易摧残浪费蹂躏。
当我们也成为父母,又会在碰着相同的问题时,教会自己的孩子这首古诗,让他们也明白,珍惜别人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是一种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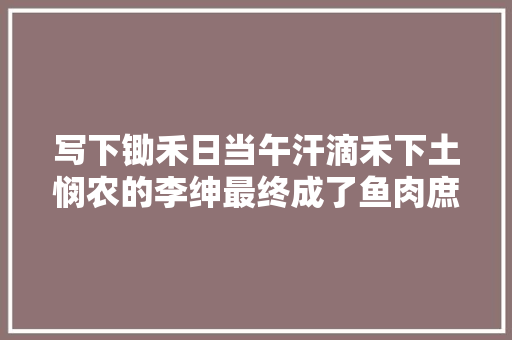
实际上,《悯农》并不是只有一首,只不过“锄禾日当午”这篇过于出名。如果要问,人们最先打仗的唐诗有哪些,那么这首“锄禾日当午”大概率排名前三,以至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首诗的名字便是《锄禾》。
由于它实在太过随处颂扬,也太过的深入民气。就这样,这首诗传承了1200多年,教会一代又一代人懂得珍惜,也让我们记住了作者李绅的名字。
而李绅也由于这两首《悯农》碰着了他仕途上的伯乐,只可惜做官后的李绅并没有成为一位“悯农”的好官,反而成为了一名鱼肉百姓的酷吏。
绅本世家子,幼年丧双亲
李绅出身名门,其曾祖李敬玄在武则天期间曾担当过中书令这样的高官(宰相职),其祖、父两代虽然没能将官职做到中心,但在前朝宰相的荫萌也在地方上有一番作为。
出生在这样一个三代为官的家里,称李绅一句“世家子弟”,想必大家是不会有见地的,李绅也因此在自己的幼年时期就打仗到了诗书礼乐,见识到了无数王侯将相关顾自家门庭的场面。
可是好景不长,在李绅6岁那年,父亲李晤撒手人寰,李绅自此暂时告别了绫罗绸缎、鲜衣美食的生活。
其母卢氏聪慧贤德,她非常清楚李家世代为官会结下不少政敌,而丈夫离世后正是他们对李家后人下手的好机会,而此时,之前所谓的“朋友”又是断然不会至心帮助自家的。
于是,母亲带着年幼的李绅和其兄长离开丈夫任职的乌程县,迁往无锡居住,并亲自教授李绅及其兄长识文断字。
可惜福无双至,灾患丛生,三年之后母亲卢氏也随夫妻李晤而去,只留下李绅和兄长相依为命,两人从原来的世家子弟沦为了流落无依的孤儿,那一年李绅年仅9岁。
年幼李绅在纷至沓来的变故面前并没有选择沉沦,虽然与兄长二人的生活清苦,但兄长一贯对他偏爱有加,李绅也一贯没有放弃习文段子,十来岁便已将科举的“经义”牢记于心,他要重走仕途路、靠自己的努力重振家风。
地虽生尔材,生不与尔时
清贫的日子一过又是五六年,此时的李绅已经来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风华男子。
为了减轻兄长的包袱,李绅离家前往风光奇丽的惠山寺,但他并不是为了寄情山水,而是欲借这一方清净之所连续提高自己的学问,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胸中才华,实现心中抱负。
可是现实远比他想象的困难,虽然在这里他逐渐展现出自己的才华,但也由于无限制地在佛经的空缺纸张上写诗被赶出庙门,开始了风餐露宿的生活。
无人的船只、破旧的牛棚、亦或是四处漏风的寺院,这些都成为了那是的李绅的居住之所。
逐渐地,他的诗开始得到众人的认可,得到了一个“短李”的名号,受到了众人赏识。
可是这还不敷以实现他重振家声的欲望,李绅明白,科举场上的一鸣惊人才是他实现空想的唯一路子,但在这之前,李绅须要让自己的名气再大一些,以便于在参加科举之时得到更高的排名。
27岁那年,前往亳州探亲的李绅碰着了浙东节度使李逢吉,二人登上不雅观稼台望着丰收时节劳作的农夫和堆积如山的粮食都感慨不已,但不同的是,李逢吉的心中期待是升官如登台般顺畅,而李绅当时却关心的是面前费力的农夫。
于是他吟出了那两首传世佳作《悯农》,一首描述了农夫在烈日下费力垦植的场景,便是日后那随处颂扬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劳”;而另一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而去世。”的诗句,则是写出了他对农人们一年的辛劳劳作却换不来饱腹机会的怜悯,和对统治阶级无休止地残酷剥削行为的不满。
他也带着这两首前往长安,开始了他的科考之路。
可是入仕之路并非坦途,虽然这两首得到了多人赏识,但是却没有帮他在科考中胜出,榜上无名是他第一次科考的宿命,而接下来的几届科考,李绅也都是名落孙山。
但在这期间他也并非没有收成,至少他在长安结识了吕温、韩愈、刘禹锡等当时的俊杰之士,并和白居易和元稹成为了至交好友,也为他们日后的“新乐府运动”打下了根本。
或许,此时的李绅还没有等到他的机会,但是机会正在悄悄地向他走来。
拂袖辞官去,因祸得福归
公元806年,第四次参加科考的李绅终于得中进士,被分配到国子督工作。
可是,好不容易挣来功名的李绅却对自己的职务非常不满,于是,以为自己被大材小用的李绅愤然辞官,离开都城长安。
在经由一段流落之后,李绅前往金陵投靠了镇海节度使李锜并很快受到赏识,卖力其军中的文书事情,李绅也光彩自己终于碰着了伯乐,决心跟随李锜大干一场,实现自己胸中抱负。然而,此时的李锜却早已有了背叛朝廷的念想。
可当时的李绅虽然仕途不顺,但还是忠于李唐王朝的,当李锜命他起草起兵檄文时,李绅冒着被杀头的风险谢绝从命,终极关在狱中将近一年,此时的李绅还算得上一个铁骨铮铮的男人。
李锜的这次兵变并不堪利,一来由于他本人随有皇族血统,但究竟只是高祖堂弟李神通一脉之后,算不得皇室嫡脉,因此他的兵变归根究底还是翻盘,很难得随处所和百姓的支持;
再者,他部下的幕僚有太多人和李绅的态度同等,都是反对他起兵的,这也导致了在他起兵之后,部下人联合他的外甥一起“反叛”将他生擒,不但自己落得个兵败身亡,还连累他的儿子一起被杀的结果。
李锜去世后,李绅得以摆脱囹圄,并由于其已去世来反对李锜起兵的行为得到了朝廷的把稳,得以返回长安为官。
这一次,李绅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仕途之路也开始平步青云。
从37岁那年担当教书郎并与故友白居易和元稹一起开辟新乐府运动,凭借着一首首针砭时势,反响百姓疾苦的诗词开始,到75岁病逝于淮南节度使任上,李绅在这近30年韶光里仕途顺利、官运亨通,长期担当地方大员不说,还曾出任过宰相一职,受封赵国公,权倾朝野。
可是,他却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对老百姓贫苦生活悲悯备至的墨客了,相反,为官后的李绅非但没有拿得脱手的政绩,反而很快变成了一个生活上奢靡成风、奇迹上剥削百姓、为祸一方的酷吏昏官。
无权时悲天悯人,得势后忘怀初心
如果只是从李绅的两首《悯农》来看,大部分都会认为,这样的人如果日后能够为官,必能成为一名造福一方百姓的好官,可是李绅很快就让所有人失落望了。
由于儿时的生活过于悲惨,有目睹过百姓真实的疾苦生活,李绅在初登仕途时确实为老百姓做过一些实事,算是对得起他“悯农”的本心。
可是随着官路越走越顺,李绅不但变得架子越来越大,也将初心忘了个一干二净,仗势欺人、剥削百姓的行为比比皆是。
面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叔父”李元将,得势后的李绅却翻脸不认人,丝毫没有顾忌昔日恩典,居然大言不惭地哀求李元将称其为“祖父”,这岂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面对前来拜会之人,无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寒门士子,乃至是曾经的同科举人,只要他们的做法没有让李绅满意,轻则冷眼相待,重则棍棒奉养、流放三千里,可以说李绅是将利令智昏和仗势欺人表示的相称淋漓尽致了。
而在对待百姓时,为官前李绅对他们的境遇有多悲悯,为官后李绅对他们的手段就有多残酷。
在他为官期间,百姓们由于无法忍受他无休止的剥削,无数人选择逃离他管理的地方,而李绅在听得手下报来的百姓外逃的后却流传宣传,逃走的不过是糟粕,留下的才是精华。
于是乎,他开始对留下的这些精华们变本加利地盘剥,各种税收压得当地百姓更加喘不上气。
而他本人却利用捐税为自己猖獗敛财,用这些民脂民膏过着奢靡的生活,在他的府上,摧残浪费蹂躏早已成为一种习气,虽说比不上《雍正王朝》中年羹尧一顿饭动辄十几二十个菜,吃白菜只吃菜心,吃猪肉只吃活猪里脊那样奢靡,但是顿顿大鱼大肉,吃不完直接倒掉的征象还是存在的。
此时的李绅怕是早就忘却了自己从前间发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劳”这样感慨时的心情了,又那顾得上农夫会不会饿去世呢?
除此之外,李绅在担当司空时曾在府中无数美艳女子,著名墨客刘禹锡就曾在拜访李绅时被其家中的奢靡场景所震荡,留下了那首传世佳作《赠李司空妓》和一个“司空见惯”的针言。
而咱们李司空也实属大方,随手将诗中提到的杜韦娘“赏”给了刘禹锡,能将人当做物品一样平常随便赠与他人,李司空的奢靡和豪横可见一斑,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悯农”墨客了。
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李绅之以是能够在第二次入仕之后一起平步青云离不开一个人,那便是依赖其身居相位的父亲李吉甫的福荫而入仕,日后自己也登上宰相之位的李德裕。
李绅和李德裕二人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年事相差了15岁,但丝毫不影响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可以说,李绅的发迹是在李德裕的一步步扶持下实现的,而这时候的李绅也非常懂得“知恩图报”,牢牢地跟在李德裕身边,对他唯命是从,乃至不惜与他一起卷入晚唐时著名的“牛李之争”之中。
而李德裕也在掌权之后,对作为其得力干将的李绅关爱有加,一起将他擢升为刺史,节度使,知道宰相这样既有兵权又有政权的实权职务。而李绅也利用自己的权利,全新全意地为李德裕肃清政敌。
公元844年,已经74岁的李绅从相位上退下,迁淮南节度使,总督江淮军政。虽然已经是行将就木,但李绅还是竭尽全力地为李德裕做事着,当他接到有人对扬州江都县尉吴湘贪污和强娶民女的举报时,李绅立即敕令将抓捕吴湘。
经由审理,吴湘贪污的罪名坐实,但贪污的金额并不敷以判处去世罪,而关于他强抢民女的举报纯属无稽之谈。
但是,吴家和李家是有世仇的,吴湘的叔父曾因和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政见相左而得罪了李吉甫,这次吴湘落到自己手里不正是给力自己一个谄媚李德裕的好机会吗?
说不定此时之后,自己还能有升官的机会。想到这里的李绅决心置吴湘于去世地,于是他不顾朝廷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们的建议,独行其是,判处吴湘去世罪,斩其于闹市。
李绅这样的举动令李德裕心情大好,但同时也激怒了朝廷中的很多官员,他也因此没有再得到升迁的机会。一年之后,李绅病逝于扬州,但是他的“官运”却并没有由于他的去世亡而停滞。
李绅去世后不久,宠信李德裕的唐武宗病逝,新天子唐玄宗登基后整顿朝廷党争,吴湘一案被认定为冤案,成功平反。李德裕被罢免宰相一职,离京任职,李党至此分崩离析,其成员全部受到牵连。
依照当时唐朝的律法,李绅随已身死依然被贬官三级,去世后被封的太尉关衔被收回,其子孙后代也失落去了再走仕途的机会。
曾经一位心怀天下贫民的“悯农墨客”,却在为官后醉心权利,忘怀初心,终极成为党争的捐躯品。他笔下那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劳。”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去世。”的诗句现在读来,仿佛两记耳光,狠狠地扇了为官之后的李绅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