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韶光,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有关《孟子·告子下》异文的全民学术大谈论,论争双方对付究竟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各自为政,不少网友翻出语文教材据理力争,不想结果出人意料,原来不同版本的教科书竟也存在“斯人”与“是人”两种记载,孰是孰非一度陷入僵局。实在,古诗文涌现异文绝非个别征象,譬如诗仙李白的《静夜思》,中日两国教科书就存在明显差异,海内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昂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日本方面却作“床前看月光”和“昂首望山月”。此外,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随君直到夜郎西”和“随风直到夜郎西”之别,周敦颐《爱莲说》有“众人甚爱牡丹”与“众人盛爱牡丹” 之异,王安石《泊船瓜洲》也有“东风又绿江南岸”与“东风自绿江南岸”之分a。随着互联网的遍及,类似论争险些每一次都会引发不小的波澜。事实上,这类异文不独见于古诗文,在其他类型的古文献中也普遍存在。因此,不能像有的网友那样把任务大略归咎于任务编辑校正不到位,它们反响的实际是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版的一个共性问题——古诗文选篇的版本问题。本文即以《孟子》为例,解释稽核古籍版本源流对付编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古诗文篇目的主要性。
a 关于《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随君”与“随风”的问题,如公民教诲出版社2016版七年级语文上册记载为“随君”,而江苏教诲出版社 2006 版七年级语文上册、北京师范大学 2010 版高中语文选修《唐诗欣赏》等写作“随风”;有关《爱莲说“》甚爱”和“盛爱”的情形,如公民教诲出版社 2007 版八年级语文上册记作“盛爱”,而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 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公民教诲出版社 2016 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等都为“甚爱”。不过,《泊船瓜洲》一例其实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并未涌现不同的文本记载,其详细情形留待后文揭晓。
1《孟子》紧张版本源流的稽核
《孟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其篇数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西汉司马迁称:“(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汉书·艺文志》却著录《孟子》为十一篇。东汉赵岐放弃注《孟子》外四篇,外四篇逐渐亡佚,后世遂以七篇为天命。由于《孟子》成书较早,加之其作为儒学文籍的分外地位,版本流传情形颇为繁芜。顾永新曾将经学文献概括为以“正经注疏”“五经四书”两个主干系统为主,加之其他系统或载体的流传形式[2],笔者将大致沿着此思路来谈论《孟子》的紧张版本,兹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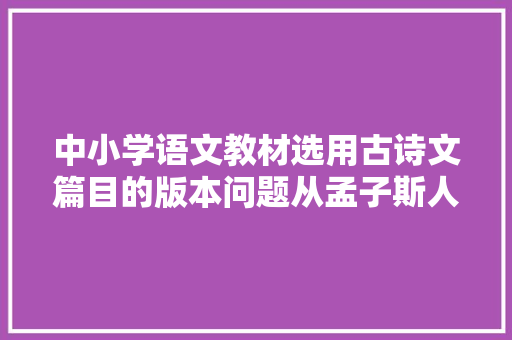
第一,白文本。目前所知《孟子》较早的白文刻本,为宋刻递修巾箱本《八经》十卷本b。明末崇祯年间,求古斋曾据宋巾箱本订正重刊,清代民间书坊也多有重印。传世的白文《孟子》以清代版本为主。康熙、乾隆两朝分别敕编的《钦定篆文六经四书》《古喷鼻香斋鉴赏袖珍丛书》皆包含《孟子》。清代统治者还将经典书本翻译成少数民族笔墨。康熙间玉树堂、天绘阁两种坊刻《新刻满汉文四书》,是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满文白文本《孟子》。乾隆天子还敕令重新厘定满文《四书》编成《御制翻译四书》,之后噶勒桑又将之译成蒙文,今有满汉合璧本、蒙汉合璧本、满蒙汉合璧本等存世。其余,石经也是《孟子》白文流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开成石经”刻于唐文宗朝,原未收入《孟子》,至清康熙三年(1664)补齐。后蜀“广政石经”亦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增入《孟子》,这是唯一一部附注文的石经。而北宋“嘉祐石经”的《孟子》部分也直到元初才被弥补[3],今仅存少量残石。有别于前三部石经的后补形式,南宋、清代石经的《孟子》皆为原生文本,特殊是刻于绍兴年间的“南宋石经”,当为现存最早的白文《孟子》,有85石幸存(《孟子》10石)。
b原有九经,包含《孟子》一卷,其《春秋左氏传》部分今已佚。近人傅增湘依据书中宋讳字的缺笔情形,断定其为宋宁宗以前的刻本,可拜会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
第二,经注本。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完全注本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别号《孟子赵注》)c。《孟子章句》版本实际可考者要下移至赵宋一代,清廷内府旧藏宋椠大字本,该本虽已失落传,但民国初年曾被上海涵芬楼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此外,明崇祯十二年(1639)永怀堂刻印的《十三经古注》亦包含《孟子赵注》。清乾隆年间,又相继涌现了孔继涵微波榭本、韩岱云本两种刻本。南宋往后,经典书本开始以释文附入经注本,产生了经注附释文本。咸淳年间廖莹中的世彩堂刊印《九经》,其《孟子》采取赵岐注与孙奭音,但廖本早已不传。入元往后,“盱郡重刊廖氏善本”为元盱郡覆宋本。民国时,北平故宫博物院又将覆宋本影印,收入《天禄琳琅丛书》。此外,元人岳浚还以世彩堂本为底本,刊刻了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
c 西汉刘向、扬雄都曾被认为著有《孟子注》,因干系证据不敷,实难断言。东汉时呈现出一批注释《孟子》的书本,除《孟子赵注》外,还有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刘熙《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等,但皆已散佚,现下仅能通过清人辑佚本窥见部分片段。
第三,注疏本。旧题北宋孙奭所疏《孟子注讲明经》(亦名《孟子注疏》《孟子正义》)是首部讲明《孟子》之作d,南宋浙刻八行本为所知的最早版本,当出自两浙东路茶盐司或绍兴府,刊刻于宋宁宗嘉泰至开禧间[4]。此外,南宋建阳书坊还刊刻了另一种附《经典释文》的十行注疏合刻本(《孟子》无释文)。现存最早的十行本刊刻于元泰定间,后经明代多次补版,当翻刻自宋本。明、清两代又衍生出多种包含《孟子注讲明经》的《十三经注疏》汇刊本,个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确当属清嘉庆二十年(1815)阮元主持刊刻的南昌府学本。清代焦循重新讲明赵岐《孟子章句》完成《孟子正义》,开辟了一套全新的注疏系统,有《焦氏丛书》《皇清经解》《焦氏遗书》《四部备要》和《诸子集成》等多种丛书本传世。
d《孟子注讲明经》托名孙奭的说法最早出自朱熹,他认为该书出自宋代邵武军某位读书人之手。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阮元《十三经注疏》等持相同见地,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对此亦有考证。可拜会俞林波.《孟子注疏》作者考论.文学遗产,2011(6):132–134。
第四,集注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是表明《孟子》的经典之作,成为有宋以降封建科考长期的法定教科书。当涂郡斋本是仅存的宋本,初刻于嘉定十年(1217),后经嘉熙、淳祐年间多次递修。元刻本方面,也有至正二十二年(1362)武林沈氏尚德堂刻本等三种留存。传世的明、清本多达数十种,尤以清康熙内府影刻元泳泽书院本e最为精美。
e该本《大学章句》序后跋文题“置诸泳泽书院,嘉与学者共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识”,曾一度被公认为宋淳祐刻本。近人陶湘创造“学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写的痕迹,又考泳泽书院始建于元代,故定其为元刻本。拜会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善本书影初编》.北京:故宫博物院,1929:4。
第五,音义本。宋人孙奭的《孟子音义》是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孟子》音义本f。该书在宋代官私书目中多有著录,但目前所知的皆为清代版本。国家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清初影宋抄本,前者原为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后者出自虞山毛氏汲古阁。《通志堂经解》本是《孟子音义》在清代的首部刻本,初刊于康熙年间。此外,还有《士礼居黄氏丛书》《微波榭丛书》《抱经堂丛书》《粤雅堂丛书》《四库全书》等丛书本,以及韩岱云刻本、许印林刻本等单行本留存。除孙奭《孟子音义》外,元广阳罗氏刻《魁今年夜字详音句读孟子》也颇具特色,该本在句读的根本上,增加了部分朱熹音注。
f 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周易》等14部儒家文籍的古音进行考证,并兼及训义,但未包含《孟子》。终唐一代,仅有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两部音义作品,但皆已失落传。
第六,节文本。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人重修《孟子》,删去个中“辞气之间抑扬过分”[5]与“非臣子所宜言”[6]等八十余条,编成《孟子节文》,作为科考教材颁行。不过,至永乐九年(1411),通畅仅十余载的《孟子节文》就被下诏破除。现存《孟子节文》皆为明初刻本:一为洪武年间内府刊本,仅载经文;二为双行夹注本,注释取自朱熹《孟子集注》;三为经厂本残页,仅存《告子章句》等。
2 “斯人”还是“是人”?
《孟子》诸版本中,白文本、经注本、注疏本、集注本最早皆可追溯至宋朝,究其缘由,除了得益于雕版印刷术在两宋的全面遍及外,也与孟子的地位在宋代得到极大抬升有直接关系。早在唐中期就兴起了“孟子升格运动”,但终唐一世奏效甚微,其系列本色性举措都发生在宋代:王安石变法规定《孟子》为“兼经”,将其指定为应举士子的必读书籍之一;元丰年间神宗为孟子首次封爵,并许之配享孔庙;徽宗时《孟子》被补刻增入“广政石经”,正式完成了由“子”升“经”的重大转变。而《孟子》的节文本和音义本,现存版本最早也仅能上溯至明、清两代。各版本对“斯人”与“是人”的记载究竟如何?笔者根据查考的结果,制成表1。
表1 《孟子》诸版本异文情形
①前文为阐述方便,在“白文本”一节先容《广政石经》,同时也指出其首创了石经“经注并刻”的体例。《广政石经》的《孟子》部分虽是宋代后补且今已不存,但从保持石经文本同等性的角度来推断,《孟子》亦当刊列有注文,故将其并入此表“经注本”之列。
以上列举的各种不同版本《孟子》,《嘉祐石经》和《广政石经》因实物的缺失落而无从查证,《孟子音义》则由于仅摘录音注关涉字词而未收录全文,很不凑巧地避开了关键词句,别的诸本均无一例外地记作“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就这些版本的镌刻主体而言,官刻、家刻和坊刻皆有之;就书本的性子和用场来看,既有研治经学的名家著作,又有做事科考的举子教材,因而具备相称广泛的代表性,进而也间接打消了两千余年间可能潜在的因传抄或刊刻轻忽而造成讹误的极个别版本。因此,已经基本能确定赵宋以降的《孟子》正文皆作“是人”。
既如此,“斯人”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通过检索古籍数据库,笔者创造了多少线索。宋人刘达可《碧水群英待问会元》(明丽泽堂活字本)卷三十一《臣道门》有“诚以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出一处,一语一默,平生易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安危寄焉”之语;元人王恽《秋涧师长西席大全集》(《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卷三十九《克己斋记》有“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俾经纶一世之事”之言;明《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卷二千五百三十七《斋名十三》收录王恽所撰的斋记,亦写作“斯人”;清人李雨堂《万花楼演义》(清经纶堂刊本)卷一也有“正合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智,苦其筋骨’之意云耳”的记载。这些都是后世化用《孟子》原文的例子,不仅将“是人”写作“斯人”,还习气在“天”字后添一“之”字,乃至还颠倒了“劳”和“苦”两动词的位置。古代引文有“略其文而用其意”的特点,此类不规范的引用,加上民国图书、报刊和当代文学影视作品的再次不当征引,对异生文本的快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浸染。
而回归到文句本身,“斯”和“是”在此处皆被用作近指代词,即“斯人”“是人”都可阐明为“这个人”或“这样的人”。也便是说,仅从意思表达、文意通畅的角度而论,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正误之分。由此看来,选用“斯”还是“是”,更多的应该是基于当时人们的语法习气。明确了以上情形,我们便可以此为打破口,寻求佐证“是人”文本合理性的其他证据。
笔者统计了南宋嘉定十年(1217)当涂郡斋刻嘉熙淳祐间递修本《孟子注疏》和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韩岱云刊本《孟子赵注》的文本情形。结果创造,撤除这次涌现争议的文句,“斯”在两版《孟子》里都涌现了50次,个中与“斯人”构造类似的用法,还有“斯民”“斯时”“斯心”“斯二者”等,但唯独不见“斯人”。而两版《孟子》之中,打消“天将降大任”一句,“是”共利用了256次。其余,《告子上》篇还包含两处“均是人也”的记载,但此处“是人”之“是”显然不是充当指示代词,而是作为连接主语和宾语的系词。不过,《孟子》中的确也存在“是国”“是君”“是民”“是路”“是门”“是心”等相称多的指代用例。因此,严格而论,《孟子》一书并没有涌现其他“斯人”或“是人”之实例,但若是从作为代词的利用频率来看,“是”多达235次,远高于“斯”的26次[7]。事实上,不仅是《孟子》,战国期间的其他文献也多习气以“是”为近指。以《墨子》《庄子》《荀子》等几部与《孟子》同处战国之际的文籍为例,“斯”的指代用法仅零散散见于诸书,而反不雅观同样作为近指代词的“是”,则可谓遍布各书,其用例数量远超“斯”百余倍g。倘若再进一步穷究,上述三部文籍中都没有涌现“斯人”的用法。以上各类情形皆表明:根据同期间普遍的文法习气,“天将降大任”的大概率是“是人”,而非“斯人”。
g《墨子》《庄子》《荀子》中,“斯”字分别涌现了1、3、6次,凡10次;“是”字分别被利用了505、382、844次,凡1731次。详参郭锡良.《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收入《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89。
3 对编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古诗文篇目的思考
古代文献去今久远,且绝大部分已泯没于岁月长河之中,幸存至今的经由历代反复传抄和翻刻,其内容涌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落真。正因如此,我们在编选古代诗文作品时,应尽可能地参考利用相对可靠的版本。绝不夸年夜地说,中小学语文教材是大多数人毕生打仗古诗文最直接的路子,留下的文化影象将会伴随国人终生。如何合理有效地完成古诗文篇目的版本甄别和审定,充分发挥语文教材的正面导向浸染,成了教材编写时必须负责思考的问题。
3.1梳理版本源流,重视最古版本
确定了教材古诗文的详细篇目,紧张事情便是对诗文来源的古籍文献进行版本梳理,以摸清各版本间的递传关系和流传情形,为后续的版本选择供应可靠依据。中小学语文教材所涉及的古诗文,多属先贤名家的经典之作,流传甚广,因而传世版本极多。如果作者的稿本或初刻初印本有幸存世,自然就不会涌现争议。但多数情形下,这些作品历经后世的辗转传抄和翻刻,传世版本每每互有利害。只有在广泛包罗、梳析源流、比较异同的根本上,才能在诸多版本中择善而从。其余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些传世名作向来就备受学界关注,因此累积了颇为丰富的干系研究成果,个中就有很多对作品成书过程及版本情形的稽核,这也为我们节制古诗文作品来源古籍的版本情形供应了一条便捷有效的路子。
一样平常而言,古籍的版本越古老就越靠近于祖本,这是由于传播的环节越少,出错的几率就越小,可信程度自然也更高。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小学教材选用的古诗文,有相称一部分属于“集部”。集部文献又有总集、别集之分,从成书规律看,总集的编纂常日以多部别集为依据,故而总集的完成每每晚于别集,因此在选用古诗文时要更重视别集,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详细到某部作品来说,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国家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珍藏的两部宋刻《李太白文集》,末句皆作“随君直到夜郎西”,但元至大三年(1310)勤有堂所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则为“随风直到夜郎西”,明、清两代刻本也多为“随风”。虽然有学者从诗歌意境角度比较过“随君”与“随风”的差异[8],二者皆说得通,并无绝对利害之别。但从版本学的角度考虑,由于“随君”产生更早,同时又与诗歌创作年代较靠近,因而更加可靠。前文提及的《静夜思》,今存宋刻本《李太白文集》《乐府诗集》皆作“床前看月光”和“昂首望山月”,其笔墨的改动可追溯到明代,个中尤以《石仓历代诗选》和《古今诗删》中“床前明月光”与“昂首望明月”的影响最大,清人编《唐诗三百首》时将上述两种异文同时接管,才出身了如今广为人知的千古名句[9],但已非李白笔下原文,选用宋刻本的说法实际更为稳妥。至于周敦颐《爱莲说》的“众人甚爱牡丹”和“众人盛爱牡丹”两种文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吴郡周与爵刻《宋濂溪周元公师长西席集》、四库全书本《周元公集》等皆为“甚爱”,而宋刻《元公周师长西席濂溪集》记作“盛爱”,“甚”与“盛”的差别更是微乎其微,但联系到周敦颐的宋人身份,“盛爱”之说显然更能站得住脚。
3.2充分利用影本,参考当代整理本
所谓“影本”,包括“影抄”“影刻”“影印”三种形式。“影抄”又称“影写”,其起源或与书法艺术有关,“影刻”亦名“覆刻”“影刊”等,明代中期刻书业盛行慕宋之风,由此呈现了一批雕印精良的影宋刻本,即为目前所存较早的影刻本实物,清代至民国,影刻古书之风仍旧兴盛不衰。影印之法系清末自欧美传入,光绪五年(1879)上海点石斋的古籍出版即为海内最早运用之例。时至今日,影印仍是古籍出版的主要办法,合营日益精进的信息技能以及运作成熟的当代出版体系,古籍影印的成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质的跃升。
较之影抄、影刻等原始的书本生产形式,古籍影印由于引进了摄影、扫描等新兴技能,除了据原书尺寸版式印刷外,还能灵巧地缩印、拼页。可无论怎么说,只管影本的生产办法不断发生迭代,力争最大程度再现古籍旧貌始终是其颠扑不破的主题。当然,影本的文物代价、艺术代价自是无法与原来比较,但仅从学术代价来看,正是由于影本保留了旧本的原貌,就能够为古诗文版本的选择供应主要的参考。不过还要指出,部分影本古籍的确存在随意编削添补且不附解释的情形,影响了文本内容的可信度,因此应该谨严地加以甄别,尽可能地选择高质量、争议少的影本。
经专家点校、注释的整理本,一方面通过梳理版本源流精选了底本,另一方面参照其他版本对底本进行订正,因而内容质量是最高的。不仅如此,就上手翻阅的难易程度来说,较之传统古籍较高的阅读门槛,古籍整理本显然也更符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气。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奇迹起步于解放之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成立了古籍方案小组,古籍整理出版事情开始全面展开,虽然六七十年代受“左”的思潮的冲击而短停息止,但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心印发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又重新推动古籍整理奇迹迈入繁荣期间,前后七十余载光景,大批精良古籍整理本相继问世。从语文教材编选古诗文的角度来看,别集方面,如李杜之作可参看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公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总集方面,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高质量的整理本。至于历代正史、先秦诸子之作,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含最新修订本)和《新编诸子集成》皆属业界较为认可的整理本。与传统古籍类似,当代整理本实在也很难有一部真正做到尽善尽美,多方参照比拟仍是最可靠的处理办法。其余,大部分规范的校本都会在页下或文末注释中标明异文的版本来源,这又为古诗文版本的循证供应了便利。
3.3避免轻信引文,务必回溯原文
征引文献是古人写作时常用的方法。不过,由于古代长期缺少严格的引文规范,引文时多依据个人喜好或凭借影象,却不负责核检原书,导致引文每每只用其意,并不强求与原句同等,明人方以智所谓“古人称引,略得其概,则以意摛辞”[10]便是指此而言。
《孟子·告子下》的“斯人”之说即是不规范引用的范例。文前提及的《泊船瓜洲》与之一模一样,《临川师长西席文集》《王荆文公诗笺注》等诗文集皆作“自绿”。“又绿”之说实际出自《容斋续笔》《茶喷鼻香室丛钞》《锦绣万花谷》《舆地纪胜》之类的条记、类书、地理志等其他文献的征引,因而应该选用前者作为教材编写的依据。部编版高一语文必修上册教材选用的韩愈《师说》也是一个范例的古文引用案例。韩愈《师说》有“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记述,即通过援引孔子之论来佐证“以能者为师”的不雅观点。而实际上,韩愈取用的贤人箴言源自《论语·述而》,原文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仅就“三人行”一句来说,《论语》毫无疑问是绝对威信的文本,《师说》只是诸多引文的一个代表。但也必须指出,异生文本的确已成为《师说》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既不可因韩愈的自行变更,而强行将干系文本按照《论语》的记载还原,更不能受《师说》引文的滋扰,旁边对《论语》原文的精确把握。
不规范的引用习气注定会造成引文不愿定性的增加,进一步匆匆成原生文本的变异,而异生文本的广泛散布,又将不断挤占原生文本的传播通路,乃至可能粉饰文句的本来面貌,固化为人们的普遍影象。正因如此,在敲定古诗文篇目之前,必须摒弃大脑中的既有文本印象,而去反复核检原书,严格遵照原文的记载。
3.4标注版本及异文信息,遍及文献学知识
语文教材选录古诗文,实质上属于对古人作品较大规模的直接引用。既然是文本引用,标注选文的版本来源天经地义应成为一种基本的学术规范。详尽的版本解释,不但可以作为师生溯源回查的直接依据,还能给学生群体供应课外阅读的方向指引。从理论上来说,为了充分担保语文教材的严谨性,可通过详细表明古诗文选篇的异文信息,反响不同版本中笔墨差异的详细情形,培养师生的文献素养。然而,教材的编辑出版究竟还是要以实际的适用场景作为依据,处在中小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认知水平有限,日常的课业包袱也相称繁重,为避免教材内容过于繁琐而影响到正常的课程节奏,仅展示具有范例意义的异文更契合现实的传授教化情形。此外,除了采取页下或文末注释等办法标注异文信息,适当在干系篇目内设置思考题,勾引学生亲自体会不同版本的笔墨差异,加深对异文观点的理解,这也是教材编写的一种灵巧思路。
异文是古籍文献流传过程中伴随版本更迭累积而涌现的一种正常文化征象,常日情形下,版本数量越丰富,异文情形相应也就越繁芜。整体而言,异文实在不外乎两种类型:其一为显而易见的讹误,字词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句子的正常构成,或导致文句涌现逻辑性毛病;其二是模棱两可的差异,笔墨的出入并不会造成明显差错,乃至都能够自作掩饰,这也是引发诸如“斯人”与“是人”等诸多异文之争的根源。明确了上述事实,若要再进一步穷究的话,除非直接节制作者亲笔稿本等关键证据,否则选用任何版本都无法完备担保文本的绝对精准,尤其是对付某些年代久远且版本链条不甚明晰的古籍来说,文本的取舍并非一锤定音,而只是多重考证往后的谨严决议。基于此,语文教材实在不宜过度渲染异文的绝对正误观点,以免对学生造成古籍文本非黑即白的误导,可通过设置拓展知识专栏的形式,依据学生不同年事阶段的特点,逐步遍及文献学的基本知识,通报理性的版本不雅观念。
4 结语
以《孟子》“斯人”与“是人”为代表的古诗文的异文之争,其背后固然有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对古诗文版本审定欠精密的缘故原由,反响出当前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短缺一个必要的环节,即对古诗文篇目来源的古代文献的版本源流进行系统梳理、稽核和甄别,并作必要的题讲授明;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部分网友偏狭地认为,只有自己小时候用过的语文教材才是最好的,之后新出版的各种教材都是低劣、缺点的,乃至极个别人有疑惑语文教材遭受恶意修改的过激辞吐。这一方面解释童年期间植入的“文化影象”是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的,但另一方面也反响出国民古籍版本意识的普遍性缺失落。中小学语文教材在每一个中国民气中的分量不言而喻。一套精良的语文教材造就一代新人的发展,不仅要使其领略汉措辞文学之美,也将为其深深烙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网民自发的古诗文异文之争提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古诗文篇目的编选不仅要考虑其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还应充分屈服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演化规律,向国民遍及古文献的版本知识。
向上滑动阅览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43.
[2] 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普通化——以近古时期的传刻为中央[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12–120.
[3] 顾永新.关于嘉祐石经的几个问题[M]//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央.儒家文籍与思想研究: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3–117.
[4] 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32–334.
[5] 刘三吾,等.孟子节文[M]//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956.
[6]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982.
[7] 郭锡良.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M]//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9.
[8] 路德奎“.随风直到夜郎西”,还是“随君直到夜郎西”?[J].语文月刊,2017(7):61.
[9] 森濑寿三.关于李白《静夜思》[M]//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西北大学中文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唐代文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48–253.
[10] 方以智.通雅·卷首[M].北京:中国书店,1990:25.
(原文揭橥于《图书馆杂志》2024年第6期)
作 者 简 介 李明杰,江西丰城人,管理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索引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智能开拓与利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图书馆学卷“文献学与文献保护”分支副主编、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打算实验室研究员、武汉大学古籍保护暨文献修复研究中央研究员。主持教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著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揭橥论文近百篇。紧张研究领域:文献整理与保护、中国图书文化史。 任务编辑:朱田子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年夜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容许,请勿利用。 欢迎互助、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