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李白的偶像很多,春秋的鲁仲连,前朝谢安等等都是,在当时来说,他最崇拜的人,则当之无愧是大他20岁的孟浩然。
孟浩然这个人,也是一个挺可爱的人。他和李白一样,面临着从政与隐居两个方向的迷茫,这个迷茫是伴随了他生平的。
不过在李白看来,孟浩然一贯在隐居,恬淡且激情亲切,大概便是真的放下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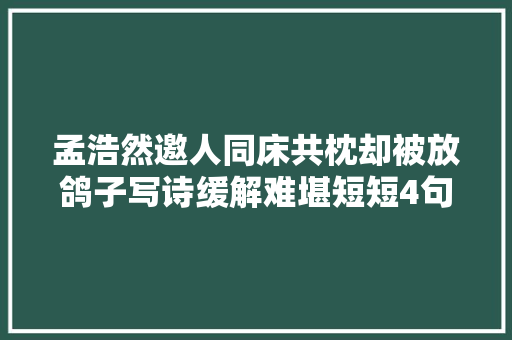
但孟浩然放下了吗?
肯定没有,真正放下的人在隐居生活中是不会留下什么字句的,过着自己空想中的生活,并没有什么须要表达的东西了。
像陶渊明,像辛弃疾,像陆游,他们隐居的时候留下的诗篇最多,为什么?
由于生活并不称心快意。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孟浩然诗中那种恬淡自然是很吸引人的,所往后众人才乐意把他和王维放在一起,成为盛唐山水田园派的两大墨客。
本日来看他很负盛名的一首诗。
【诗篇】
【临境】
这首诗歌的背景在题目中交代得很清楚。
孟浩然住在僧人业师的山房中,僧人之房,也便是山中小庙了。唐代僧人多有才华,喜好与文人交往,更出了不少著名的诗僧。孟浩然借宿僧房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一天晚上,孟浩然兴起,约自己的朋友丁大过来共宿,两个男人共宿,听起来有些奇奇怪怪的,但在古代实在也并不少见,现在的针言“抵足而眠”便是描述这种情形。
新友初见或者老友相逢,每每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自然就须要秉烛夜谈了。
丁大,大是此人家中排辈,丁大是家中宗子,李白被叫作李十二,也是同理。不过我们这一辈人,一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很少有排到十二、三十六的。
本来该当是宾主尽欢的一晚上,变故就出在诗题的末了两字:不至。
丁大答应得好好的,竟然没有来。
孟浩然被人放鸽子了。
我们来看孟浩然在这种情形下是怎么反应的。
【诵析】
诗的节奏很慢,为什么这么说。由于诗歌一共四联,前三联谈论的全部是自己看到的内容,一贯到第四联才点题。
夕阳西下,逐步从天边一片火彤霞光黯淡下去,末了消散在西山微茫的烟雾之中。
了望重山众壑,在晴日里分外清晰的轮廓也随着黯淡下去,换成模糊的一团绿,一团灰。
“倏已暝”,在孟浩然眼中,夕阳落山,群壑黯然的转变是很快的。这一点与常理相违,通过我们的日常履历,当你在等待某个你所期待的人或事物时,韶光该当是漫长而煎熬的,孟浩然这里为什么还会用倏还表现韶光流逝之快呢?
我们暂且留一个小悬念,读完全首诗你自然就理解了。
第二联写到了玉轮与泉水。松间有月光洒下,清清冷冷的,带着夜的寒气。风从清冽的泉水上吹过,带来寒凉的水气与风声,很有些“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无怪乎与王维并举。
第三联中,终于有了人的涌现。那些白天上山砍柴的樵人现在也循着山间小路回家了,活泼的鸟儿借着明月的微微光亮寻得自己巢穴,扑棱棱一声钻进去。随着太阳的落山,统统都变得安静、安谧。
这里樵人与烟鸟的涌现,实际是为了以动趁静,三联下来,孟浩然营造出一个黯淡、清冷、宁静的山中夜色图。
那孟浩然此时心境如何呢?
等着丁大按照约定的韶光来共宿,自己带着一把古琴横坐在庙门口的小路上,等着他。
这两句话写得很有风姿,他不像赵师秀“有约不来过夜半”诗中暗含着些许讽刺与不满,孟浩然给人的觉得是一位真正的高士。
朋友没来,便出门去等,一起上沉醉在山中风景中,感想熏染着大自然的呼吸,没有丝毫担忧或者疑虑。
你来或者不来,我的兴致不会受丝毫影响。
当然,丁大一定会来。
由于孟浩然的这份信赖。
【尾言】
我以为,唯有一个内心圆满的人,才能做到如此不带感情去面对世间统统不顺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孟浩然在生命的后半程,真的放弃了仕途空想。真的犹如诗中所说“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
李白所仰慕孟浩然的,也便是这一片恬淡。他当然是做不到的,李白的生命活力太过于充足,临去世前尚且想要从军报国,哪能够真的放下统统,终老山林呢?
这是幸运,也是不幸。
在现在这个时期,做个孟浩然一样的人,生活压力会小很多。但我甘心做李白,至少,这生平有个奔头。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会立即删除!
你的关注与评论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