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诗歌的创作,到了唐代无疑达到了文学艺术的顶峰。
唐诗就其产生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它所涉及的墨客群体,以及创作韶光之持久来剖析,不难创造其流派中,众所周知的有“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以及“咏侠诗派”。从分类研究看,学术界对山水田园诗,边塞诗研积丰硕,而面对唐代社会“任侠风尚”中的咏侠诗潮及其咏侠诗派却无多关注,笼统地将其混迹于边塞诗之中,这彷佛有些没有道理。纵不雅观唐代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从社会风尚与文学流派的关系来看:如果说“隐逸风尚”,是“山水田园诗”的温床;看重“建功立业”和“文化互换”,是“战役边塞诗”的催化剂,那么唐代社会“任侠风尚”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它流淌于墨客们的热血之中,它的产生波及到初盛中晚的大唐帝国,以是产生了咏侠诗潮和咏侠诗派。哪个热血男儿没有侠骨柔肠?据史料不完备统计,在唐代墨客中,大约有150多位墨客,曾经留咏侠诗篇,他们共创作咏侠诗400余首。个中不乏一些响当当的名字——诸如“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王维,李白,杜甫,岑参,李颀,李益,王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贾岛,贯休,司空图……都曾经以饱满的激情亲切,积极创作过这类“咏侠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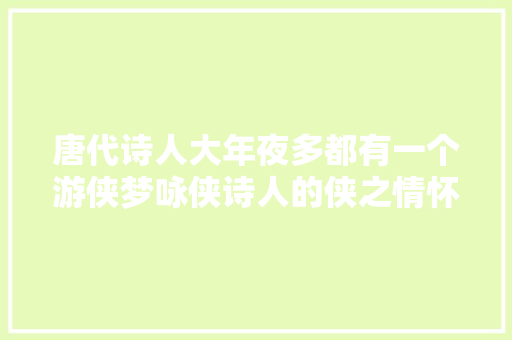
2.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去世难在横行。翠羽装剑鞘,黄金饰马缨。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卢照临《刘生》
3.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诗人。”——杨炯《从军行》
以上三首带走浓郁古风的“咏侠诗”便分别出自初唐墨客卢照临、杨炯手笔。个中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诗人”,可谓后世文人之模范,千古流传至今。
3. 除此之外,“初唐墨客”陈子昂不但能“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而且还可以“平生闻高义,书剑百夫雄。言登青云去,非此白头翁。”(陈子昂《送别出塞》)。
纵览初唐期间,这类诗中歌咏的游侠形象多为“古游侠”。从风格看创作可分为两个期间,以“四杰”和陈子昂为标志。前期咏侠诗创作承魏晋六朝,多拟古拟意之作,后期逐渐转移到对现实任侠风尚的描写和自我胸臆的抒发,诗题逐步开始灵巧多样,摆脱了拟古的形式。著名古诗词学者闻一多师长西席说:“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期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盛唐期间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高朋——康震在评论诗仙李白时曾经说过:在唐代每一个墨客多少都有一个“游侠梦”。盛唐期间,也是墨客们任侠风气的炽盛期,更是“咏侠诗”创作的繁荣期。
墨客歌咏游侠,实在是一种时期精神,是一种昂扬向上的人格力量,诗中行侠与赴国难,以报国恩,侠客与文人紧密结合,将其视为文人的终生崇奉,这一文化征象展现着极具特色的时期内容。
这一期间的咏侠诗创作,险些占了唐人咏侠诗的一半旁边。虽不能逐一颂咏那些随处颂扬的作品,让我记住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李白、王维、王昌龄、孟浩然、高适、岑参……他们都是时期的游侠儿,他们的咏侠诗创作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最强音。
诗仙李白无疑是“文人任侠”的精彩代表,也是唐代咏侠诗创作最多的一位。一首《侠客行》,杀气腾腾,霸气侧漏。
这时的“咏侠诗”紧张表现出两种创作方向:其一,是墨客将游侠置于天地间的分外空间——边塞、市井;将作品的主人公游侠意识与对国家、民族高度的任务感紧密结合;将游侠本身的青春豪迈,视为一种个人的民气抱负和精神追求,乃至将他们纵情随意率性的我行我素,视为一种激情燃烧的生命存在。
这种以游侠的形象和生命情调为表现中央的少年情怀,是盛唐咏侠诗的主体和代价所在,是“盛唐气候”的主要艺术表征之一。
李白《少年行•三首》,其一云:“ 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侠好过,浑身装扮服装皆绮罗。”;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一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昌龄《杂兴》云:“可悲燕丹事,终被虎狼灭。一举无两全,荆轲遂为血。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在盛唐墨客笔下,已更多地将侠衍变为一种侠义气质的追求,一种人生境界的神往,一种空想人格的崇拜。中晚唐期间“咏侠诗”进入中晚唐,由于受社会动荡和侠风衰变的影响,这时咏侠诗的创作表现出两大特色:
其一,极力表现游侠纵情行乐,这在中唐咏侠诗中最为光鲜;其二,是咏侠诗中对侠客的歌咏已表现出某种神秘幻化色彩,与现实生活渐远渐离;其三,特殊是晚唐,可以说是咏侠诗创作的衰落期,唐人的游侠梦随风而去,可以醒醒了。
孟郊《杂曲歌辞•游侠行》诗中“平生无恩酬,剑闲一百月”;贾岛《剑客》:“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吕岩《七言》:“雨雪霏霏天已暮,金钟满劝抚焦桐。诗吟席上未移刻,剑舞筵前疾似风。”;“背上匣中三尺剑,为天且示不平人”;“粗眉草竖语如雷,闻说不平便放杯。仗剑当空千里去,一更别我二更回。”虽然也是赞赏“侠义精神”,却散发着浓厚的神秘色彩,以及套话空言,早已分开了侠义精神的本色和内涵,将其留于形式,即便是“郊寒岛瘦”这样的大家,其咏侠诗作也落入“口号标语”,大而化之,空洞虚无。这大概也是“晚唐社会”现实的弯曲反响。@兵法天下 如是说(结束语)
总而言之,唐代“任侠风尚”的起始,贯穿着初、盛、中、晚的“咏侠”诗潮,从某些层面来说,不能说不是一部“唐诗”的发展简史。
每个期间以“侠”为题材,墨客们共同的创作方向,是文人通过对“任侠行为”及“侠义精神”的崇尚,已自觉地将其为一种抒怀况象,诗歌创作意象,从而抒发昂扬向上的时期氛围,建立功名的个人抱负,寄托自我深厚的忠义情结,以及宣泄怀才不遇的愤懑。
游侠或侠义之精神意象,积极地参与了文人的人格空想、生活空想、艺术审美空想的建构,任侠风气与文人在文学创作中也形成了多层面的联系。
而在此根本上的咏侠诗创作及表示出的任侠精神,就成为唐代咏侠诗派的主要标志和唐诗美学风格的组成部分。
唐代墨客及其咏侠诗创作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咏侠诗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温馨提示:兵法天下,诗词文化。爱崇原创,不忘初心。自古读书本难,行文不易;既然头条有缘,文笔相见。如果您认可“兵法天下”,敬请赞转分享,雅评留言】
大家好,我是@兵法天下 ,感谢你的悦读,共同分享唐诗中的“侠之情怀”,此文章纯属个人不雅观点。赠人玫瑰 ,手有余喷鼻香;奇文共欣赏,疑意相与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