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雪,仿佛我也有了那样的美。
我想写一首诗,却找不到词。我听见了音乐,C大调——
小时候每逢下雪,我们一群孩子满村落跑,叫喊:“下雪了!
下雪了!
”我们手舞足蹈,跑着捉雪,而后不知不觉,都停了下来,悄悄看雪。
昨天傍晚,在玛利恩广场,人们走在纷飞的雪中,就像电影里的场景。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仰着头,摇扭捏晃地,用眼睛接雪,用嘴巴吞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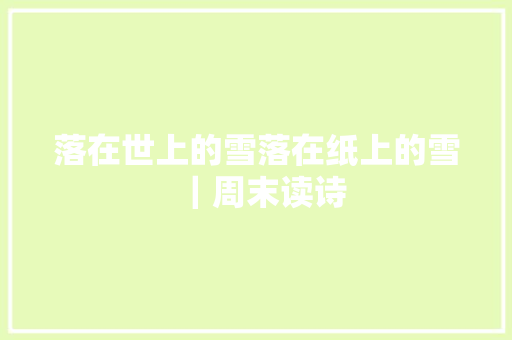
雪越飘越大。就让雪落在我身上,就让雪轻轻地,把我灼伤。
——《爱雪精确的爱法》
撰文 | 三书
01
飘在窗外的雪
《南歌子》
(五代)张泌
锦荐红鸂鶒,罗衣绣凤凰。
绮疏飘雪北风狂,
帘幕尽垂无事,郁金喷鼻香。
汉语是闻得见喷鼻香气的,不信你试试这首词,或任何一首花间词。
锦荐便是锦垫,锦锻的坐垫,绣着一对紫红鸳鸯。锦垫上坐着一位美人,大概她正侧身望着窗外,我们不见她的容颜,但见罗衣上绣着凤凰。何以知其为美人?以锦荐,以罗衣,以每个词散发出的喷鼻香气。
“绮疏飘雪北风狂”,绮疏即雕饰花纹的窗子,表面正飘着雪,北风狂吹。美人房中,一派静穆,“帘幕尽垂无事,郁金喷鼻香”。“尽垂”二字,有无限的寂寞,无限的幽思。
并非这时才寂寞,一开始就寂寞了。锦垫上的鸂鶒,罗衣上的凤凰,都已悄悄通报出寂寞,不过墨客在用明丽的色彩写哀愁罢了,与温庭筠的“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儒,双双金鹧鸪”,异曲同工。
郁金喷鼻香弥散开来,弥散在房中、词中、时空中。
唐宋诗词中的郁金喷鼻香,并非我们本日所知的花名,郁金是一种喷鼻香草,可以浸酒,可以焚喷鼻香。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喷鼻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说的便是郁金浸泡后的喷鼻香酒,上古敬拜亦用之。
如果你执取郁金喷鼻香为爱情之花,置之词中,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以为美,至于是否合乎墨客本意,又有多大关系呢。
那么词中的寂寞心情,是悦享呢,还是愁苦?不好断言。愁苦被不雅观照,被写成诗,就变成了美。人类的寂寞可分两种:一是不雅观之赏之的寂寞,可以很美;一是没有人陪的寂寞,寂寞而已。
窗外飘雪,家人闲坐,是我怀念的光阴。儿时家里是瓦房,木格窗糊着粉莲纸,一方一方的格子,贴着剪纸窗花,红红绿绿的喜气。尤其是过年,莉莉姨到我家来,她是舅爷抱养的女儿,生得很好看,牙齿又白又齐,粲然一笑,陋室生辉。午后,母亲、莉莉姨和我,坐在炕上打牌,雪光透过窗纸,映得炕头一片新白,莉莉姨和母亲都还年轻,情同亲姊妹,牌间闲话谈笑,声音轻似寂静。
后来,为什么故事都要有“后来”呢?莉莉姨每况愈下,一起落魄,我不忍说,就把这首《南歌子》赠与她吧。
北宋 燕肃(传)《寒岩积雪图》
02
雪初晴,听孤鸿
《忆王孙·冬词》
(宋)李重元
彤云风扫雪初晴,
天外孤鸿三两声,
独拥寒衾不忍听。
月笼明,窗外梅花瘦影横。
李重元,平生不详,大约于宋徽宗宣和前后在世,工词,传世词作仅《忆王孙》四阙,分别咏春、夏、秋、冬。春词最为众所熟知:“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销魂,杜宇声声不忍闻。欲薄暮,雨打梨花深闭门。”像一段经典的旋律,几个大略的和弦,唱出来就很好听。
诗坛、乐坛,有一鸣惊人而不朽的,也有激情亲切高产却速朽的。乾隆天子生平写了近四万首诗,名世佳作却没有一首,诗关别才,这是没办法的事。那首听说曾入选小学教材的《飞雪》,恰好也是写雪,不妨一并赏读:“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这也叫诗?如果不是末了一句,实在不敢阿谀为诗。大概只是戏作的口水诗,或纯属好事者的杜撰,都不必索证了。
且看李重元的成名作。全体南宋期间,词林对这四首《忆王孙》称扬备至,黄升的《花庵词选》与何士信《草堂诗余》均曾选入,并都注明作者是李重元。不知何故,到了清代,康熙期间编的《钦定词谱》却将四首词记在秦不雅观名下,后来更传是李甲。时隔数百年,不知清朝人有什么依据,南宋距李重元不远,该当更可信。无论如何,作者去世已久矣,他叫张三还是李四,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差异呢,主要的是传世的作品。
这首冬词从雪晴写起,境极孤寂。“彤云风扫雪初晴”,彤云便是红云,大约夕阳西下,天空中涌现了晚霞,北风呼呼地劲吹。不知你是否有过类似的履历,雨始霁,雪初晴,会有那么一个少焉,空缺而宁静,时空彷佛刚刚转场,舞台布景已切换,演员将出未出。那时,我们的听觉会很机警,各种声音非常清晰,亲切又使人有点心惊。
词入耳到的是“天外孤鸿三两声”。天外,不见得便是遥天之外,而是诗中人听雁声而觉得迢遥,彷佛瞥见孤鸿一点,消逝于地平线。孤鸿让他更觉孤单,也将他的心带往更远的地方,或许是天外的故乡。这句诗用孤鸿三两声,画出了辽远的空间,彤云消散,暮色向晚,一片雪后的严静。
不忍听而听,孤鸿哀鸣,使寒衾更冷。“月笼明,窗外梅花瘦影横”,寒夜漫漫,薄衾独拥,然而有温顺的月光,有梅花瘦影横在窗上。墨客大概都是这样,一边瞩目着美,一边行在地狱。
明 沈宣《江天暮雪图》
03
高树上的鸟巢
《醉花间》
(南唐)冯延巳
晴雪小园春未到,池边梅自早。
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
山川风景好,自古金陵道,
少年看却老。相逢莫厌醉金杯,
别离多,欢会少。
冬天最好看的,要数高树上的鸟巢。别的时令看不见,树叶落光了,鸟巢这时都显露出来,衔在高高的枝杈上。晴雪后,那些鸟巢更觉可亲,让人以为春天就快回来了。
南唐冯延巳在我们的文学史教材中略有提及,今人的把稳力多聚焦于南唐二主。在南唐开国之初,冯延巳因才华横溢,被南唐烈祖李昪任为秘书郎,并令与太子李璟交游,后被李璟任为宰相。陆游在《南唐书·冯延巳传》中,赞誉延巳工诗,虽贵且老不废,并引孙晟的话:“鸿笔藻丽,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 使政敌心折如此,才艺文章可想而知。
读《阳春集》,不得不惊叹延巳诚为词之大家,正如王国维师长西席的评价:“冯正中词虽不失落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不失落五代风格,示正中词的题材因循老例,亦多写闲情离恨、春愁秋悲。堂庑特大,指其境界阔大,纵然写柔情,笔力亦能扛鼎,字句也颇新鲜,比如“云雨已荒凉,江南春草长”,“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楼上春山寒四面,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
《醉花间》词里的韶光,该当是冬至前后,金陵的早梅已经开了。晴雪后,小园中尚无春的,池边的梅树,已经近水花先发。时节暗换,雪还是冬天的雪,梅已是春天的梅。都是白的,以故常常使人惊异,以为是雪,却是早梅,以为是梅,却仍旧是雪。
池边梅自早,人彷佛总是迟一步,彷佛永久没有准备好。
“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此二句历来多被名家圈点,确实写得好,叫人一读就爱上,过目不忘,窃以为比王维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散发到读者身上的能量频率更高。
鸟鹊将归巢,寒草亦复活,这个中存在着永恒。“山川风景好,自古金陵道”,自古以来,多少人走过金陵道,看着山川风景,看风景的人都去哪儿了?他们彷佛从未存在过,风景也彷佛是一个梦。
“少年看却老”,“看却”二字要紧。纵然我每天看着你,你也每天从我眼皮底下溜走;纵然执子之手,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失落之交臂。老,只是一瞬间的事。
“相逢莫厌醉金杯,别离多,欢会少”,及时行乐,珍惜在一起的光阴。冯延巳是一个很深情的人,词中常写酒阑人散独自盘桓,这几句强作宽解,不是超脱,是无可奈何。
超脱的是庄子。怎么才能留住一个人,不让岁月神偷夜半负之而走?庄子说,你该当放手,藏天下于天下,而使其无所遁。换以当代说法,便是我们始终相聚在大海。
末了,想起我的母亲,读到雪和梅,才又记起母亲叫“雪梅”。这是她念高中时给自己取的名字,后来印在身份证上,平时没有人叫,村落里都按辈分称呼或叫小名。想起这个名字,我也无法把它和母亲联系在一起,像是另一个人,一个年轻姑娘,梦想着上大学,那时她还不是我的母亲。有时不经意间,我瞥见雪梅从她身上闪现,接着又隐入生活的幕后。
撰文 | 三书
编辑 | 刘亚光
校正 |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