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在攀越一座高峰,前40年我们在上坡路上爬行,面向的是生活,憧憬着高峰上的景致,以追求幸福为目标;可是,当我们攀上峰顶后,便看到了峭壁下的去世亡,我们心坎不安地瞩目着深渊,齐心专心只想慢点滑向它,这时候人生的基调在于避免不幸。
为什么童年生活让人感到愉悦?
对付大部分人来说,童年的回顾每每是快乐的,这种愉悦感在成年之后就难以重现了。
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的不雅观看画展,那么童年期间就好比站在远处不雅观摩到一副模糊不清的画作,随着年事的增长,我们不断地走近它,画面变得清晰起来,美感也就萌生于心,这解释童年生活的基调在于认识。
童年期间,外界事物对付我们来说都是新奇而鲜活的,我们渴望认识和理解它们,以是孩子们的眼神里总是充满着直不雅观和负责。这期间,认识活动在民气中霸占了主导地位,意欲尚未完备萌发。孩童们对这个天下理解得太少,只假如一点知足就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乐趣,就像饥饿的人吃到了第一口食品一样——这便是为什么童年光阴总是那么愉悦的缘故原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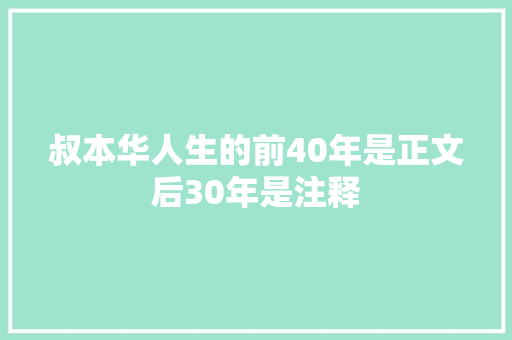
同时,童年期间智力尚未发达,对生活的认识也仅仅勾留在表象阶段,儿童更多还是通过动漫、电视剧、小说等虚拟的材料来认识生活,而不是基于自身的体验。这些虚拟材料每每会把生活给空想化乃至玄幻化,天下在他们的面前宛如宁静的伊甸园,而未来也大有可期。因此,在教诲方面,我们应只管即便勾引他们走向求真务实,避免过分的耽于抱负,要让他们树立自己的志向。
孔子说“十有五志于学”,童年和少年的乐趣就在“学”之中。
青年时期的烦恼人活到了青年期间,才真正步入喧嚷、骚动的人生,逐渐看清画像的真容,同时也创造身边拥挤着许多围不雅观者,大家评头论足,不雅观念不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
生存意欲也是在这时候才超越认识活动,童年期间我们只想看清生活这幅俏丽的花卷,青年时期,我们却萌生了霸占它的动机。可是画卷毕竟只是画卷,虽然看上去很美,却不能吃也不能穿——荒谬也就由此而生,我们所想得到的居然是虚幻的东西。
青年们梦想着模糊不清的幸福,齐心专心只望超越鉴戒线去霸占那副无用的画作。这种虚幻的意欲导致他们对生活感到不满,他们渴望解脱束缚,游离于规则之外,希望过上小说和诗歌里描述的生活,把真实人生的空虚与可怜归咎于自己的生存环境,烦恼就是以而生。
年轻人总以为生活是轰轰烈烈、丰富多彩的,纵然他们整天在呆板与无聊中度日,仍是乐此不疲。他们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登上人生的顶峰,因而昼夜攀爬,把所有的光阴都抛掷在对意欲的追求之上,可惜他们不知道去世亡就在对岸瞩目着自己。
青年时期大抵是人受生存意欲作弄的期间,它表现为“对幸福苦苦追求而又无法知足”。年轻人并烦懑活,他们感想熏染到更多的是痛楚与空虚,显得敏感而忧郁。他们用奋斗与逐求挤压了安宁和平和,不知道安宁乃是快乐的条件,以是显得躁动不安,愁绪满怀。
少年维特的烦恼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认清生活当我们冲破鉴戒线,奔向那幅生活之画卷,并把它捧在手心时,统统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原来这是一幅无用的刺绣画。近间隔地不雅观察生活之画,让我们看到了上面粗糙的线条与肮脏的涂料,美感也就随之消散。这种幻灭会使少部分人因对生活的失落望而选择自尽,也让一些人复苏了过来。
当然,更多的人则无缘触摸到那副画卷,他们或是被拥挤的人群淹没,或是因头酸脚麻而选择退出,或是在远处张望而感叹——大部分人终极都会找到自己的本分之所在,放弃对虚幻目标的逐求,他们不再与人争抢地盘,而是渴望立稳脚跟,追求稳定的生活。青年时期,他们觉得自己被众人抛弃,现在他们渴望逃离众人。
成熟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核阅人生,他们从生活的履历中学会用朴素的眼力来看待事物,抛弃青少年时期各种奇特古怪的动机。原来生活中并不是充满着唾手可得的幸福,也不是由于我们苦于道路才找不到它;相反,生活本身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只要能免于痛楚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过去我们总是渴望幸福来拍门,现在我们恐怕不幸会率先来拜访。只要没有什么事情打扰到我们,毁坏沉着,日子过得安安稳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惬意呢?
当我们领悟到生活的平淡,并心安理得地咀嚼、品尝着那得过且过的现状,乃至能够从平淡中找出乐趣时,也就能摆脱生存意欲的捉弄,放弃逐求,认清生活,“四十不惑”了。
中年使人走出了烦恼,当我们活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人生的正文部分就已经结束了。由于我们已经认清了生活,并且接管了它,给出了却论。我们翻过手中的刺绣画,虽然它的背面没有色彩,不像正面那么俏丽,却能给予我们教益,由于它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生活的线条。
中年的叔本华离开大学,度过了末了隐居的27年
老年也可以是丰收的时令如果把人生后30年称为老年的话,实在它所占的篇幅非常之大,但是在每个老年人看来,却显得很短暂。老年光阴意味着人在一步一步地滑向去世亡的深渊,我们的生命力开始消退,对生活的勇气也逐渐减弱,就连回顾也总是面向年轻的时候,而不是年迈的期间。
从中年起,人生已经步入了平淡无奇的轨道,老年则是这一轨道的加长版。文学艺术不以老年人为主角,电视剧也不反响老年人的生活,由于它们实在寡淡无味。某些人在青年时期招人喜好,中年时期受人敬仰,老年期间却每每变得一无是处,被人遗忘——不过有一些人是例外,那便是思想家。
思想家就像美酒,年纪越大反而越睿智,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没有受人嫌弃,而是被人敬仰。古希腊人把四五十岁称为“壮盛年”,哲学家们的“壮盛年”则更延后。北宋五子里只有程颐活过了七十岁,朱熹说:“伊川(程颐)晚年笔墨,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歌德也是直到晚年期间才完成了自己最好的作品《浮士德》。
青年人用直不雅观的方法来面对生活,老年人则把思想放在了紧张位置。直不雅观在于接管事物的印象,积聚它们的数量,思想则把它们升华成了观点。年迈意味着精力衰退,我们不再有精力去捕获事物、网络素材,却具备了反思这些素材的空隙。老年人通过对毕生积累的感性材料进行反思、比拟,创造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和连接点。就彷佛拼图游戏一样,青年人把散布在各处的碎片网络回来,老年人则把它们拼接在了一起。
因此,在人生的上半段,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总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我们仅仅是从量的角度上去感想熏染它,彷佛可以有无穷无尽的韶光可以尽情挥霍。到了老年,我们才能对生活得到一个完全的、连贯的认识,从表象深入到了实质,能够全面认清生活的真面孔乃是痛楚和无聊,不再断念塌地,缺点地认为事情迟早总会变得完美。有思想的老年人拥有着更强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对事物根本性的认识,真正地达到了“知定命”之境界,把老年作为人生的注释是恰当的。
叔本华说:“我们创造一个伟大的小说作家,常日要到50岁才能创作出他的鸿篇巨制。”平庸的作家则只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创作期全在青年时期,作品在实质上也只是把自己网络到的素材呈现给读者,而不含有对这些素材深刻的认识,缺少聪慧。他们一过中年,就立即枯竭。如果青年时期肯研究哲学,那么老年对付人来说,是认识人生实质的最佳阶段。因此,西塞罗说:
“我所赞颂的只是那种年轻时期已经打好根本的老年。”
西塞罗《论老年》
精神的安宁是人生之归宿叔本华说:“只有当一个人老了,亦即在他生活了足够长的韶光往后,他才会认识到生活是多么的短暂。”
老年时期,我们开始回顾自己的生平,在回顾的过程中,我们的影象首先把最不愉快的事情剔除掉,其次又把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撤除,末了只剩下美好的回顾以及印象深刻的事情。但是,人生的大部分韶光都是平淡无奇的,如果我们把它们筛选掉,可供回顾的素材就越来越少,以是我们才会发觉人生是那么的短暂。
正由于我们在老年时期领悟了人生的实质,才能认清事物的客不雅观面孔,看到了尘世的微小与虚无。不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受制于生存意欲,贪恐怕去世,寻求刺激。当我们解脱生存意欲的锁链之后,精神便得到了安宁,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安宁是构成幸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幸福的条件条件和实质。邵雍早就领悟了这个道理,以是他把自己的居室取名叫“安乐窝”。
青年人的前景是生活,老年人的前景却是去世亡,前者让民气忧,后者令人胆寒,而唯有精神上的安宁,才能够将它们战胜。在达不雅观者看来,生活乃是充斥着痛楚和无聊的劳役,去世亡则是无梦的就寝,是人生的安歇。以是庄子才说: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去世,故善吾生者,乃以是善吾去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