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因“灞水”而生。作为长安八水之一,“灞水”原名“滋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春秋期间,秦穆公称霸西戎,灞河“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自此,长安城东逐渐形成“灞”字文化,不但有了“灞桥”,还有了“灞城”、“灞上”、“灞陵”、“灞头”,而以“灞桥”为中央的诗歌意象,也开始走进中国古诗词,汉末文人王粲《七哀诗》,已经有句:“南登霸陵岸,回顾望长安。”身逢浊世,初离长安的墨客,踏上灞桥,频频回顾之中,已定下恨别千年的基调。
“灞桥”走进古诗词1.灞桥之于伤别。
灞桥、灞柳与灞河,从来十全十美,不可分开。没有灞河,桥、柳无从谈起。没有灞桥,如何容身送别?而没有灞柳,灞河、灞桥又何其萧索寂寞?没有灞柳,灞桥的别离之韵也不会如此缠绵悱恻。柳者,留也。“灞桥折柳送别”也不是唐代才有。至迟在汉代,已经形成折柳送别的习俗。地理名著《三辅黄图》云:“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到了唐代,灞桥折柳送别之际,还有了习气性的赋诗。
直接以“灞桥”为意象的伤别。如岑参有句:“初程莫早发,且宿灞桥头。”拳拳挽留之意。宋人黄庚的《析柳》:“阳关一曲灞桥春,垂绿阴中别恨新。漫折青丝千万缕,多应绊不住行人。”比较之下,北宋宰相寇准的《长安春日》,统写别意,十分蕴藉:“淡淡秦云薄似罗,灞桥杨柳拂烟波。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愁春一倍多。”名为愁春,实写人间离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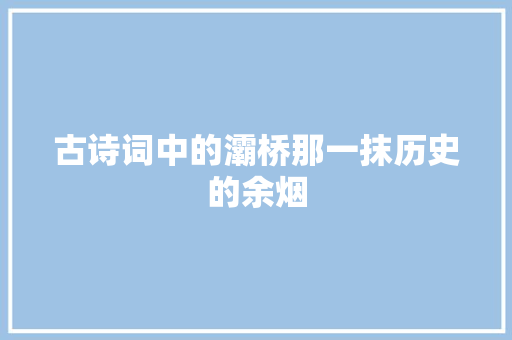
大文人柳永的《少年游》,则是一首标准的灞桥离去之作:“参差烟树灞陵桥,景致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干瘪楚宫腰。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词人以“灞桥”开始,连同“夕阳、”“阳关”、“古柳”、“蘅皋”诸多意象,深深地抒发了孤漂羁旅的愁怀。当然,也饱含着人生失落意的苦闷。帝都长安,谁不念繁华?到底是呆不下去了。别恨之中,自有空想的落差。
元人马致远编《汉宫秋》杂剧,写到汉元帝送别王昭君,唱道:“尚兀自渭城衰柳助悲惨,共那灞桥流水添愁怅。偏您不断肠,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真是演绎得声泪俱下。明人徐复祚《红梨记·再错》也说:“看他迎风袭袭,笼烟袅袅,肠断灞桥滨。” 便是到了清末的秋瑾,一篇《赋柳》,灞桥别魂犹在啊:独向东风舞楚腰,为谁颦恨为谁娇?灞陵桥畔销魂处,临水傍堤切切条。诗以灞桥烟柳,即就成章。
“灞桥”之外,以“灞河”、“灞池”、“灞亭”、“灞柳”、“灞岸”、“灞陵”、“灞上”等等,为意象的诗词,实则是灞桥意象的延伸或者说拓展,仍旧属于灞桥诗词一类。这构成了“灞桥”意象更繁盛的表达,更丰富多变的容纳。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送别一位朋友回洛阳,相饮于霸池,句云:“霸池一相送,流涕向烟霞”(《送李庶子致仕还洛》)。中唐墨客李益的《途中寄李二》又云:“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好风倘借低枝便,莫遣青丝扫路尘。” 晚唐墨客罗隐《柳》云:“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依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均在送别之间,反复翻意。
2.灞桥之于思人。如宋人潘柽《赠姜邦杰》有句:“应记灞桥人寂寞,依然风雪撚霜髭。” 晁冲之亦有《玉蝴蝶》云:“目断江南千里,灞桥一望,烟水微茫。”清人王士祯《灞桥寄内》:“太华终南万里遥,西来无处不魂销。闺中若问金钱卜,秋雨秋风过灞桥。”两情相思,写得婉转。
3.灞桥之于历史兴亡。
面对唐朝盘据乱象,墨客引发离乱之殇。如胡曾《咏史诗·灞岸》:“长安城外白云秋,萧索悲风灞水流。 因想汉朝离乱日,仲宣从此向荆州。” 再如李商隐《灞岸》七绝:“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
灞水桥边倚华表,平时仲春有东巡。”墨客依赖灞桥,远不雅观长思,字里行间,是沉痛的伤乱。这里的“灞桥”,更见沧桑之感。再如民国于右任《灞桥》:“吾戴吾头竟入关,关门失落险一开颜。灞桥两岸青青柳,曾见亡人几个还?”
当然,灞桥兴亡,古今一绝,自然少不了李太白。一首古风式的《霸陵行送别》,开头便是“送君霸陵亭,灞水流浩浩”,谪仙的气势出来了。到了千古绝唱《忆秦娥·箫声咽》,李白写出了“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将灞桥的历史、沧桑与伤别的主调,交汇至此,一时称冠今古,王国维许为“千古登临之口”(《人间词话》)。
4.灞桥之于孤独与流落。这也是“灞桥”意象广泛寄寓的情思。如晚唐墨客罗隐的《红叶》:“游子灞陵道,美人长信宫。”再如唐朝墨客黄滔《壬癸岁书情》云:“易生唯白发,难立是浮名。 惆怅灞桥路,秋风谁入行。”宋代词人张炎,在他的《悲惨犯/北游道中寄怀》中说得更加明白:“酸风自咽。拥吟鼻、征衣暗裂。正凄迷、天涯羁旅,不似灞桥雪。”又在《摸鱼儿·又孤吟》中说:“又孤吟、灞桥深雪,千山绝尽飞鸟。梅花也著东风笑,一夜瘦添多少。春悄悄。”同样是一片萧索的孤独。再如李商隐的《泪》:“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一场送别,却牵出身世之伤,穷达之慨。
5.灞桥之于人生失落意。如卢尚卿七律《东归诗》:“九重丹诏下尘埃,深锁文闱罢选才。 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 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灞陵桥上过,路人应笑腊前回。”将一个学子的落第写得蕴藉、体面,还带一点调侃和心伤。再如晚唐墨客刘沧《长安冬夜书情》:“古巷月高山色静,寒芜霜落灞原空。今来唯问心期事,独望青云路未通。” 同样的失落落。
6.其余,“灞桥”意象还有刚健的一壁。如李贺《送秦光禄北征》:“髯胡频犯塞,高慢似横霓。灞水楼船渡,营门细柳开。将军驰白马,豪彦骋雄材。”写了灞桥出征的大唐锐气。岑参《浐水东店送唐子归嵩阳》:“野店临官路,重城压御堤。山开灞水北,雨过杜陵西。归梦秋能作,乡书醉
灞桥别号“情尽桥”、“断肠桥”、“销魂桥”。表达不一,源出不同,却都是指向一个意思,那便是依依惜别之情。杜颜《灞桥赋》云:“莫不际此地而举征袂,遥相望兮怆离群,或披襟以延伫,独掩涕而无已。”唐墨客雍陶的《折柳桥》,可堪表明:“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
千古灞桥,承载了多少变幻,又岂止离人、游子和征夫。
“灞桥风雪”与“灞桥风雪骑驴”这就要说到“灞桥风雪”的掌故了。“灞桥风雪”又称“灞柳风雪”。清《西安府志》云:“灞桥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亚肩迭背,为长安之壮不雅观。”每当春意盎然、东风迎面之际,漫天柳絮飞舞,烟雾蒙蒙,为长安灞桥一大景致。也一度是“长安八景”之一。
最初这里的“风雪”显然是虚指,并非真正的风雪,而是柳絮喻雪。而说到这个,不能不提到东晋才女谢道韫。她是东晋绅士谢安侄女。据刘义庆《世说新语》,一天谢安跟子侄辈谈诗论文。不一会儿,天空飘起了又大又急的雪,谢安高兴地起句:“大雪纷纭何所似?”侄子谢朗说像天空撒盐。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赞,谢道韫由是被称“咏絮才”,这段故事也一贯为人津津乐道。
不仅诗文,“灞柳风雪”还是很多画家绘画素材。如南宋画家夏圭,明代画家沈周、吴伟、吴士英等人,都有名画《灞桥风雪图》。
即便唐之后首都西移,长安不再是中央,迎来送往的灞桥也不再劳碌如初,灞桥风雪的奇景却至清不绝。清朝康熙年间还有朱集义作诗:“古桥石板半倾欹,柳色青青近扫眉,浅水平沙深客恨,轻盈飞絮欲题诗”。
但另一方面,“灞桥风雪”的涵义到了晚唐,确实不一样了。尤其是经当时的宰相郑綮演绎后,“灞桥风雪”走出了另一个画风。据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相国郑綮善诗。或谓:‘相国近有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这一番诙谐的对话,一下了将“灞桥风雪”的春日实景,在加入驴子的形象后,变成了一种写诗探求灵感的俏皮说法,一种作诗的情调和自我调侃。
而“灞桥、风雪加驴子”的典故,最早源自孟浩然。据明代文人张岱《夜航船》记载,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后来的李贺、孟郊、贾岛等人都有效法,于是“灞桥风雪”中的“风雪”不但保留了原意“柳絮”之意,同时拥有了新意,即“风雪”便是冬日的“风雪”,被坐实。原来形容繁花似锦的春色,现在也有了在大雪天探求作诗灵感的表意。这与宋人作诗讲究理趣一拍即合。故宋人诗词里的“灞桥风雪”多是这一种意思。
如 吴龙翰《久客湖海买舟西还》:“万里烟波兴渺然,片心如在灞桥边。归装诗少不成担,自拗梅花凑满船。”再如秦不雅观词《忆秦娥》:“灞桥雪,茫茫万径人踪灭。人踪灭,此时方见,乾坤空阔。骑驴老子真奇绝?肩山吟耸清寒冽。”陆游七律《作梦》颔联:“结茅杜曲桑麻地,觅句灞桥风雪天。” 又《幽居书事》:“山阴清绝君须记,雪里骑驴未办诗。”范成大:“犯寒书剑出春萝,风雪桥边得句多(《李子永赴溧水,过吴访别,戏书送之》)。”明人王行《如梦令/题雪景》:“满眼落花飞絮,回顾琼林玉树。驴背是何人?得了灞桥诗句。”清人孙中岳:“词笔已从梁苑秃,诗情又向灞桥生。”都因此“灞桥风雪”代指作诗的雅兴或灵感。
灞桥与规复之志
紧张表现在大墨客陆游。此时的南宋已经沦为半壁江山。昔日繁华象征的长安、灞桥成为金人的盘踞区。作为主战派的武断代表,陆游渴望收复失落地,48岁时从军南郑,只有短短的8个月,却彻底引发了他的爱国激情与战斗意志。反响在诗里,“他的气概沉雄、轩昂,每一个字都从纸面上直跳起来”(朱东润/《陆游传》)。不少写到灞桥的诗词,除了表达“灞桥风雪骑驴”的雅兴,便是抒发光复河山的壮志。
长调《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里,墨客末了感叹:“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悲惨谁寄音?东风里,有灞桥烟柳,知我归心。”这跟他在那首著名的词,《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里的煞拍,一模一样::“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灞桥已经融为江山故国的代称。
此外,近代女词人沈祖棻身处动乱,一曲《霜花腴/雪》,有句:“灞桥梦残,纵凭高、休望长安。”亦有故国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