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词题材广阔,百花齐放,在苏轼以前,宋代的词作多写男女之情、离去愁绪,怨妇之思,好似靡靡之音,但是苏轼的词却冲破了这个束缚,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线,肃清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首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无怪乎有人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不雅观。”
苏轼所创作的词首创了新的词风,具有主要的地位。苏轼的词横跨豪放柔顺约两个领域,他的词作中有气候一新的咏物词,缠绵悱恻的悼亡词,雄浑豪壮的怀古词,清新自然的村落庄词,以及动情悠扬的送别词等,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在苏轼浩繁广阔的题材中,他的送别词风格多样,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犹如他的宋词花园中的一朵琪花瑶草,为词坛增长了优雅的气候。
苏轼的送别词都是在送别朋侪时写下的,苏轼的生平,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他仕途的第一站便是凤翔,此后他又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度过了基层磨炼的光阴;在汴梁,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光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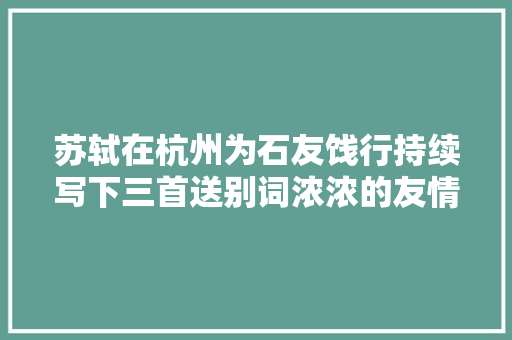
乌台诗案后,他在贬谪的道路上与黄州、汝州结下不解之缘;此后,随着仕途的起起伏伏,他又从汴梁动身,一起兜兜转转,南下与北上,再临杭州、行旅颍州、南下扬州、北上定州,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不朽的诗词作品;在惠州、儋州,他度过了人生中的末了光阴。
苏轼的足迹北至定州、密州,南至惠州、儋州,迎来送往成为苏轼生命中的常态。诗和远方,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苏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为人正派坦率、襟怀开阔、洒脱不拘。在他不平凡的生平中,他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他的生平中交游甚广,以是朋友遍天下。
正因如此,在一次次的迎来送往中,苏轼的一阕阕送给词也就从他的笔端倾泻而下,苏轼的送别诗交情诗词内容十分丰富。
与他送别、唱和的朋侪中不仅有王侯将相、高僧绅士,也有他的学生或是普罗大众。而杭州,是苏轼两次事情过的地方,苏轼的第一次杭州之行,因此通判的身份来到杭州的,这一职位相称于杭州副市长。
而当时的杭州知州是陈襄,陈襄,字述古。苏轼与陈襄在杭州共事期间,两人情投意合,相知甚深。当陈襄调离杭州时,苏轼在有美堂为上司兼朋友的陈襄饯行,在推杯换盏之际,苏轼有感于交情的珍惜,随即谱写了这首《虞美人》,赠给陈襄,原词如下: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次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更阑风静欲归时,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苏轼这首词虽是官场中的饯行之作,但并非虚和应景,而是从心间流出的真情,由于情真,以是意切。上片前两句极写杭州有美堂的形胜,也即湖山满眼、一望千里的壮不雅观。
后两句反响了词人此时此刻的心情:朋友此去,何时方能重回杭州?何时方能杯酒遣怀?他的惜别深情是由于他们志同道合,陈襄因批评王安石和“论青苗法不便”,被贬出知陈州、杭州。然而他不以迁谪为意,在杭州任上,励精图治,齐心专心为民。
而苏轼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外任,来到杭州,他们共事的两年多过程中,能折衷同等,组织治蝗,赈济饥民,浚治杭州六井,兴办学校,提拔文学后进。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公民的事,在共事的过程中,他们也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下片是词人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对杭州繁华景象进行了描写。词人放眼望去,沙河塘里两岸华灯初上,从江上传来的曲调正是唐代盛行的歌曲《水调》,他由此而想到杜牧笔下的十里扬州,并把它与杭州景物联系起来。
直到宋代,《水调》仍风行民间,这种曲调旋律伤感,于此时听来,更增长离怀别思。离思是一种抽象的思绪,能觉得到,却看不见,摸不着,对它本身作详细描摹很困难。词人借助华灯和悲歌,既写出环境,又写出心境,极见功力之深。
结尾两句,苏轼借“碧琉璃”喻指江水的碧绿清澈,生动形象地形容了有美堂前水月交辉、碧光如镜的夜景:当夜深风静我们扶醉欲归时,只见在一轮明月的映照下,钱塘江水澄澈得像碧色琉璃。
行文至此,词人的感情同满江明月、万顷碧光凝成一片,仿佛暂时忘掉了适才的宴饮和世间的骚动,而进入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妙境界。在词中,明澈如镜、温婉安谧的江月,象征朋侪高洁的品质,也象征他们交情的纯洁深厚。
此词以美的意象,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词中美好蕴藉的意象,是作者的感情与外界景物发生互换而形成的,是词人自我情绪的象征;那千里湖山,那一江明月,是词民气灵深处缕缕情思的闪现。
一曲歌罢,酒过三巡,离陈襄动身的韶光越来越近,而送别的情景依然在延续。十里长亭相送,自古以来便是送别的名场景,而苏轼心中对好友的拜别有万般的不舍,以是,他决定将好友再送一程。
当送行的人群来到孤山竹阁的时候,苏轼又一次为陈襄设宴饯行,竹阁在杭州西湖孤山寺内,为唐代墨客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所建,故又称白公竹阁。在竹阁饯行的宴会上,还有歌女吟唱着苏轼刚刚填好的另一首送别词《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画堂新构近孤山。曲栏干,为谁安?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欲棹小舟寻往事,无处问,水连天。
当歌女吟唱起这首送别词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冲动了,连歌女也被苏轼歌词中的深情所冲动,她们在吟唱的时候落下了伤心的泪水,但歌女们又羞于在宴会上落泪,恐怕会给宴会增长忧伤的气氛,以是她们用纨扇掩面而偷偷落泪,压抑着情绪。于是她们移宫换羽,不再演唱苏轼的伤感歌词,而是唱起了唐代墨客王维的送别名曲《阳关曲》。
而此时的苏轼呢,贰心中明白,纵然陈襄离开了,他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天下,要年夜胆面对饱经离去的人生,于是他殷勤劝陈襄再饮一杯送别的酒。
竹阁的画堂是陈襄在任时建筑的,画堂色彩斑斓,依山傍水在孤山上,还有风雅玲珑的曲栏干。苏轼在这里宴别陈襄,自然有人去楼空、触景生情之感。在苏轼的看来,如果好友陈襄不离任,或许还可以和他在画堂的曲栏徘徊不雅观眺。
这也不由得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顾,去年春天,苏轼与陈襄等僚友曾数次游湖,吟诗作词,眼下已是花飞春尽,大好春色要到明年才有了。
欲棹小舟寻往事,无处问,水连天。结尾处含蕴空灵而情意无穷。官妓想象她明年春日再驾着小船在西湖寻觅旧迹欢踪时,往事或许已如风,渺茫无处寻访,唯有倍加惦记与伤心而已。
苏轼送别朋友的情意总是发自肺腑,虽为送别而作,却都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毫无半点矫揉造作,词意情绪流泻,浑然天成。
看着陈襄拜别的身影,苏轼以为此去一别,何时才能再见好友一壁,这样一想,不觉悲从中来,于是他又提笔填写了这首《南乡子》,以此来表达此刻的离去之情:
回顾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
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词的上片回叙分离后回望离去之地临平镇和临平山,抒写了对往事无限美好的回顾和对朋侪的留恋之情。
起首两句写词人对陈襄的拜别特殊依依不舍,一送再送,直到转头不见城中的人影,而那临平山上亭亭伫立的高塔彷佛也在翘首西望陈襄拜别的身影,不忍好友的调离。
下片写词人归途中因思念朋侪而夜不成眠。晚风凄清,枕上初寒,残灯斜照,微光闪烁,这些意象的组接,营造出清冷孤寂的氛围,陪衬了词人的悲惨孤寂心境。
苏轼生平仕途坎坷,他在困顿中愈加感到交情的弥足宝贵。他的感情给予朋侪,常和好友休戚与共,相濡以沫;苏轼格外器重朋友的相聚与相逢,更多情于离愁别恨,但他不会悲悲切切、刻意雕饰,而因此朴拙的情绪宣泄心灵深处的交情。
从苏轼送别陈襄时写的这三首词来看,苏轼的送别词不但以情动人,而且使人得到启迪与抚慰,他冲破词为艳科的传统风格,在交情中注入豪放的进取精神。
苏轼性情中旷达坦率、正派乐不雅观的精神鼓舞着朋友们,也正是对朋侪的朗照日月的至心使苏轼的诗词洋溢着诚挚的交情,使他的妙语佳句如“万斛之泉”滔滔涌出。
苏轼之前的词人,他们谱写离愁别绪,格调大多低沉凄婉,如柳永笔下的“多情自古伤离去”,而苏轼送别词中也有离愁别绪,但不仅仅建立在这一基点上,他的送别词中的交情有着高亢豪迈的气概。
更主要的是,在对朋友的情绪表露上,苏轼领悟了诗庄词媚的各自特点,在词中注入了大江东去的豪迈气势,倾吐出朋侪世的空想与抱负,从而拓宽了词的表现力,打破了绵软纤细的情绪界线,表现出丰富而朴拙的情绪,进一步深化了词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