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歌咏柳树的古诗词,真的是太多太多。古人尤其喜好以柳入诗,咏柳成了咏物诗中的一个门类。
为何历代文人骚客都钟爱写柳呢?“柳”与“留”谐音,古人分别时每每有折柳枝相赠的风尚。逐渐地“折柳”就富有怀远惜别的涵义。
以是古人写的咏柳诗多写相思、离去。
柳树,人们已经是见惯不惊了;咏柳诗作为诗歌的一种种别,也是加倍为人们所熟习的。因此越是大略的事物,越是多数人写的诗,就越是难写。如果要在一众咏柳诗中,脱颖而出,不写出些新鲜的东西来,就不会引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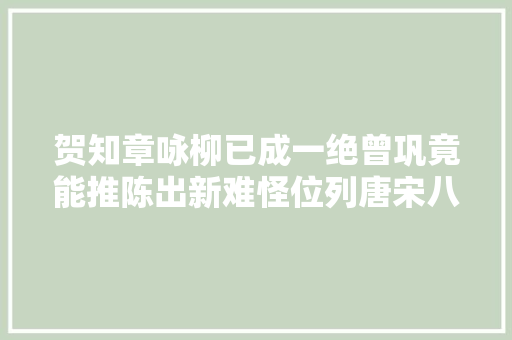
在一众咏柳诗中,不得不提到贺知章的《咏柳》。在笔者看来,这不仅写活了柳树,更写绝了盛唐的春天。
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来,
仲春东风似剪刀。
这首诗写的柳树有多美呢?在那阳光明媚,东风送暖的早春仲春,那些沉睡了一个冬季的柳树,偷偷地地抽芽出叶。那一片片嫩叶还泛着点点绿光,远了望去,像是用一小块一小块的碧玉装扮而起的。
那千万条垂下的柳枝就像一条条洒脱的丝带,如妩媚可人的少女,亭亭玉立。
清风吹来,缕缕柳丝迎风舞动。如丝帛,如绸带,婀娜多姿。这些翠如碧玉的嫩叶呀,怎么说生出就生出来了呢?难道是春天这个高等的裁剪师,拿起仲春的东风作剪刀裁剪出来的?
贺知章笔下的这首《咏柳》,如果只以柳树“高”、色“碧”、形“丝”等特点展开来写,这不过是写出了老百姓普遍认知中的柳树,不敷以千古流传。
这首诗的精妙之处不在前两句对柳树的直接描写,而在后两句是墨客奇妙的想象和那绝妙的比喻。写柳树轻盈俊秀的诗词很多,但在贺知章之前,谁能想象把那仲春的东风,比喻为裁缝手里的剪刀呢?
贺知章奥妙利用拟人与比喻,将一棵普通的柳树写得充满诗意,这首《咏柳》也成一绝。
但是,如果你以为贺知章的《咏柳》已成咏物诗里的顶峰,那可就错了。须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
数百年后的北宋,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打算写一首《咏柳》。
但是,有贺知章的珠玉在前,从哪个角度写咏柳才能出奇出新呢?众人皆知,柳树有离去伤感之意,如果再从这个角度写,就落入俗套。像贺知章那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难以超越。
于是,曾巩想到另辟路子。他看到那柳絮在风中随意率性飞扬,散发的漫天都是的情景,溘然灵机一动,写成了千古绝唱:
乱条犹未变初黄,
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这首诗一出,冲破了人们历来对柳树的固定印象,而且柳树在曾巩诗中也已经不是大略的咏物诗了,而是由物及人,状物与哲理交融——
“乱条犹未变初黄”,一个“乱”字,写出了柳絮随风乱舞的样子,更可叹的是,此时的柳条还“未变初黄”呢!
看,这像不像生活中那些羽翼未丰就不可一世的专横狂小人?
“倚得东风势便狂”,一个“倚”字,一个“狂”字,已经不仅仅是写柳树缭乱的姿态了,更是借柳树写出了小人得志一人得道的觉得,这是多么辛辣而无情的讽刺!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末了这一句,明显是墨客给那些专横狂小人的忠言:别看你现在把自己的柳絮散发的漫天都是,蒙蔽了日月新天,要知道天地之间还有清霜!
看你还能蹦跶到何时!
曾巩写这首诗的时候,恰逢王安石变法,此时朝廷涌现了很多趋炎附势的小人。曾巩实在看不过去,于是借咏柳,对那些在政治上倚仗权贵的无耻小人进行严肃的指斥。
全诗比喻形象,借物喻理,不浅薄直露,寓意深刻,发人深省,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贺知章的咏柳诗,柳树是被美化的意象;而曾巩的咏柳诗,则是故意丑化柳树。但不管怎么说,曾巩能在贺知章精良前作之上,匠心独运,推陈出新,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写咏柳诗,足见其诗中高超的叙事说理能力。曾巩的《咏柳》足以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