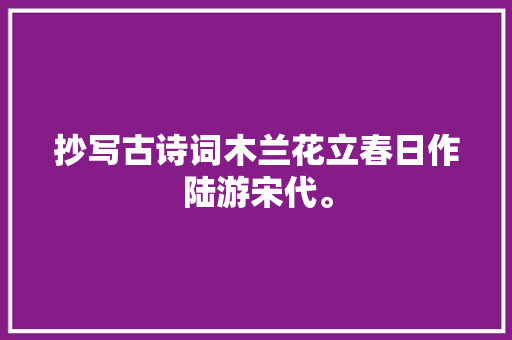陆游自三十九岁被贬出临安,到镇江作通判,旋移隆兴(府治在本日江西省南昌市);四十二岁又由于“力说张浚用兵”,被削官归山阴故里;到四十五岁才又得到起用夔州通判的新命。他的朋友韩元吉在《送陆务不雅观序》中把陆游心中要说的话说了个高兴:“朝与一官,夕畀一职,曾未足伤朝廷之大;旦而引之东隅,暮而置之西陲,亦无害幅员之广也。……务不雅观之于丹阳(镇江),则既为贰矣,迩而迁之远,辅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称小大无改于旧,则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风涛之险(由于途中舟坏,陆游险些被溺死)病妻弱子,左饘右药……”(《南涧甲乙稿》卷十四)。这段话是送陆游从镇江移官到隆兴时写的,说得冲动大方愤慨。从近处愈调愈远,既不是明明白白的贬职,也不是由于升迁,为什么要这样折腾他呢?韩元吉故作不解,实在他是最理解这个中的缘由的。孝宗赵眘登基后,表面上志存规复,实则首鼠两端。陆游坚持奉劝孝宗抗金,孝宗对之貌似奖掖而实则畏恶。陆游在内政上主见加强中心集权,以增强国力,由此也得罪了握有实权的官僚集团。先前由京官而出判镇江,对他是一个挫折;进而罢黜归里,更是一个挫折;此刻虽起用而远判巴蜀,这又是一个挫折。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显然并非加之于一人,而是意在摧折全体主战派的心志,浇灭抗金复国的火种,那么不幸的人岂只是陆游一个人吗?由此可见,三年流落之哀,不仅是一己之哀,实在是国家民族的大哀。创痛巨深,安得不言之如此深奥深厚痛切?
上片正面写心底烦闷潦倒之情,抒发报国无门之愤这是陆游诗词的主旋律,在写法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下片忽然换意,紧扣“立春”二字,以醉狂之态写沉痛之怀,设色陡变,奇峰突起。立春这一天士大夫戴旛胜于头上,这是宋时的一种习俗,戴上旛胜表吉庆之意。但戴银旛而曰“试”,节日痛饮而曰“判”(“判”即“拚”之意),就显然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不平常意味了。这只是词人借酒消愁,逢场作戏罢了,而内心是很伤感的。结尾处更是飏开一笔,表面上是说不是他一人偏老,而实际上是词人深深感到光阴的虚度。这就在上片烦闷潦倒的情怀上,又添一段新愁。词人强自宽解,故作旷达,正是推开一层、透过一层的写法。哭泣本人间痛事,欢笑乃人间快事。
但今日有人焉,不得不抹干老泪,强颜顺俗,把哭脸装成笑脸,让酒红遮住泪痕,这种笑,岂不比哭还要悲惨吗?东坡《赤壁赋》物我变与不变之论,辛弃疾《丑奴儿》“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句,都是强为解脱而写的违心之言,写出更深一层的悲哀,那手腕近乎反衬,那境界是一样平常人所难以达到的。
纵不雅观全词,高下片都是写心底烦闷之情,但乍看竟好象是两幅图画,两种情怀。沈谦论词作云:“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蕴藉。”(《填词杂说》)但作词之道,条贯、错综,两不可失落,此意刘永济《词论·构造篇》曾深言之。读陆游此词,烦闷之情贯穿始终,高下片表现手腕截然相异,构局又极错综繁芜。读上片,看到的是一个忧国伤时、穷愁潦倒的悲剧人物形象;读下片,看到的是一个头戴银旛,醉态可掬的笑剧人物形象。粗看似迥然不同,但仔细看看他脸上的笑全都是装出来的苦笑,终于领悟到这笑剧实在不过是更深奥深厚的悲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