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孔役夫旧书网APP动态
(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在春季末了一个节气开始的时候,读完了浩然的短篇小说集《春歌集》。这部作品揭橥于文革中期的一九七三年七月,但是个中收录的却是作者文革前十年间的“习作”,个中第一篇《喜鹊登枝》作于一九五六年八月,最末一篇《初显技艺》作于一九六六年春天。
提到《春歌集》,就不得不提到作者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彩霞集》。由于《春歌集》中有近乎一半的篇章,都曾涌现于十年前(一九六三年十仲春)出版的《彩霞集》之中。而《彩霞集》自初版后一贯没有重版,想来是由于《春歌集》的珠玉在后吧。实在所谓“珠玉在后”,而不是“在前”,还是由于作者对付所选录的篇章做了“一番笔墨上的加工”,实在便是做了符合文革时期对付文学哀求的修正。虽然说经由了修正,但是书中对付人物的刻画,风景的描写,笔墨的利用,情节的编排,呈现给读者的每一篇小说都非常生动而富有河北屯子的生活气息与民俗风味,展卷读来令人饶有兴味。众所周知,文革中对付所有文艺作品的哀求便是“三突出”,说白了便是一点突出政治。政治性强了,故事及人物的文学艺术性一定大打折扣,于是大部分文革作品都呈现出一副理念“严明,刻板”,人物“横眉立目”,情节“狂风暴雨”的征象。然而品读《春歌集》,自己却没有感想熏染到上述那些觉得,而是正相反,所感想熏染到的是“生动,活泼,是清风拂面温暖如春,是和风小雨润物无声”,纵然在后几篇如“老支书故事”和“枣花学艺”系列短篇里,作者描写了“阶级斗争”性子的笔墨,但是却没有其他作品中的一触即发,而因此理服人说服教诲,给人的觉得,那些“坏分子”不过便是一些私欲过重之人罢了。
文革中的浩然,号称“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然而正是这个作家,却在那样一个“严厉”的形式下为广大读者奉献出这样一部并不完备符合当时政治大方向的作品,是故意为之还是“借鸡下蛋”不得而知,但是得益于作者当时的政治地位该当是确实的。想来当年的读者在读到这部作品时所感想熏染到的不仅仅是听到一首“春歌”,更是感想熏染到了“东风”,听到了“春潮”,看到了“春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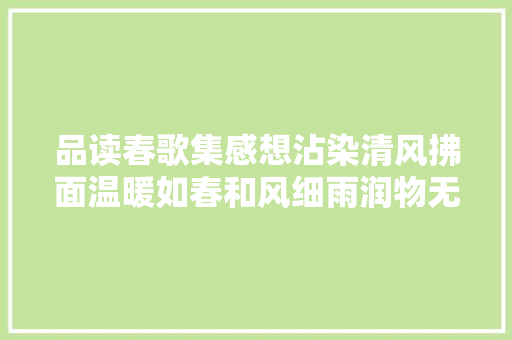
溘然想起,“天下读书日”,搁下《春歌集》,当然可以再捧起别的书。读书日,不可不读书也。